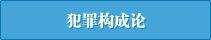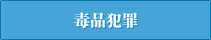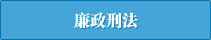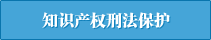魏东:刑法解释学基石范畴的法理阐释
刑法解释学基石范畴的法理阐释*
——关于“刑法解释”的若干重要命题
魏 东**
(四川大学法学院)
引用本文时请注明出处:魏东:《刑法解释学基石范畴的法理阐释——关于“刑法解释”的若干重要命题》,载《法治现代化研究》2018年第3期。
【内容摘要】刑法解释作为刑法解释学的基石范畴,是指对刑法规定含义的理解、阐明和具体适用。刑法解释具有作为法律解释的基本特性,包括司法适用性与司法甄别性、双向性与主体间性、两面性与主客观性、合法性与正当性、方法性与目的性等。刑法解释的类型论可以有多重视角,根据刑法解释的规范目标的立场,刑法解释的分类主要有刑法的主观解释与客观解释;根据刑法解释的规范属性的立场,刑法解释的分类主要有刑法的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根据刑法解释的方法,刑法解释的(方法)分类有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四种(传统经典四分法),但刑法解释方法的传统经典四分法自引入中国开始从来都面临着争议、挑战和发展,中国刑法学者现在越来越多地主张将刑法解释方法分为刑法解释的文义解释方法、论理解释方法、刑事政策解释方法三种(新经典三分法),这种新经典三分法逐渐成为有强大理论解释力的理论共识。
【关键词】刑法解释 司法适用性 刑法解释教义学 经典四分法 新经典三分法
目次:
一、刑法解释的概念界定
二、刑法解释的特性阐释
(一)司法适用性与司法甄别性
(二)双向性与主体间性
(三)两面性与主客观性
(四)合法性与正当性
(五)方法性与目的性
三、刑法解释的类型分析
(一)刑法解释立场:规范目标与规范属性
(二)刑法解释方法:传统经典四分法与新经典三分法
在中国尚处于蹒跚起步的刑法解释学,“刑法解释”作为刑法解释学的一个基石范畴,其概念界定、特性把握、功能指引与类型分析等方面尚存在较为突出的观点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刑法解释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方向,较为严重地阻碍了我国刑法解释学的适当教义化,进而成为影响我国刑事法治建设实践的理论掣肘,亟需进行适当的理论归正。本文就此展开学术研讨,试图在归纳分析既有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刑法解释的概念、特性、功能与类型等基础性法理问题提出某种更为科学合理和“可接受”的学术命题并予以适当阐释,以期抛砖引玉。
一、刑法解释的概念界定
概念界定在本质上是一种形式逻辑方法。刑法解释在形式逻辑上是法律解释的下位概念,因此刑法解释的概念界定必然遵从法律解释的概念逻辑,应当以法律解释的概念逻辑分析为起点。法理学认为,法理学上对于法律解释是否必要的疑问存在争议,“而要回答法律解释及法律解释学的必要性,我们就必须对法律解释或法律解释学是什么搞清楚”[1];再者,法律解释作为法律解释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奠基性的基本范畴,也有必要首先加以概念界定,这是深入展开法律解释学的理论研究所必需解决的首要问题。关于法律解释的概念,西方学者对此主要有以下四种用法或理解:一是解释性活动说或者“泛解释论”。如德沃金认为法律是一种解释性活动,是通过解释的方法解决新的法律问题和使法律自身不断地得到发展的法的运用,包括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等。二是执法活动说或者司法活动说。认为解释是法律运作过程的一个阶段,与立法有别的执法活动,特别是司法或裁判活动。三是司法技术说。认为法律解释是一种与填补漏洞有别的司法技术,它是通过扩大或者缩小法律规定的文字内涵的办法解决所要处理的案件。四是学理解释说。认为法律解释是法学家对法律文本或社会事实进行研究,以阐述法律真实含义的活动。其中,第二种和第三种认识,即执法活动说或者司法活动说、司法技术说是西方法解释学关于“法律解释”的含义的主流见解。[2]
而我国法理学界关于法律解释的见解,经历了一个从与上列西方法理学见解不一致到接近一致的过程。我国的权威性文件中只承认立法机关、最高司法机关和最高行政机关有权进行法律解释,“是不允许或不承认一般的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所进行的‘执法’活动为‘法律解释’的”,对此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学界一般称之为“解释性立法”;我国法律解释学者后来逐步认识到“应该认真研究和科学地吸纳西方占主流观点的‘法律解释’理解”,即认为法律解释的含义所指在总体上不以“立法”、而是以“执法”或处理社会纠纷为对象,讲的是审理案件中的法律的“适用”问题,是“适用”法律的一种方式或技术,即侧重于司法活动并且认为这一领域才是真正的“法律解释”。[3]因此,有学者指出,作为一种具有普适性的理解,法律解释一般是指在具体个案当中或者与法律适用相联系的一种活动。[4]有鉴于此,一方面,我国法理学者针对中国法律解释的概念界定与西方法理学者视野里的法律解释的概念界定之间大异其趣,感叹“如果要和国外学者去交流,就请记住这句话,他们讲的法律解释必然是在个案裁判中适用法律这样一种解释,而不是我们国内所讲的法律解释。因为我们的法律解释概念是个抽象的概念,而他们的解释是在个案中法官的解释,这种分歧是非常非常大的。当然要承认他们的这种理解是更具普适性的,而我们的理解是关起门来的自我欣赏的理解”。[5]另一方面,我国法理学者还主张吸纳中西方两种不同的法律解释理论与实践,将法律解释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即“将西方针对个案的解释称为狭义的法律解释,将中国式的法律解释归入广义的法律解释。广义的的法律解释指对法律内容的说明。狭义的法律解释仅指与个案相关的对法律内容的说明与选择、确定适用规范的推理过程”,“西方的法律解释是经审法官的行为,而在中国法官这类行为没有正当性;中国的法律解释在西方人看来又不是法律解释。也就是说,以西方的概念,中国没有法律解释;以中国的概念,则西方没有法律解释。为了求得一个可以用来描述东西方不同行为的‘法律解释’概念,只能以此‘偷懒’的办法”,这样,法律解释不仅包括对法律文字的理解,也包括对立法者意图的探究,还包括对社会利益的平衡、对社会公理的认同。[6]
综合中西方法理学界的学术见解,我们认为法律解释不仅包括对法律文字的理解,也包括对立法者意图的探究、对社会利益的平衡、对社会公理的认同,因此对法律解释的概念作以下界定比较合理:法律解释是指对法律规定含义的理解、阐明和具体适用。借助法理学对法律解释的概念界定方式,我们认为可以将刑法解释的概念界定如下:刑法解释,是指对刑法规定含义的理解、阐明和具体适用。
中国刑法解释学者对刑法解释的概念界定也有一个逐步摸索、逐步借鉴吸纳中西方的法律解释学尤其是西方刑法解释学原理、逐步臻于完善的发展过程。李希慧教授认为我国学者提出的刑法解释概念可以归纳为五种:一是规范含义阐明说,如认为“刑法的解释就是对刑法规范含义的阐明”[7];二是规范含义及其适用阐明说,如主张“刑法解释就是阐明刑法规范的含义及其适用”[8];三是规范的内容、含义及其适用原则阐释说,如认为刑法解释“是对刑法规范的内容、含义及其适用的原则等所进行的阐释”[9];四是刑事法律意义、内容及其适用说明说,如提出“刑法的解释,就是对刑事法律的意义、内容及其适用所作的说明”[10];五是规范、概念、术语、定义说明说,如主张刑法解释是“对刑法规范的含义以及所使用的概念、术语、定义等所作的说明”[11]。对此五种定义,李希慧教授认为其均存在以下缺陷:都未对刑法解释的主体加以描述;均没有对刑法解释的态式作全面的揭示;均未准确地反映刑法解释的对象范围;未能准确地确定刑法解释的目的。在此基础上,李希慧教授提出了刑法解释的“第六种定义”,即:刑法解释,是指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或者其他机关、社会组织、人民团体、法律专家、学者、司法工作者或者其他公民个人,对刑法规定的含义进行阐明的活动,或者这些主体对刑法规定含义进行阐明的结论。[12]
李希慧教授关于中国学者提出的刑法解释概念的学术归纳较为客观、全面,其个人提出的有关刑法解释概念的学术见解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具有一定代表性,获得了一些刑法学者的明确支持。例如,赵秉志教授和陈志军教授认为“刑法解释是指国家机关、组织或者个人,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法学理论或者自己的理解,对刑法规范的含义等所作的说明”;刑法解释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解释主体的广泛性(即包括刑法解释的权力主体和权利主体),解释对象的特殊性(即解释的对象是刑法规范)、解释性质的从属性(即刑法解释具有从属于刑法立法的性质)。[13]再如徐岱教授也认为,刑法解释的概念必须反映刑法解释的主体、刑法解释的对象、刑法解释的目的、刑法解释的样态等四要素,因而刑法解释的概念应当界定为“刑法解释是指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社会组织及公民对法律文本的意思,基于立法目的所进行的理解与说明”。[14]
自21世纪开启之交开始,中国刑法学者对刑法解释的概念界定逐渐走向简明、科学,高铭暄、马克昌、赵秉志、陈忠林、张明楷等著名学者均给出了较为一致的简明而合理的刑法解释概念,并对刑法解释的“真相”予以深刻揭示。如,高铭暄、马克昌和赵秉志等主张,刑法解释是对于刑法规范含义的阐明[15];张明楷教授认为刑法解释是对刑法规定意义的说明[16],刑法解释的对象是刑法规定,刑法解释的目标应是存在于刑法规范中的客观意思,刑法解释必须同时适应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的需要[17];陈忠林教授和袁林教授指出,刑法解释不仅限于对刑法规范意义的说明这种结果或行为,也包括对刑法规范的理解过程,因此刑法解释不一定要采用以书面或口头言辞进行阐释的形式,解释者“将自己的理解付诸行动”同样是一种“解释”[18]。除这些刑法学者外,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法官牛克乾提出的相关见解值得关注。牛克乾法官认为法理学界关于法律解释范畴的纷争对刑法学界关于刑法解释的概念界定影响不大,并且刑法解释的概念尽管存在分歧但是并没有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大量刑法教科书对刑法解释的界定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主张,一种主张刑法解释是对于刑法规范含义的阐明[19],另一种主张刑法解释是对刑法规定意义的说明[20];牛克乾指出,关于刑法解释的概念及其内在意蕴,刑法学界大体共识有四点,即刑法解释的主体并无特别限制、刑法解释的效力可做有效和无效以及正式解释和非正式解释的区分、刑法解释的场合和目的并不做特别限定、刑法解释是动态解释活动和静态解释结论的统一,因而刑法解释的概念界定的最大分歧点在于对刑法解释对象的认识不同,即刑法解释究竟解释的是刑法规范还是刑法条文,进而认为法律解释的对象应该是法律条文(法律规定)而非法律条文所体现的法律规范,因而认为刑法解释是对刑法规定意义的说明;牛克乾还强调说,我国刑法解释学基于刑法解释分类的共识仍然存在两个明显的不足,一个是将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归结为正式解释的全部而对同样具有法律效力的适用性刑法解释尤其是法官的个案刑法解释适用未能得到体现,另一个是将学理解释等同于非正式解释但忽略了理应关注且对维持刑法解释范畴体系完整性和系统性至关重要的任意解释。[21]
我们认为,尽管刑法解释的主体、权力、目标和目的、体制以及刑法解释方法和结论等问题均可以成为刑法解释必然关注的要素,但是这些要素可以在刑法解释的概念涵摄下进行具体讨论,而无需在刑法解释的概念界定中予以特别列举,否则有违概念界定的形式逻辑,也有违概念界定的简明性和抽象性要求。刑法解释的概念界定应当是尽可能简明扼要地揭示其抽象性的共性特征,而刑法解释的这些抽象性的共性特征只能是“对刑法规定含义的理解、阐明和具体适用”。刑法解释的这一概念界定充分说明了刑法解释主要有两项抽象性的共性特征:其一,刑法解释的性质是对刑法规定含义的“理解、阐明和具体适用”,既包括作为动态的“理解、阐明和具体适用”行动过程,也包括作为静态的“理解、阐明和具体适用”结论;其二,刑法解释的对象是“刑法规定”的规范含义以及作为刑法规定所涵摄的具体案情事实的规范含义。至于刑法解释的主体、权力、目标和目的、体制以及刑法解释方法和结论等要素,其本身本来就是具体的多样性存在,由于这些具体的多样性存在本身可以被刑法解释概念所涵摄,理应在刑法解释概念之下进行具体的多样性的讨论而不应当被纳入刑法解释的概念界定之中,否则将导致刑法解释的概念界定成为繁杂冗长的肥胖症患者。
二、刑法解释的特性阐释
法律解释的特性对于恰当认识和把握刑法解释的特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而,梳理法理学界关于法律解释的特性十分必要。应当说,法理学界对法律解释的特性有多种角度的观察描述。如严存生教授在“法律解释的性质、特点和目的”的标题之下将西方法律解释(理论)的特性归纳为以下几方面:一是法律解释的本质,是法律运作的一个阶段、法发展或法令续造的一种方式;二是法律解释的方式,是裁决或者法的适用,即从性质上说法律解释不是立法活动而是执法活动或者适用法律的活动;三是法律解释的两面性,包含着用法律解释事实和用事实解释法律两面;四是法律解释的双向性(双相性),是解释者与法律文本(及其作者)之间的对话,即解释者带着自己的“前见”并站在新时代的立场上谈他对原法律文本的新理解,解释者在其中有很大的主观能动性;五是法律解释具有二重性,即既有主观性又有客观性,其主观性表现在解释者带有“前见”和目的进行解释、解释的结果具有个性和倾向性,其客观性表现在解释活动不能离开法律文本并且必须以文本为基础和为解释对象、解释者的“前见”和目的不是纯个人的和偶然的而是与时俱进的并且受制于“法律解释共同体”的、解释的标准是客观的并且要遵守相关规则;六是解释的目的,是解决社会纠纷、建立和维护法律秩序、续造法律并使得法律获得新生。[22]可见,严存生教授归纳出的法律解释的特性涵盖了法律解释的本质、法律解释行为过程、法律解释对象、法律解释主体、法律解释立场、法律解释结论、法律解释目的等内容。再如陈金钊教授,其对法律解释的特性归纳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法律解释的突出“特征”的简要归纳,是独断与探究;[23]二是对法律解释的基本“特性”的立体梳理,包括以下四组:解释的独断性与客观性,解释的探究性与创造性,解释的循环性与自主性,解释的正当性、有效性及其语境。[24]陈金钊认为,法律解释采取的是独断的形式、探究的过程,因为,从司法过程的形式性来看,针对案件的法律解释只能是独断型解释,这是法律解释区分于文学解释的显著特征;但是,独断型解释并不意味着法律解释是专断或任意的,独断的解释形式并不排斥法律解释是过程的探究性,法官独断地解释法律是建立在审判过程中不断探究的基础上的,法官独断的意见是对诉讼参与人的各种意见整合的结果。其中,法律解释的这种独断性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根据法律教义学原理,法官在个案中所释放出来的法律意义,被假定是早已存在于法律之中的应有之意,即个案中法官所表达的法律意义不是个人的意思,而是法律中的意义;二是(法官)在法律解释过程中,只能由一个独断的主体(即法官)来确定法律的意义。因此陈金钊强调,法律解释的独断性也许是当然的,“以法官为主体的法律解释,其最根本的特征就是解释的独断性”,而其探究性也是不能缺少的,没有探究的独断很可能是专断,没有独断的探究也可能走向任意。[25]
如果说,针对作为法律解释主体的法官的法律解释特性进行归纳描述,独断性与探究性确实是(法官)法律解释的突出特征;那么,针对普适性的、一般法律解释而言,可能就应当将法律解释的特性概括为:司法适用性、两面性(即用法律解释事实和用事实解释法律的两面性)、双向性(即解释者与法律文本的双向互动性)、二重性(即主观性与客观性)、合法性、正当性(即解释的探究性与创造性)、方法性(即解释的循环性与自主性)、目的性。值得注意的是,法律解释的这些特性必须结合法律解释价值目标、法律解释立场、法律解释原则、法律解释主体、法律解释权、法律解释对象、法律解释行为过程、法律解释方法、法律解释结论等法律解释范畴进行理解和循环阐释。
我国刑法解释学者在较为充分地借鉴吸纳法理学者有关法律解释的特性的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对刑法解释的特性(或者特征)已有一些归纳。如李希慧教授认为,刑法解释的特征应区分动态刑法解释的特征与静态刑法解释的特征,动态刑法解释的特征有三个,即解释主体的广泛性、解释对象的特定性(只能是“刑法规定”)、解释目的的唯一性(仅限于“阐释刑法规定的含义”);静态刑法解释的特征也有三个,即与动态刑法解释的相联性、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作用重要性。[26]再如徐岱教授认为,刑法解释的特征可以归纳为四个,即刑法解释主体的广泛性、刑法解释对象的特定性、刑法解释效力与解释主体的关联性、刑法法律解释目的的明确性(即“刑法解释要以实现法律正义与法律的人文关怀为导向,必须摒弃偏离这一目标的刑法解释”)。[27]其他学者也有一些看法,应当说有的看法比较接近作为法律解释的刑法解释的“本质特征”的提炼,有的看法则比较接近中国刑法解释的“现象特征”的描述,值得进一步审查和研究。
我们认为,按照法律解释学对法律解释的特性的归纳,参照刑法解释学者的既有研究成果,刑法解释具有作为法律解释的基本特性,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司法适用性与司法甄别性、双向性(即解释者与法律文本的双向互动性)与主体间性、两面性(即用法律解释事实和用事实解释法律的两面性)与主客观性、合法性与正当性、方法性与目的性等。
(一)司法适用性与司法甄别性
司法适用性与司法甄别性可以说是刑法解释的两大功能特性。刑法解释的功能,是指刑法解释在刑事法治实践中所具有的价值与功用。广义上讲,刑法解释的功能不仅仅是指刑法解释在刑事法治实践中所具有的价值与功用,还包括其对于刑法理论研究的价值与功用。因此,刑法解释学中有的归纳为刑法解释的价值,有的归纳为刑法解释的功能,有的则归纳为刑法解释的价值目标或者价值功能,应当说其基本含义是一致的。如徐岱教授认为,刑法解释的价值目标有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双重价值目标,形式合理性目标强调刑法解释必须在实定法的框架下进行阐释和运用,其是国民发挥预测可能性最好的标尺;实质理性目标是保护法益目标和功利选择目标。[28]李希慧教授认为,刑法解释的功能是指由刑法解释自身所固有的特征决定的其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刑法解释的功能具体包括规范指导刑法司法功能、弥补刑法立法欠缺功能、促进刑法立法完善功能、刑法法制宣传教育功能、繁荣刑法理论功能。[29]结合刑法解释学原理和学术界已有见解,我们认为,刑法解释的功能主要是司法适用(即实现刑事法治和人权保障)和司法甄别(即发现真正的刑法立法漏洞并有利于完善刑事立法)。
刑法解释作为法律解释的突出特性是司法适用性,其终极目标是为了司法适用,其发生过程、结论的最终形成和运用都围绕着司法适用展开。如前所述,法理学界认为,法律解释的本质是法律运作的一个阶段、法发展或法令续造的一种方式,是法律解释适用的方式,是裁决或者法的适用,从性质上说法律解释不是立法活动而是执法活动或者适用法律的活动,这些论点的核心即在于确认法律解释的司法适用性这一特性,[30]由此可以较为充分地证成“刑法解释的司法适用性”命题。即便在中国语境之下,刑法解释包括司法解释(文本)、立法解释(文本),但是这些刑法解释都具有司法适用性,其起因于、服务于司法适用的需要;更不用说法官针对个案审判时的刑法适用解释,其发生过程、结论的最终形成和运用都围绕着司法适用展开。应当说,刑法解释的这种属性认知(命题认知),部分得益于法理学者关于外国“法律解释(范畴)”的引介和讨论,部分得益于刑法解释学者自身的学术自觉,是十分重要的和值得充分肯定的。尽管其中部分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如立法解释(文本)到底是否可以归属于“法律解释”[31]、是否具有“司法适用性”,以及立法解释(文本)和司法解释(文本)是否可以“再解释”[32]等疑问,但是这些疑问的客观存在仍然无碍于我国刑法解释学关于刑法解释总体上具有司法适用性的逻辑判断。
“刑法解释的司法适用性”命题具有区别于其他部门法解释适用的特殊性,这就是刑法解释所应当具有的适当保守性。刑法解释的保守性命题不但具备法律解释学意义上的正当性,[33]法理学一般认为,法学总体上看是一门比较保守的学科,保守性是法学的一种重要性质;[34]更重要的是,刑法解释的保守性命题有效契合了刑法所特有的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谦抑性的基本要求,有利于具体恰当地解决刑法疑难案件的定罪量刑问题,获得了较多刑法学者的认同,从而获得了刑法解释学意义上更为充分的正当性。[35]因为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就是适当限制国家刑罚权以充分保障人权,其基本要求当然是刑法解释必须保守和内敛,反对过度解释和国家刑罚权的过度张扬。而“刑法谦抑性究其实质,无非是限制刑法的扩张,使其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其可以通过刑事立法上的犯罪圈的划定、刑罚处罚范围、处罚程度和非刑罚处罚方式的适用、刑法解释等方面加以体现,其中刑法解释因是动态的刑法适用第一层次的问题,最能够体现刑法谦抑的精义”。[36]为此,部分刑法学者强调了刑法解释的从属性、严格性等特征。如赵秉志教授明确指出,刑法解释的特征之一是“解释性质的从属性”,认为刑法解释具有从属于刑法立法的性质,刑法解释的任务只是对已有刑法规范的含义进行阐明,不能突破刑法立法所确立的刑法规范,否则罪刑法定主义和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必将成为空谈。[37]再如有学者指出,刑法解释具有从属性和严格性特征,刑法解释的从属性是指刑法解释必须充分尊重和严格遵从刑事立法的内容、精神和权威,并且严格遵从刑法规定的字面含义、刑法立法的目的、刑法的效力等;刑法解释的严格性是指刑法解释必须格外慎重,当然需要严格操作、严格解释。[38]再进一步观察还可以发现,客观上,刑法解释的保守性命题还有利于准确把握当下中国刑法的主观解释与客观解释之争、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之争的内核,有利于合理权衡刑法的秩序维护与人权保障之间的价值紧张关系,以最终达致在适当照顾刑法的秩序维护价值机能的前提下尽力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价值机能(以及个别公正、实质公正)的最佳价值权衡状态,[39]具有十分重大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刑法解释作为法律解释的司法甄别性的重要内容是发现真正的刑法立法漏洞并有利于完善刑事立法。“任何法律秩序都有漏洞”[40],法律漏洞是法理学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异常纠结的理论问题,对其如何恰当界定、逻辑划分、可否填补以及如何填补等问题,均存在理论争议。法理学认为,法律漏洞,是某种“违反立法计划的不圆满状态”[41],是指由于立法者在立法时未能充分预见待调整的社会关系,或者未能有效协调与现有法律之间的关系,或者由于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超越了立法者立法时的遇见范围等原因导致立法缺陷,这种缺陷表现为调整特定社会关系的具体法律规范的缺失,或者既有法律规范之间存在矛盾,或者既有法律规则在今天的适用明显违背了法律对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法律漏洞的分类有明显漏洞与隐藏漏洞、自始漏洞与嗣后漏洞、全部漏洞与部分漏洞、碰撞漏洞与非碰撞漏洞;尽管法律漏洞首先要通过立法来解决而不是通过司法来解决,但是通常要求法官在个案裁判中必须进行漏洞填补,其填补的方法包括类推适用、目的性扩张、目的性限缩、基于习惯法和比较法填补漏洞以及基于法律原则填补漏洞。[42]但是,法理学以及非刑事法律意义上的法律漏洞及其填补原理,由于刑法及其罪刑法定原则的特殊性,通常需要刑法解释学予以特别审查。从刑法解释论立场言,“法律漏洞”应当进一步区分其规范功能属性,将其划分为“真正法律漏洞”与“非真正法律漏洞”。[43]真正法律漏洞属于规范功能性法律漏洞,因其缺失堵截性法律规范为刑法解释提供指引,在法律上难以找到任何明确的扩张解释依据,因而原则上不允许以法律解释技术加以填补而只能予以立法完善;非真正法律漏洞则属于非规范功能性法律漏洞,因其终究有某种明确的堵截性法律规范提供解释指引,故允许以法律解释技术对其加以填补(司法填补)。[44]对于真正的刑法立法漏洞,刑法解释依法不应通过解释入罪,而是确认其为真正的“刑法立法漏洞”并作为问题展现给社会公众和立法者,从而有利于完善刑法立法。可见,通过刑法解释可以发现刑法漏洞、尤其是真正的刑法立法漏洞,然后通过修订完善刑法立法以填补真正的刑法立法漏洞,秉持“解开实然与应然冲突的途径只能从立法技术入手”[45]的严谨态度,最终有利于完善刑事立法并实现刑事法治领域的良法之治。
刑法解释的司法适用性与司法甄别性,还可以合乎逻辑地推导出刑法解释所具有的繁荣整体刑法学知识体系这一特别价值功能。刑法解释是对刑法解释学原理的具体、生动的运用,一方面有利于丰富完善刑法解释学原理,尤其是在我国“法制体系(立法体系)相对完备之后,我国法学研究的重心就应当转向法律解释学”[46];另一方面有利于检验、运用其他刑法学原理,最终有利于实现整体刑法学知识的增长和体系性完善。我国刑法学通过数十年尤其是近二十年理论熔铸逐渐走向成熟并向着刑法教义学的方向发展[47],其中刑法解释学的成熟发展和适当教义化是刑法教义学十分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刑法解释毫无疑义地具有繁荣整体刑法学知识体系的价值功能。
(二)双向性与主体间性
刑法解释作为法律解释的主客体性的重要方面表现为刑法解释者(解释主体)与作为刑法解释对象的刑法规范文本(解释客体)之间的双向互动,解释者理解和解释刑法规范文本,刑法规范文本限定解释者的理解和解释根据,刑法解释的双向性特征有利于确保刑法解释的合法、客观、合理的刑事法治理性。解释者与法律文本(及其作者)之间的对话,即解释者带着自己的“前见”并站在新时代的立场上谈他对原法律文本的新理解,解释者在其中有很大的主观能动性,包括解释立场、解释限度的选择与确定,既是刑法解释的双向性(或者双相性)互动的体现,也表明刑法解释的二重性(即主观性和客观性)交织的体现。
刑法解释主体,是指刑法解释者,即刑法解释的作出者、发布者、决定者、行动者,包括所有进行刑法解释的组织与个人。与刑法解释主体相关的问题是刑法解释权。刑法解释权是指进行刑法解释的权力。应当说,刑法解释主体在刑法史上曾经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以确定哪些机关、哪些人员的刑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在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刑法解释主体问题,西方国家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基本上一体化地承认法官是当然的刑法解释主体,法官针对具体个案具有无可争辩的刑法解释权。但是,现实主义的实践论者发现,在中国当下刑法解释实践中,似乎并不承认法官个体的刑法解释主体资格和刑法解释权,而仅仅承认了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刑法立法解释)、作为最高司法机关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刑法司法解释)的刑法解释主体资格和权力,除此之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个人均没有法律解释主体资格和权力。当然,关于刑法解释主体资格和权力问题的这种理解,是建立在作出有效力的刑法解释的主体资格和权力的意义上的,这种意义上的刑法解释主体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刑法立法解释主体)、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刑法司法解释主体)。需要指出的是,针对我国的国家立法层面上仅仅承认了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刑法立法解释权,以及作为最高司法机关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刑法司法解释权这一制度性安排,我国学术界是将其归结于“刑法解释体制”问题加以研讨的。林维教授认为,刑法解释权力体制在我国的历史演变,可以分为一元单极刑法解释体制(1949年至1954年)、二元单极刑法解释体制(1954年至1981年)和二元多级刑法解释体制(1981年至今)。[48]对此,陈兴良教授指出,不仅法官,甚至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的各级人民法院都是没有司法解释权的,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具有司法解释权,又是中国特色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司法解释更是一种权力之行使,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一种准立法权。因而司法解释也就具有司法法的性质”;“我称之为司法法,即司法机关制定的法”,即“我国司法解释是一种亚法”;在“刑法解释是一种权力运用”的视域下,“林维对刑法解释作出如下界定:一是作为法律活动或者行为的刑法解释;二是作为特定结论的刑法解释;三是作为技术或者方法的刑法解释;四是作为制度及其运作的刑法解释”。[49]因为在二元多级的刑法解释体制下,“附属于正式解释权力主体的部门或者个体也都以独特的方式进行着解释,并且现实地发挥着正式权力一般的效果,填补着正式权力所无法顾及的方面、领域,而更为众多的非正式解释主体又以丰富的形式参与着刑法的解释,他们可能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具有任何的强制效力,但是通过特定的参与途径影响、制约着正式解释权力的实现。这一格局的形成都来源于系统中正式权力和非正式权力的分界,充分地反映了刑法解释权力解释的复杂性”。[50]也就是说,在形式逻辑上,刑法解释主体是指所有进行刑法解释的组织与个人。这些论述的启发意义在于,中国刑法解释学必须适当关注刑法解释主体及其权力分析、由刑法解释主体和刑法解释权所共同型构的刑法解释体制问题。
关于刑法解释对象,法理学认为,法律解释的对象是指法律解释的标的,包括法律文本(规范文本)与案情事实(法律事实)。[51]其中,法律文本是法律解释的首要对象、基础对象,对于法律解释研究具有更为基础的意义,因而,法律文本通常是法解释学研究的重点。同时,案情事实也是法解释学必须关注和解释的对象,由此才能将法律文本与案情事实对接,将文本意义上的“死法”变成现实意义上的“活法”,并对现实社会生活发生实际作用。因此,刑法解释对象,是指刑法解释的对象文本与对象事实。作为刑法解释对象的文本,只能是刑法,即刑法典以及刑法修正案、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因而,“刑法”以外的其他法律文本以及全部“软法”文本,[52]其中当然包括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出台的各种“司法解释”规范文本,均不属于作为刑法解释对象的文本。作为刑法解释对象的刑案事实,只能是“证据确实、充分”予以证实的并且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案情事实,而不能是诸如民事领域之中所要求的“优势证据”予以证实的案情事实。关于刑法解释对象事实与其他部门法之法解释对象事实的这一简单对比其实也表明,作为刑法解释对象的“事实”远比作为其他部门法之法解释对象的“事实”要严格得多、保守得多,其从刑法解释对象的角度十分鲜明地彰显了刑法解释的保守性(命题)。[53]
应当指出,刑法解释的双向性(双相性)还与“刑法解释的主体间性”命题紧密相关。刑法解释作为法律解释的主体间性,有诠释学范式与方法论范式两层意义的阐释。诠释学范式指出,刑法解释主体间性(命题)意味着“刑法意义是使用者与文本‘主体间’对话的产物,使用者天然是刑法意义的创造者”,“法律解释就是读者与法律文本商谈的过程,法律意义是二者在商谈中达成的共识”;进而“可以将刑法意义生成的主体间性特征归纳如下:其一,刑法意义不是客体,而是读者意识和文本主体间关系的产物”,“其二,法律解释的过程就是法律意义生成的过程”,“其三,法律解释的任务是创造(而非发现)法律的意义”,“其四,刑法意义具有无限性”;因此“刑法的解释目标应是:在文本的意义界限内,立足于读者全部的案例经验,最大化地实现社会主流价值观认可的罪刑等价关系”。[54]可见,诠释学范式视野下的主体间性,主要揭示的是刑法解释的双向性(命题),其重要内容是将刑法文本予以拟人化并带有浓烈思辨性质:刑法解释者作为实在的人(解释主体)与刑法文本作为拟制的人(解释对象)之间进行平等的“主体间”对话,最终获得的“法律意义是二者在商谈中达成的共识”。而方法论范式认为,刑法解释的主体间性(命题)实质上揭示的是解释主体上的多元性与解释结论上的法律论证性。如有学者指出,“刑法解释从来都不是一个解释问题,而是一个论证问题,现代刑法解释学应将刑法文本融入解释者的价值判断,来消解刑法文本及其所用语言过于僵化的弊端,建立一种基于主体间性的刑法解释理论,从而使刑法文本与案件事实有效地对接起来,并以法律论证实现刑法解释结论的可接受性。”[55]再如有学者指出,“刑法解释主体是具有多元价值观的解释者构成的解释共同体,刑法解释的标准是多元互动解释共同体通过对话协商获得的共识。制度化的对话协商可以通过求同存异的办法防止实质性价值冲突的激化,成为刑法解释及适用的合法性保障。”[56]应当认为,方法论范式视野下的刑法解释的主体间性(命题)更值得重视,尤其是该命题所主张的多元互动解释共同体通过制度性的法律论证有助于形成刑法解释结论上的法律论证性并使得刑法解释结论更加臻于完美。
(三)两面性与主客观性
刑法解释的两面性(命题),是指刑法解释作为法律解释的对象包括刑法规范文本(含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也包括案情事实,刑法解释的过程是在刑法规范文本与案情事实之间的往返循环,包含着用法律解释事实和用事实解释法律之两面。刑法解释者作为解释主体与具有两面性关联的刑法解释对象(法律和事实)之间的主客体性活动,最终形成法律规范匹配于案情事实、案情事实匹配于法律规范的两面性匹配,从而得出合法、客观、合理的刑法解释结论。
刑法解释的主客观性(命题),又称为刑法解释的二重性(命题),是指刑法解释作为法律解释兼有主观性与客观性之二重性,其主观性表现在解释者带有“前见”和目的进行解释、解释的结果具有个性和倾向性,其客观性表现在解释活动不能离开法律文本并且必须以法律文本为基础和为解释对象、解释者的“前见”和目的不是纯个人的和偶然的而是与时俱进的并且受制于“法律解释共同体”的、解释的标准是客观的并且要遵守相关规则。[57]因此,刑法解释二重性既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交织一体,也是刑法解释双向性的互动结果。
刑法解释的主客观性(命题)涉及刑法解释立场问题。刑法解释立场,主要有刑法的主观解释与客观解释之分、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之别,此外还有刑法的折中解释(具体包括刑法的主观解释与客观解释的折中论、刑法的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的折中论)作为“第三种”解释立场,[58]相关的学术之争仍然浓烈,其具体内容留待后文详述。
(四)合法性与正当性
刑法解释作为法律解释必须合法,以法律规范文本为解释对象、解释根据、解释限度,以法治理性为实质的法理基础,兼顾好刑法解释的过程和结论的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合法性是刑法解释的最基本原则,是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解释上的最基本体现,是刑法解释正当性的前提和基础,因而刑法解释必须特别强调合法性。
刑法解释作为法律解释的正当性意指合理性和可接受性,强调刑法解释的根据、内容和结论都必须是正当合理的。同时,为了实现刑法解释的正当性,刑法解释必须在严格审查刑法解释的根据、内容和结论的正当性的同时,谨慎权衡刑法解释各种要素之间的恰当关系,包括审查刑法解释的客观性与探究性、主客观性与主体间性之间的恰当关系,进行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全面周到的价值权衡,适当体现刑法解释的谦抑性,通过周全的法理论证以得出刑法解释的正当性。
应当说,刑法解释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命题)强烈关涉刑法解释限度问题。关于刑法解释限度(命题),理论界主要有如下三种学说:一是主张从法的犯罪定型中去寻求解释限度的犯罪定型说;二是主张从法律条文的语义中寻求解释限度的法文语义说;三是主张从一般人的预测可能性中寻求解释限度的预测可能性说。[59]我国学者对刑法解释限度(命题)有较多论述,但是还难说达成了一致见解。如有学者指出,刑法解释限度是刑法解释所能达到的具体、客观的程度和范围,应具有内在规范性、客观性与确定性的品质,应是质的限度与量的限度的统一体,是事实与规范关系性的限度;刑法解释限度的三种理论学说中,国民的预测可能性由于其自身的特征与独特的适用场域,并不符合刑法解释限度的特征标准,是不能作为刑法解释限度而存在的;法文语义理论由于所持的立场不同于刑法解释限度之立场,加之宽泛性与抽象性的缺陷以及自身限度的虚设性,使得其作为刑法解释限度不具有真正的合理性;犯罪定型才应作为解释限度予以真正对待,将犯罪定型作为刑法解释限度,完全符合刑法解释限度特征之要求,符合刑法规范整体性、系统性的特征,能够更好地处理犯罪定型与法文语义理论、预测可能性理论之间的关系。[60]我国另有学者指出,合理的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别并非在于思维模式或认识方法的不同 ,而是在于解释结论的差异 ,即解释结论是否超过了合理限度,衡量合理限度的标准是:通过扩大解释所包含进去的事项是否具有被解释的概念的核心属性;[61]刑法解释应当遵循罪刑法定主义,应被限定为在国民可预测范围内的“文义射程”。[62]再有学者指出,以考夫曼及其学生哈斯默尔为代表,从根本上否认“可能的字义”作为解释的界限,并坚持将类型代替“可能的字义”作为解释的界限;以埃塞尔为代表,并不全面否定“可能的字义”作为解释的界限,只是对此提出质疑;以拉伦茨为代表,完全站在通说的立场,对“可能的字义”作为解释的界限持肯定态度;按照法治的基本精神,必须保留“可能的字义”理论作为法律解释的界限。[63]可见,刑法解释限度(命题)仍然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刑法解释限度有其限定合法性与正当性价值诉求的预设语境,从中外学者立场看,“文义射程说”、“可能的字义说”和“法文语义说”在基本含义上应当说是大体一致的,都可以归结于语言哲学视野下的“语义”论。但是“语用”论值得重视,因为“根据语用哲学,语言意义产生于使用过程中,同样词汇由于语境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意义,原本的‘意义’是不存在的”,因此“根据主客一体哲学,没有客观存在的作品意义,任何文本的意义都是解释者视域和文本视域、古与今、传统与现实的融合,刑法文本也不例外”。[64]既然如此,笔者认为,语言意义并不能从纯粹的语义中获得而只能从语用和语境中获得,那么,刑法解释限度的寻求可能就有必要从语义论转向语用论,亦即在语用的功能意义及其在国民预测可能性的范围内寻求刑法解释限度,将法文语义说修正为“法文语用说”,并参考预测可能性说的合理成分,倡导一种“语用论的国民预测可能性说”(命题)。例如,陈兴良教授在分析“婚内强迫性行为”的定性处理时指出,“奸”的词源学考察业已表明“奸的原始含义是指婚外性行为”亦即“奸”的语义本来是婚外性行为、“婚内无奸”[65],但是按照强奸罪的立法原理、内在法理和人文理性的发展(论理解释),法解释论上可以并且应当将部分情节恶劣的“婚内强迫性行为”解释为强奸罪[66]。对此解释结论,从刑法解释限度范畴考察,“文义射程说”、“可能的字义说”和“法文语义说”均难以证成其合法性和正当性,但是“语用论的国民预测可能性说”(命题)则可以从刑法解释限度上获得合法性和正当性确证。
就刑法解释结论而言,法理学界认为,法律解释结论是指法律解释的结果,在存在论和认识论意义上,法律解释结果的多样性是正常的,“一方面是由文本本身的开放性多义性造成的,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事实对本文的影响所致”;但是在司法论上,“法官必须拿出一个判决标准,但根据法治原则,又不能任意拿出一个标准。这就凸显出了法律论证的必要性。也就是说法官应经过综合论证(包括合法性、合理性、合事物本质的论证等)来确定一种可接受的解释结果。这种可接受的结果,不能是多解,而必须是一解,否则法官无法阐明判决的标准。当然,这种可接受的结果也很可能是多解结果的综合,但一旦综合,我们不能称之为多解,而只能是一解”;而且“正是在多解事实与一解的追求目标的不断循环中,相对正确裁判标准才能出现”。[67]因此,刑法解释结论,是指刑法解释的结果。“我们必须牢记,刑法解释的核心、出发点和归宿点均在于保障人权,因为我们维护社会秩序价值本身的终极目标恰恰也在于保障人权。‘人权自由最大化与必要社会秩序最低限度化’是一对紧张关系,在相当意义上是终极目标与必要手段的关系,应当以终极目标为核心、出发点和归宿点。因此,在具体个案中,不同的解释立场和解释方法可能会得出不同结论,这时就必须注意解释结论的保守性,即寻求倾向于保障人权机能的价值目标权衡的结论。刑罚的最后手段性、不得已性、谦抑性,正是这种解释结论的保守性的深刻表达,亦即:可定罪可不定罪时,解释结论应当是不定罪(不逮捕、不定罪、不判刑);可免除处罚可不免除处罚时,解释结论应当是免除处罚;可缓刑可不缓刑时,解释结论应当是缓刑;可杀可不杀时,解释结论应当是不杀,等等。”[68]可见,刑法解释结论的最终得出,必须是通过刑法解释的综合性法律论证,根据刑事法治原则对多种刑法解释结果进行综合权衡之后得出的可接受的一种解释结果。
(五)方法性与目的性
刑法解释作为法律解释必须全面兼顾法律解释的本体论与方法论,本体论上在全面关注刑法解释的两面性(即用法律解释事实和用事实解释法律的两面性)、双向性(即解释者与法律文本的双向互动性)、二重性(即主观性与客观性)、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同时,合理审查、适当筛选并谨慎运用特定的法律解释方法,以充分体现刑法解释的方法性。例如,刑法解释的方法性审查中,要注意充分运用法律解释的循环性与自主性以及通常的解释方法与解释规则,还要注意刑法解释方法论上的特殊性。法律解释的循环性又称为循环性原则、语篇原则,是指“语词的意义必须在句子中把握,句子的意义必须在文本的整体中来把握,而文本的整体意义则必须通过对组成文本的个别句子、语词的准确理解而得到把握。解释者必须往还穿梭于部分和整体之间,最终达到对法律概念、法律规范和法律精神的准确理解”[69],对法律文本的理解是句子决定意义而不是语词决定意义,并且在句子也未必能决定法律的意义的时候,需要对文本的整体与部分之间来回循环——包括施莱依马赫所说的在理解过程的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循环,以及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所提倡的从结果逆向回溯到开头的循环(流程)——才能达到最终的理解。[70]法律解释的自主性是指贝蒂的解释学理论中的自主性整合的学说,是指在法律出现漏洞、模糊或者矛盾的时候,如果运用类推方法仍然不能解决问题,则在一般法律原则中寻求可作为判准的异质整合法则;但是,解释的自主性并不是说解释者可以任意解释,相反自主性解释主张一种受道德和法律约束的解释,强调法官必须不受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影响或者政治团体的影响(司法独立的要求),法官必须听取他们可能不愿意听取的冤屈以及所有将受判决影响的人的意见(利益相关人的规定),法官必须对所作出的判决承担个人责任(署名规则的传统),法官必须用普遍的术语阐述其判决的合理性(中立原则的要求),同时解释的自主性还意味着法官不能尊奉教条主义的解释学。[71]关于法律解释的方法(构成要素、标准或者根据),法律解释学上有语义解释、逻辑解释、历史解释和目的解释的概括,[72]也充分说明了法律解释的方法性。那么,刑法解释的方法性,不但必须得到充分的、必要的强调,同时还必须审查一般法律解释原理中哪些具体的解释方法和规则在刑法解释中所具有的合理性及其特别限定,如前所述一般法律解释的方法论内容中的“类推”、异质性整合法则,有的方法论内容就可能因为其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实质正当性而不能简单运用于刑法解释之中,这些问题就成为刑法解释的方法性的特殊性。
刑法解释作为法律解释的目的性,相对于一般法律解释的目的性而言,可能具有一定特殊性。如果说一般法律解释的目的,是解决社会纠纷、建立和维护法律秩序、续造法律并使得法律获得新生[73],那么,刑法解释的目的性就只能是解决作为社会公共政策问题的刑事犯罪问题、维护刑事法律法治秩序和保障人权。在刑法解释的目的性中,在相当意义上是没有“续造法律并使得法律获得新生”的存在空间的,因为维护刑事法治秩序和保障人权本身,就要求不得通过刑法解释“续造法律”,更必须反对解释入罪(司法上犯罪化)。如果刑法规定存在漏洞,正确的处理方式只能是罪刑法定原则所要求的“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原则上不得通过刑法解释来堵塞刑法立法上的漏洞,司法上作出“无罪处理”、仅准许立法填补刑法漏洞是解决刑法立法漏洞的基本立场。
三、刑法解释的类型分析
刑法解释的类型论,应当借鉴吸纳法理学关于法律解释的类型论知识,结合作为部门法解释学的刑法解释学自身特点进行适当的分类。从西方法律解释学术史考察,萨维尼在区分法律解释的种类与构成要素的基础上指出,法律解释的方法只有文法解释与逻辑解释两种方法,而法律解释的构成要素有文法要素、逻辑要素、历史要素和体系要素四个方面。[74]拉伦茨提出“法律解释的标准(或者依据)”,认为法律解释的标准有字义、逻辑、历史、目的、宪法五个方面,此五方面的关系是互相支持、相辅相成和联结为一体的,其中语义分析(字义分析)是基础并且“构成解释的出发点,同时为解释的界限”,然后从逻辑、历史和客观目的几个不同的角度进行解释,从而使解释更全面、更准确。[75]我国有学者认为,萨维尼和拉伦茨针对法律解释的“构成要素”、“标准”或者“根据”的讨论,具有法律解释的分类意义,萨维尼提出的四点中“体系”也是逻辑问题,因而实际上可以概括为三点:文法解释、逻辑解释(即体系解释)、历史解释;而拉伦茨提出的五点中“宪法”所讲的只是目的中的“位阶者更显重要”,因而实际上可以概括为四点:语义解释、逻辑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论解释(含合宪性解释)。[76]我国有学者还进一步指出,萨维尼作为法律方法论的奠基者所提出的迄今仍被奉为经典的制定法解释方法论是“四分法”(经典四分法),即文理的或语言学的解释、伦理的或体系的解释、主观的或历史的解释、客观的或目的论解释,并且德国学者考夫曼也认为法律解释方法论“四分法”是自萨维尼以来法律解释学的经典见解。[77]我国法理学者在借鉴吸纳西方法理学关于法律解释的分类理论的基础上,对法律解释的分类既有繁简之分,也有内容之别。如陈金钊认为,法律解释方法可以分为文义解释方法、价值衡量解释方法、目的解释方法、社会学解释方法四种,其中“文义解释是法律解释的最基本方法”[78];而按照诠释所追求的客观性的来源看,法律解释方法可以分为文义的方法(即在法律文本中追寻客观性的方法)与文本外追求客观性的方法两种。[79]再如严存生教授认为,法律解释的分类可以从四个方面或角度进行,包括语义解释、逻辑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四种(四分法),并且“应有个先后秩序和轻重关系,即语义解释、逻辑解释、历史解释、目的和事理解释,越往后越重要”,前两者属于形式标准和浅层次标准,后两者属于实质标准和深层次标准,因此,一方面要尊重文本、从文本出发、不妄加己意,另一方面又不能仅限于字义和逻辑、不能仅仅停留于法律文本,而是要不完全受文本的束缚并且在必要时可跳出文本、有所创新和突破并给文本加添内容,要尊重“事实”(历史的和现实的事实);总体立场是“客观实际需要第一,文本第二。从文本出发,但不局限于文本,不搞文本至上”[80],这样才能使“解释”不变为文字的考证,才能通过“解释”揭示法律的现代意义和服务于实际的需要。
从中外法理学界对法律解释的分类问题的讨论来看,获得较多学者认同的看法是(传统)经典四分法,即主张法律解释可以分为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论解释四种;此外,法律解释的分类也可以简单化地分为文义解释与论理解释两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上列讨论所及的法律解释的分类,主要是指法律解释的“构成要素”、“标准”或者“根据”意义上的讨论,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意义上的讨论值得关注。如,根据法律解释的立场,法律解释的分类有主观解释与客观解释;根据法律解释的主体及其效力,法律解释的分类有有权解释(有法律效力的解释)与无权解释(无法律效力的解释或者学理解释)等。
刑法解释的分类存在较为复杂的情况,不同刑法学者提出的刑法解释分类看法差异较大,有的较为遵循法理学上法律解释分类的基本原理,有的则另辟蹊径自行其是地提出种类繁多的刑法解释分类观点,值得刑法解释学者深入反思检讨。
类似于法理学关于法律解释的分类标准,刑法解释学关于刑法解释的分类标准通常是指刑法解释方法的分类,对此,刑法学界的观点分歧较大、争议较多,具体见解有16种之多[81],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类分类法:(1)传统二分法,认为刑法解释的基本方法包括文义解释和论理解释两种,但是论理解释下面还包括若干具体的解释方法,[82]一般认为论理解释包括扩张解释、限制解释、当然解释、反面解释、系统解释、沿革解释、比较解释、目的论解释、合宪解释、社会学解释等。[83]其中,曲新久教授和张明楷教授各自提出的二分法有一定特殊性。曲新久教授提出的二分法是语义解释和系统解释,主张以语义解释为主,系统解释为辅。[84]张明楷教授在基本赞同传统二分法观点的基础上指出,传统二分法所列举的解释方法是极为有限的,例如人们常讲的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等在刑法理论的通说中都没有地位;为此,张明楷认为应当借鉴吸纳日本学者将刑法解释方法进行形式分类和实质分类、区分解释的参照事项与条文的适用方法的做法,将刑法解释方法具体区分为解释技巧与解释理由,即“将解释方法中的平义解释、宣言解释、扩大解释、缩小解释、反对解释、类推解释、比附、补正解释等(即条文的适用方法),称为解释技巧;将解释方法中的文理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比较解释、目的(论)解释等(即解释的参照事项),称为解释理由”。[85](2)三分法。有学者认为刑法解释方法有历史解释、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三种[86],或者认为刑法解释方法可以分为平意解释方法、想象重构解释方法和目的性解释方法[87]。(3)四分法。有学者认为刑法解释的方法主要有文意解释、历史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四种方法(同时还有当然解释、反面解释、比较解释等辅助方法)[88],或者认为刑法解释方法通常有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和目的解释四种[89],或者认为刑法解释方法通常有语义解释、逻辑解释、历史解释和体系解释四种[90],或者认为刑法解释方法可以主要归结为文义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和体系解释[91]。(4)五分法。有学者认为刑法解释的方法包括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和合宪性解释五种[92],或者认为刑法解释的主要方法包括文理解释、逻辑解释、历史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五种[93]。(5)其他多标准划分方法。如有学者认为,按照解释的方法是否单纯进行语义说明可以分为文理解释和论理解释;从解释方法主要从属的学科划分,可分为(自然)科学方法、社会科学方法、经济学方法、逻辑学方法和哲学方法;从解释的起点划分,可以分为实证方法与思辨方法。[94]
我们认为,上列学术见解主要是基于刑法解释方法的特点而对刑法解释进行的分类,即刑法解释方法的分类,这当然是刑法解释的分类中十分重要的一种情形;但是,除此之外,还可以根据刑法解释的立场、主体及其效力等标准对刑法解释进行分类。因此,刑法解释的分类大致可以进行以下三种分类:
(一)刑法解释立场:规范目标与规范属性
根据刑法解释的立场对刑法解释的分类,具体可以区分为两种立场并据以确定刑法解释的分类:一是根据刑法解释的规范目标的立场,刑法解释的分类主要有刑法的主观解释与客观解释(二分法),此外还有刑法的折中解释(刑法的主观解释与客观解释的折中论)作为“第三种”解释立场;[95]二是根据刑法解释的规范属性的立场,刑法解释的分类主要有刑法的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二分法),此外还有刑法的折中解释(刑法的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的折中论)作为“第三种”解释立场。
刑法的主观解释,又称为意志论、主观论、主观说、立法者意思说,主张在解释立场上坚持以探求立法者制定法律时的真实意思、立法原意与立法本义为解释目标,并以此解释目标作为判断解释结论的正当性的标准。在“刑法的立法原意与立法本义”的意义上,主观解释论还可以成为立法原意说、立法本义说。主观解释论有其特定的哲学基础、政治理论基础和法理基础。[96]刑法的主观解释论的法理基础是强调刑法的安定价值和人权保障机能(同时也需要适当兼顾秩序维护机能),突出强调在现行刑法规定之下应当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较为充分地体现了传统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
刑法的客观解释,又称为客观论、客观说、法律客观意思说,主张在解释立场上坚持以探求法律规定在解释适用时的客观意思和规范意义为解释目标。刑法的客观解释论的法理基础在于强调司法公正和秩序维护机能(但是并不公开反对人权保障机能),尤其强调在现行刑法框架之下确保法益保护和秩序维护的现实需要。
刑法的折中解释(刑法的主观解释与客观解释的折中论),又称折中说、折中论与综合解释论,是一种试图将主观解释论和客观解释论进行折中调和的解释立场。折中论的传统见解是指对刑法的主观解释与客观解释的机械折中或者综合运用,如我国台湾学者林山田即主张综合解释论,强调对于新近立法或者立法时间间隔不久的法律,采用主观说;对于立法时间间隔较长的法律,则“应着重客观意思,以为解释”。[97]还应注意的是,折中论内部还有一些细微差别,有的折中论者主张以主观解释论为基础兼而采客观解释论,如德国耶塞克、中国台湾林山田,另有的折中论者主张以客观解释论为基础而兼采主观解释论,如德国施罗特和拉伦茨。[98]
那么,中国刑法学者对刑法的主观解释、客观解释、折中解释之争的基本态度如何?有学者指出,中国刑法学者多数(以及中国法理学者多数)主张客观解释论,如陈兴良、陈忠林、张智辉、王政勋、刘艳红等;另有部分学者主张主观解释论,如王平、李国如、白建军、许发民等;也有部分学者主张折中论,如梁根林、张明楷等。[99]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有学者认为,就刑法解释立场而言,目前不但德日刑法解释立场是客观解释,而且中国也当然是客观解释,此点不存在争议或者说不应存在争议。如陈兴良教授和王政勋教授等学者明确主张客观解释并明确反对主观解释,认为这是中国的刑法解释应当坚持的立场和目标问题。[100]但是,另有学者考证指出,尽管德日等法治发达国家已经较多地主张采用刑法客观解释立场,但是,由于我国具有特殊国情,尤其是现阶段我国的法治基础薄弱,人治、专制传统过于强大,人权保障缺失严重,重刑思想根深蒂固等原因,因而我国现阶段不适宜完全采用客观解释论,并且外国和国外地区也有刑法学者主张折中说立场,这对于我国现阶段不宜完全采用客观解释论也提供了佐证。[101]我们认为,机械的折中说可能并不可行,我国应采取适当保守的刑法客观解释立场。[102]所谓保守的刑法客观解释,是指基于罪刑法定原则而对刑法的主观解释和客观解释予以适当的价值权衡,秉持适当保守的刑法客观解释立场,对于“当下应定罪而没有定罪的立法规定”之情形,应从有利于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的特别考量出发,明确肯定刑法的主观解释因其有利于恰当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而具有的合理性,同时确认刑法的客观解释因其不利于恰当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而存在的不当性;对于“当下不应定罪而有定罪的立法规定”之情形,则应明确肯定刑法的客观解释因其有利于恰当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而具有的合理性,同时确认刑法的主观解释因其不利于恰当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而存在的不当性。[103]
刑法的形式解释,是指以罪刑法定原则为核心,主张在对法条解释时,先进行形式解释亦即对刑法条文字面可能具有的含义进行解释,然后再进行实质解释亦即对刑法条文规定的行为在性质上是否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实质进行解释。刑法的形式解释特别强调形式判断与实质判断的先后顺序,即在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先对行为进行形式解释并确定该行为是否包含于刑法条文之中,然后再作实质解释并确定该行为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104]
刑法的实质解释,是指刑法解释应以处罚的必要性为出发点,主张对法条解释时,首先应直接将不具有实质的处罚必要性的行为排除在法条范围之外,亦即首先实质地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属于具有处罚必要性的社会危害性行为进行判断,然后再进行形式解释并审查刑法条文的可能含义是否涵盖了该行为方式。可见,刑法的实质解释也特别强调形式判断与实质判断的先后顺序,与刑法的形式解释相反,刑法的实质解释在对行为进行解释时,强调应先从实质解释出发并审查确定该行为是否具有处罚的必要性,然后再进行形式解释并审查确定刑法条文的可能含义是否涵盖了该行为方式。[105]
刑法的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之争,是在相当意义上独具“中国特色的”刑法解释论之争。[106]我国刑法学界大约在21世纪之交开始出现刑法的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之争,这一学术争论常常也放置于更为广阔的形式刑法观与实质刑法观之争之中[107]。我国刑法学界甚至认为,关于刑法的形式解释(形式刑法观)与实质解释(实质刑法观)之争十分深刻并特别引人瞩目,[108]可以说是中国刑法学界开始出现所谓的“刑法学派之争”的一个重大事件。陈兴良教授较早关注到中国刑法学界出现的关于形式主义刑法学与实质主义刑法学之争这一学术现象,其中明确指出我国出现了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的区分,并且指出这是在德日刑法学中并未发生过的现象。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形式解释以陈兴良教授和邓子滨研究员等为代表,实质解释以赵秉志教授、张明楷教授、刘艳红教授和苏彩霞教授等为代表。赵秉志教授指出“在法解释学上,向有形式的解释论与实质的解释论学说之争”,认为“我国应确立实质的刑法解释论的立场”。[109]刘艳红教授针对刑法的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之争也进行了论辩,明确主张刑法的实质解释并反对刑法的形式解释。[110]邓子滨研究员则明确主张刑法的形式解释并反对刑法的实质解释,提出对于中国实质主义刑法观应当予以批判,而不是轻描淡写的批评。[111]陈兴良教授和张明楷教授于2010年同时在我国权威法学理论刊物上发表文章,各自系统地阐述了其所坚持的刑法的形式解释与刑法的实质解释的基本立场观点。[112]笔者曾经提出过应坚持保守的刑法实质解释(或者单面的实质解释)的学术见解,其中分析提出了激进的实质解释(或者双面的实质解释)可能存在严重侵犯人权的巨大风险的某种担忧并对激进的实质解释论进行了有利于充分实现人权保障机能并适当限缩秩序维护机能的某些修正,并主张应当适当吸纳形式解释的某些合理因素,因而可以说笔者在总体立场上主张应当兼顾吸纳刑法的实质解释和形式解释的合理内核,[113]而并非片面地主张刑法的实质解释或者刑法的形式解释。因此,笔者主张某种比较契合刑法谦抑性的谨慎的刑法的折中解释(刑法的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的折中论),亦即保守的刑法实质解释论,其与保守的刑法客观解释论一起共同形成刑法解释的保守性命题。[114]
在相当意义上,刑法的主观解释与刑法的形式解释之间存在较大的通融性,其优点在于有利于确保刑法解释的客观性和安定性,其不足之处在于过于死板僵化而无法适应社会发展变迁的需要,而且其推崇刑法的法条含义的主观化色彩和形式化色彩过于浓厚,在某些场合反而不利于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如对于“当下不应定罪而有定罪的立法规定”之情形)。同理,刑法的客观解释与刑法的实质解释之间也存在较大的通融性,其优点在于有利于确保刑法解释的客观化并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其缺陷在于过于实质化和价值判断化而易于侵蚀立法权并出现司法上犯罪化现象,而司法上犯罪化现象很容易形成刑事法治理性缺失并可能出现人权保障不足的重大风险。
正是为了恰当权衡兼顾刑法解释的人权保障机能和秩序维护机能,笔者提出了刑法解释的保守性命题,主张适当保守的刑法客观解释和刑法实质解释的立场。刑法解释的保守性命题有利于准确把握当下中国刑法的主观解释与客观解释之争、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之争的内核,主张合理权衡刑法的秩序维护与人权保障之间的价值紧张关系,以最终达致在适当照顾刑法的秩序维护机能的前提下尽力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以及个别公正、实质公正)的最佳价值权衡状态。因此,刑法解释的保守性命题特别注意区分不同情形以具体确认解释个案的妥当性问题:对于“当下应定罪而没有定罪的立法规定”之情形,刑法解释的保守性命题从有利于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的特别考量出发,明确肯定刑法的主观解释和形式解释因有利于恰当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而具有的合理性,同时确认刑法的客观解释和实质解释因不利于恰当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而存在的不当性;对于“当下不应定罪而有定罪的立法规定”之情形,刑法解释的保守性命题相应地明确肯定刑法的客观解释和实质解释因有利于恰当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而具有的合理性,同时确认刑法的主观解释和形式解释因不利于恰当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而存在的不当性。刑法解释的保守性命题有效契合了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谦抑性的基本要求,有利于具体恰当地解决刑法疑难案件的定罪量刑问题,获得了较多刑法学者的认同,具备刑法解释学意义上的充分的正当性。[115]
(二)刑法解释方法:传统经典四分法与新经典三分法
如前所述,传统的观点认为,根据刑法解释的方法,刑法解释的(方法)分类有文义解释(语义解释)、体系解释(逻辑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四种刑法解释方法。刑法解释方法的这种四分类,不但符合法理学对法律解释方法的分类原理,也符合德国刑法学对刑法解释方法的分类原理,如德国权威刑法学教科书将刑法解释方法分为文理解释、体系解释(即逻辑解释)、历史解释和目的解释四种[116],堪称西方法律解释方法的(传统)经典四分法、刑法解释方法的(传统)经典四分法。
中国刑法学界总体上是比较认同西方法律解释方法的(传统)经典四分法的,但是中国刑法学者关于各种刑法解释方法的具体讨论可能并不完全同于西方而更具有“中国特色”,还有许多学术见解值得特别关注,需要进行专题性的详细论述,因而本文这里囿于篇幅限制而仅作如下简要归纳:(1)刑法的文义解释,又称刑法的语意解释、语义解释、文意解释、文理解释、文法解释、语法解释、语言解释、字面解释,是指根据刑法用语的文义及其通常使用方式阐释刑法用语含义的解释方法。刑法的文义解释,根据其相关性观察,还包括刑法的平义解释、当然解释等刑法解释方法。所谓刑法的平义解释,是指刑法用语的最平白的含义的阐释。有学者认为,平义解释一般是针对法律规定中的日常用语而采用的解释方法,但是对于专门的法律术语(如“故意”、“过失”等)则不宜采取平义解释方法,而只能按照刑法的解释性规定进行解释。[117]所谓刑法的当然解释,是指根据刑法用语含义可以当然得出的解释结论的解释方法。如刑法第236条“二人以上轮奸的”,其含义当然包括“三人轮奸的”情形。有学者认为,刑法的当然解释“蕴含了在出罪时举重以明轻、在入罪时举轻以明重的当然道理”[118];但是,“在入罪时举轻以明重”这种看法可能过于实质化、超规范化和类型模糊化,有时可能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应当谨慎地注意审查犯罪行为定型的特别规则。(2)刑法的体系解释,又称刑法的逻辑解释、系统解释,是指根据刑法用语在刑法典中所处位置及其与其他法条、与整体法体系的相关性,系统地、逻辑地阐释其含义的解释方法。刑法的体系解释(逻辑解释)强调刑法解释“整体只能通过对其各部分的理解而理解,但是对其各部分的理解又只能通过对其整体的理解”[119],意在防止对刑法用语的断章取义和不协调。[120]刑法的体系解释(逻辑解释),根据其相关性观察,还包括刑法的反面解释(反对解释)。所谓刑法的反面解释,又称刑法的反对解释,是指根据刑法条文的规定内容,推导其反面含义的解释方法。(3)刑法的历史解释,又称刑法的沿革解释,是指根据刑法制定与实施的历史背景、演进沿革来阐明刑法条文的含义的解释方法。(4)刑法的目的解释,又称刑法的目的论解释、刑法目的解释,是指根据刑法规范的保障人权和维护秩序的双重目的的指引,具体阐明刑法条文的含义的解释方法。鉴于法理学上“目的解释”的复杂性与刑法学上“刑法规范目的”的立体性,中国刑法学者关于刑法目的解释的界定存有较大分歧和争议。有学者认为,刑法目的解释是根据刑法规范的目的阐明刑法条文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121];也有学者认为,刑法目的解释是“根据刑法立法之目的,阐明刑法规定含义的方法”[122];还有学者从刑法机能的角度出发,认为刑法目的解释是根据刑法规范所有保护法益的目的或实现的宗旨而作出的解释[123],或者直接提出“刑法的目的就是保护法益”[124]。对刑法目的解释的概念界定存在分歧,反映了刑法目的解释本身的复杂性。中国刑法学者注意到,德日刑法具有刑法解释的研究传统,目的解释尤为受到推崇,“解释方法的桂冠当属于目的论之解释方法……其他的解释方法只不过是人们接近法律意思的特殊途径”[125];刑法目的解释具有目的解释的一般特征,同时鉴于其解释对象的特殊性,又与其他部门法的目的解释具有鲜明的区别,日本学者就曾将刑法目的解释总结为:“目的论的解释,必须沿着作为法支配原理的罪刑法定主义这条线,从刑法具有的保护法益机能与保障人权机能一并考虑进去的合目的性来进行解释。依据这种目的论的解释,才不至于使刑罚法规局限在法律条文的文理解释,根据情况把在规定中能够包括的范围作扩张解释,或者作限制解释,据此调和现实的社会生活。”[126]应当说,德日刑法学中的刑法的目的解释对于我国刑法学界恰当界定我国的刑法的目的解释的概念具有启发借鉴意义。[127]其中,刑法规范目的的立体性可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但是恰恰经常性地被忽略的突出特点,因为刑法的罪刑法定条款(刑法第3条)以及其他众多刑法规范恰恰体现了刑法规范目的具有保障人权和维护秩序的立体目的性(双重目的性),而不是仅限于维护秩序之“单一”规范目的;同时,刑法规范目的的价值判断属性与认知本身也是十分微妙的,有主观目的论与客观目的论、立法目的论与司法目的论之争,从而进一步导致刑法规范目的的复杂化。这些情况表明,刑法目的解释的学理之争与解释学运用尚待进一步研究。再者,根据其相关性观察,刑法的目的解释可以包括具有刑法论理解释属性的全部解释方法,主要有刑法的扩张解释(扩大解释)、限制解释(缩小解释)、补正解释、合宪性解释、比较解释、社会学解释等刑法解释方法。所谓刑法的扩张解释,又称刑法的扩大解释,是指根据刑法规范目的及其他相关法理,对刑法用语的规范含义进行解释适用时作出大于其字面含义的解释结论的解释方法。所谓刑法的限制解释,又称刑法的缩小解释,是指根据刑法规范目的及其他相关法理,对刑法用语的规范含义进行解释适用时作出小于其字面含义的解释结论的解释方法。所谓刑法的补正解释,是指根据刑法规范目的及其他相关法理,对刑法用语的规范含义进行解释适用时对其字面含义作出补充和纠正的解释结论的解释方法。所谓刑法的合宪性解释,是指根据刑法规范目的及其他相关法理,对刑法用语的规范含义进行解释适用时对其字面含义作出合宪性审查说明并确定解释结论的解释方法。所谓刑法的比较解释,是指根据刑法规范目的及其他相关法理,对刑法用语的规范含义进行解释适用时对其字面含义进行比较法学审查说明并确定解释结论的解释方法。所谓刑法的社会学解释,是指根据刑法规范目的及其他相关法理,对刑法用语的规范含义进行解释适用时对其字面含义进行社会学原理审查说明并确定解释结论的解释方法。综上可以说,刑法解释方法的(传统)经典四分法一度获得了中国多数刑法学者的充分认可,在相当时期内业已成为中国刑法解释方法的(传统)经典四分法。其中,刑法的文义解释包括了刑法的文理解释、平义解释、当然解释等概念,其法解释论价值重在阐释论证并限定刑法规定的文义底线;刑法的体系解释包括了刑法的反面解释(反对解释)等概念,其法解释论价值重在阐释论证并限定刑法规定的文义逻辑体系和法理逻辑体系,因而兼有形式逻辑化的文义解释属性和实质体系化的论理解释属性;刑法的历史解释包括了刑法的沿革解释等概念,其法解释论价值重在阐释论证并限定刑法规定的历史精神和文化传统之法理,因而具有实质的论理解释属性;刑法的目的(论)解释包括了刑法的扩张解释(扩大解释)、限制解释(缩小解释)、补正解释、合宪性解释、比较解释、社会学解释等概念,其法解释论价值重在阐释论证并限定刑法规定的合目的性之法理,因而具有实质的论理解释属性。由此可见,在中国刑法解释方法的(传统)经典四分法中,除文义解释(方法)外,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论)解释均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完全具有或者部分具有)实质的论理解释属性,并且是以目的(论)解释为“桂冠”[128]、为“基本指导原则”和“最高准则”[129]、为典型、为中心来展开的法理论证的;这种学术观察归纳有助于我们认识刑法解释方法的二分法(即将刑法解释方法划分为文义解释方法与论理解释方法)的逻辑自洽性。
因此还有必要指出,刑法解释方法的(传统)经典四分法自引入中国开始从来都面临着争议、挑战和发展,中国刑法学者现在越来越多地推崇刑法解释方法的二分法和三分法,即如前所述将刑法解释方法划分为刑法解释的文义解释方法与论理解释方法(二分法),或者即将刑法解释方法划分为刑法解释的文义解释方法、论理解释方法、法社会学解释方法(三分法)。目前我国较权威的刑法学教材就采用了刑法解释方法的二分法(即将刑法解释的基本方法划分为文义解释与论理解释)[130]。而我国学者主张的刑法解释方法的三分法不但早已出现,而且应当说其在法理学界和部门学界均逐渐获得了相当充分的法理支持,如有的学者将刑法学理解释分为文理解释、法理解释和非法学解释三种[131],或者将刑法解释分为文理解释、论理解释和进化解释三种[132],或者分为范围性因素、内容性因素和控制性因素三类[133];再如法理学界杨仁寿、民法学界王利明等均认为,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文义解释、论理解释、社会学解释[134],并且王利明教授主张“原则上,狭义的法律解释应当从三个方面入手展开,即从确定文义可能包括的范围、探求立法目的、社会效果等考量。而这三个步骤既是法律解释的程序,也是法律解释方法运用的顺序”[135]。就刑法解释方法的二分法与三分法的比较法立场而言,应当说二者具有融贯一致的法理逻辑:在文义解释与论理解释的刑法解释方法的二分法基础上,由于论理解释还可以进一步区分为规范法理上的论理解释与非规范法理的刑事政策原理上的论理解释(刑事政策解释方法)两种,有的学者直接称之为法内的论理解释与法外的论理解释(或者非法学的解释方法),因此三分法是在首先确认了文义解释方法(在这一“点”上完全等同于二分法)之后才再对二分法之论理解释方法做出了进一步区分,即将论理解释方法进一步区分为“法内”的“规范”的解释说理(即狭义的论理解释)与“法外”的“超规范”的解释说理(即非法学解释、法社会学解释与刑事政策解释),将解释说理从“法内”的“规范”的层面扩大至“法外”的“超规范”的层面,这种“进一步区分”非常有利于更加周全、立体、深刻地阐释法解释结论的正当合理性,从而这种“进一步区分”具有十分重大的方法论意义。如此一来,刑法解释方法的二分法还可以根据其内在一致的法理逻辑而进一步细化划分为以下三种(新经典三分法):刑法解释的文义解释方法、论理解释方法(即狭义的论理解释方法、法内的论理解释方法、规范法理上的论理解释方法)与刑事政策解释方法(即广义的论理解释方法、法外的论理解释、法社会学解释方法、刑事政策原理上的论理解释方法或者刑事政策解释方法)。这里值得特别说明的是,所谓法社会学解释,或者非法学解释,是指运用社会学方法、统计学方法、经济学方法、伦理学方法等非法学方法来解释法律[136],在本源意义上适用于民法、刑法甚至宪法等部门法的解释,这是没有问题的;更深入、更具体的法理观察还可以发现,基于刑法上罪刑法定原则和刑事政策原理的特殊立场(这是除刑法外的其他部门法所不具备的特殊立场),在刑法解释的法理上确有必要将“法社会学解释(方法)”转化成“刑事政策解释方法”,因为刑事政策原理可以包容法社会学(刑法社会学)的全部内容,而法社会学原理却可能难以包容刑事政策原理(尤其是其中的罪刑法定等刑事政策价值理念),从而“刑事政策解释方法”这种称谓上的转换更加符合刑法解释论特质,更加具体而贴切,可以成为刑法解释方法的三分法中的一个“创新点”。如果说,法社会学解释(方法)意在运用“法外”的社会学原理解释法律,从而法社会学解释(方法)作为“法外”的非规范法理的论理解释方法就能够成为区别于作为“法内”的规范法理的论理解释方法;那么可以说,刑事政策解释方法作为运用“法外”的刑事政策原理解释刑法的论理解释方法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法社会学解释(方法)在刑法解释中的进一步具体化、特别化,是刑法解释方法中唯一区别于其他非刑事法律解释方法的、具有独占性和标签性的特别解释方法,并且刑事政策解释方法作为运用“法外”的刑事政策原理解释刑法的论理解释方法同样也能够成为区别于作为“法内”的规范法理的刑法解释的论理解释方法。可见,不但我国刑法学者所主张的刑法解释方法的二分法和三分法有具有融贯一致的法理基础和逻辑自洽性,尤其是刑法解释方法的新经典三分法,即将刑法解释方法分为刑法解释的文义解释方法、论理解释方法、刑事政策解释方法三种,有力地契合了功能主义刑法观所内在要求的刑法解释方法的功能性类型化划分和功能性体系化定位,具有更细密周全的法理逻辑性、更强大有效的理论解释力,已经顺理成章地逐渐成为中国十分有力的学术见解,值得推崇和倡导。关于刑法解释方法的新经典三分法(命题),有两点必须加以补充强调:其一,其之所以可以被称为“经典”(经典三分法),是因为如前所述,其业已获得法理上较为充分突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业已获得我国法理学界尤其是刑法和民法等部门法学界较多较权威学者的充分肯定,如赵秉志、陈兴良、杨仁寿、王利明等均主张和认同新经典三分法。其二,刑法解释方法的新经典三分法命题之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刑法解释方法的功能性类型化(命题)与刑法解释方法的功能性体系化(命题)两个子命题,并且完全聚焦于刑法解释方法对于刑法解释结论所具有的独特限定功能,即各种刑法解释方法的独特功能是有利于具体限定并得出更为科学合理的刑法解释结论:刑法的文义解释方法,具有文义上确定刑法解释结论的底线功能(文义解释功能);刑法的论理解释方法(狭义的论理解释方法),具有规范法理上限定刑法解释结论的合理性功能(论理解释功能);刑法的刑事政策解释方法(广义的论理解释方法),具有刑事政策上特别校正刑法解释结论的正当性功能(刑事政策解释功能),依次从底线功能、合理性功能、正当性功能逐级限定刑法解释结论的妥当性和可接受性。
但是毋庸讳言,中国刑法解释学界关于刑法解释方法体系化命题的争议还很大,有否定说、肯定说与折中说的不同见解。否定说的观点认为,刑法解释方法的体系化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行的、不符合刑法解释客观实际的,我国刑法学者张明楷教授[137]、周光权教授[138]、林维教授[139]、劳东燕教授[140]等坚持否定说;肯定说的观点认为,刑法解释方法的体系化是必要的、可行的,我国刑法学者赵秉志教授[141]、李希慧教授[142]、陈兴良教授[143]、梁根林教授[144]、时延安教授[145]等坚持肯定说;折中说的观点认为,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排序中既要考虑文义解释的优先性,又不宜肯定各种解释方法之间具有“固定不变的位阶性”,我国刑法学者李国如认同折中说[146]。笔者主张和倡导刑法解释方法的新经典三分法(命题)、刑法解释方法的功能性类型化(命题)与刑法解释方法的功能性体系化(命题),本文只是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命题概要,更为周详具体的法理论证已有另文[147]专述。
文末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学者认为,中国刑法解释的分类有一些特殊之处值得注意,即根据法律解释的主体及其效力,刑法解释的分类有立法解释(文本)、司法解释(文本)与学理解释(传统三分法)[148],这是中国刑法解释的特有分类,应当说其大体是有道理的,但是其中可能遗漏了法官的刑法解释则有失妥当。因此,中国刑法学者中更为严密的观点认为,根据刑法解释的主体及其效力,中国刑法解释的分类可以分为刑法的有权解释与刑法的无权解释(学理解释),其中刑法的有权解释还可以再分为刑法立法解释(文本)、刑法司法解释(文本)、刑法法官解释。刑法的有权解释,又称为有法律效力的刑法解释,是指由国家法律规定或者认可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刑法解释,包括刑法的立法解释(文本)、刑法司法解释(文本)、法官刑法解释(过程和结论)。刑法的立法解释(文本),是指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法所作出的刑法解释文本。刑法的司法解释(文本),是指由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即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简称“两高”)依法所作出的刑法解释文本。根据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第6条规定,司法解释的文本形式分为“解释”、“规定”、“批复”和“决定”四种。不过在实践中,“两高”的司法解释文本,既有“解释”、“规定”、“批复”和“决定”四种法定形式的司法解释文本,也有“意见”、“纪要”、“答复”等形式冠名的更具有刑事法“软法”[149]性质的司法解释文本,因此在广义和实质意义上“两高”的司法解释性文本的含义更加广泛。[150]法官刑法解释,是指法官在依法对个案进行司法裁判时所作出的刑法解释,包括法官的刑法解释活动全过程及其得出的刑法解释结论。在相当意义上,我国刑法学者所提及的法官的刑法解释正是西方法律解释学意义上的刑法解释。刑法的无权解释,又称为无法律效力的刑法解释、刑法学理解释,是指由无法定解释权的主体所做出的、不能直接产生法律效力的刑法解释(行动和结论)。刑法的无权解释主要是指刑法学理解释,即由无法定解释权的法学专家或者其他公民所作出的学理探讨性的刑法解释(行动和结论)。刑法的无权解释是相对于刑法的有权解释而言的,当某种学理解释获得了国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或者具体个案中法官的采纳与认可时,该学理解释即可转化成有权解释并获得法律效力。无论是刑法的有权解释或者无权解释,均必然采用一定的解释立场和方法,其内容已如前所述,不再赘述。
Legal Theory of the Fundamental Category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Criminal Law
——Some Important Propositions of "Interpretation of Criminal Law"
Wei Dong
(Sichuan University Law School)
【Abstract】The interpretation of criminal law refers to the understanding, clarification and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the meanings of the criminal law, which has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including judicial applicability, bi-directionality and inter-subjectivity, duality and subjectivity-objectivity, legality and legitimacy, method and purposiveness, etc. The function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criminal law means the values and functions of it, which reflect in the pragmatic of criminal law. The types of interpretation of criminal law can be analyzed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According to the position of normative goals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criminal law, the classification of it mainly includes the subjective interpretation of criminal law and the objective interpretation of criminal law. According to the normative attribute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criminal law, there are mainly formal interpretation of criminal law and substantive interpretation of criminal law.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criminal law, there are four methods (traditional classic quartering), in particular contains literal interpretation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logical interpretatio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and tel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classic quartering has always been facing controversy, challenge and has been developing since its introduction into China. Chinese criminal law scholars are now increasingly advocating that the method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criminal law ought to be divided into the literal interpretation, logical interpretation and the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collectively known as new classic trichotomy), which gradually become the theory consensus, because of the more rigorous and comprehensive legal logic, as well as more powerful and effective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Key words】Interpretation of Criminal Law; Judicial Applicability; Dogmatics of Interpretation of Criminal Law; Classic quartering;New Classic Trichotomy
* 本文系作者所承担的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点课题《刑法解释原理与实证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课题批准号:12AFX009。
** 魏东(1966—),男,法学博士,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刑事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1] 陈金钊、焦宝乾等:《法律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2] 参见严存生:《西方法哲学问题史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583-585页。
[3] 参见严存生:《西方法哲学问题史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587-589页。
[4] 参见张志铭:《法律解释原理》,载朱景文主编:《法理学专题研究》(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35-478页。
[5] 张志铭:《法律解释原理》,载朱景文主编:《法理学专题研究》(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35-478页。
[6] 周永坤:《法律学——全球视野》(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94页。
[7] 高铭暄主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1页。
[8] 胡新主编:《新编刑法学 总论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页。
[9] 金凯、章道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简明教程》,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
[10] 杨春洗等:《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1页。
[11] 杨敦先、张文:《刑法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9页。
[12] 李希慧:《刑法解释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9-49页。
[13] 赵秉志、陈志军:《论越权刑法解释》,载赵秉志、张军主编:《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2003年度)第一卷:刑法解释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195页。
[14] 徐岱:《刑法解释学基础理论建构》,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19页。
[15] 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上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5页;赵秉志主编:《刑法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16] 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
[17] 张明楷:《刑法学(上)》(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8-30页。
[18] 陈忠林:《刑法的解释及其界限》,载赵秉志、张军主编:《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2003年度)第一卷:刑法解释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57页;袁林:《以人为本与刑法解释凡是的创新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
[19] 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上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5页;赵秉志主编:《刑法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20] 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
[21] 牛克乾:《刑事审判视野中的刑法解释与适用》,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4-8页。其中,牛克乾法官指出,适用性刑法解释可进一步分为侦查人员适用性刑法解释、公诉人员适用性刑法解释与法官适用性刑法解释。
[22] 参见严存生:《西方法哲学问题史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585-586页。
[23] 参见陈金钊、焦宝乾等:《法律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8页。
[24] 参见陈金钊:《法律解释学——权利(权力)的张扬与方法的制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8-132页。
[25] 参见陈金钊、焦宝乾等:《法律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8页。
[26] 参见李希慧:《刑法解释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9-54页。
[27] 参见徐岱:《刑法解释学基础理论建构》,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22-125页。
[28] 参见徐岱:《刑法解释学基础理论建构》,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14-118页
[29] 参见李希慧:《刑法解释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0页。
[30] 参见严存生:《西方法哲学问题史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585-586页。
[31] 张明楷:《立法解释的疑问》,载《清华法学》2007年第1期。
[32] 曲新久:《刑法解释的若干问题》,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33] 参见魏东主编:《中国当下刑法解释论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6-7页。
[34] 参见苏力:《反思法学的特点》,载《读书》1998年第1期。
[35] 参见魏东主编:《中国当下刑法解释论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36] 徐岱:《刑法解释学基础理论建构》,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75页。
[37] 参见赵秉志、陈志军:《论越权刑法解释》,载《法学家》2004年第2期。
[38] 参见王季秋:《论刑法解释的若干问题》,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04年印制,第9-18页;杨艳霞:《刑法解释的理论与方法:以哈贝马斯的沟通行为理论为视角》,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82-186页。
[39] 魏东:《刑法解释保守性命题的学术价值检讨——以当下中国刑法解释论之争为切入点》,载《法律方法(第18卷)》,法律出版社2015年12月版,第220-236页。
[40] (德)魏德士:《法理学》,吴越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48页。
[41] 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第5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77页。
[42] 王利明:《法律解释学导论——以民法为视角》(第2版),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546-566页。
[43] 任彦君:《论我国刑法漏洞之填补》,《法商研究》2015年第4期,第106页;魏东:《从首例“男男强奸案”司法裁判看刑法解释的保守性》,载《当代法学》2014年第2期;邹治:《法律漏洞的认定与填补——司法的研究视角》,中国政法大学2008年度博士学位论文,第24页。
[44] 魏东:《从首例“男男强奸案”司法裁判看刑法解释的保守性》,载《当代法学》2014年第2期。
[45] 王勇:《论我国<刑法>第147条的罪过形式——基于刑法立法的解读》,《法学杂志》2011年第3期。
[46] 魏东主编:《刑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15页。
[47] 陈兴良:《刑法教义学的发展脉络——纪念1997年刑法颁布二十周年》,载《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3期。
[48] 参见林维:《刑法解释的权力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81页。
[49] 陈兴良:《序》,载林维:《刑法解释的权力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序”第1-6页
[50] 林维:《刑法解释的权力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页。
[51] 参见陈金钊:《法律解释的哲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6-57页。但是我国法理学界关于法律解释的对象似乎还有争议,大体有三种观点:一是法律规范或者法律条文与附随情况说,二是法律规范或者法律条文说,三是法律规范或者法律条文与法律事实说。参见杨艳霞:《刑法解释的理论与方法——以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为视角》,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78页。
[52] 罗豪才、宋功德:《软法亦法——公共治理呼唤软法之治》,法律出版社2009年11月版,第358页。罗豪才和宋功德在该书中指出:“软法”,是指与国家权力机关依法制定的“硬法”相对的、原则上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有实际效力的行为准则,既包括政策、章程、内部通知、指导性规则、官场潜规则,又包括那些“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有实际效力”的道德、伦理、风俗、习惯等社会行为规则。
[53] 参见魏东主编:《中国当下刑法解释论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9-10页。
[54] 聂立泽、庄劲:《从“主客间性”到“主体间性”的刑法解释观》,载《法学》2011年第9期。
[55] 姜涛:《基于主体间性分析范式的刑法解释》,载《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1期。
[56] 袁林:《超越主客观解释论:刑法解释标准研究》,载《现代法学》2011年第1期。
[57] 参见严存生:《西方法哲学问题史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585-586页。
[58] 参见赵秉志主编:《刑法总则要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80-95页;王政勋:《刑法解释的语言论研究》,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60-210页;徐岱:《刑法解释学基础理论建构》,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38-140页;赵运锋:《刑法解释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17-131页。
[59] 参见(日)关哲夫:《论禁止类推解释与刑法解释的界限》,王充译.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7页。.
[60] 参见龚振军:《刑法解释限度理论之关系论纲》,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年第4期。
[61] 参见刘志远:《刑法解释的限度——合理的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分》,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62] 参见蒋熙辉:《刑法解释限度论》,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4期。
[63] 参见王祖书:《法诠释学视域内“可能的字义”界限理论之反思》,载《北方法学》2015年第1期。
[64] 王政勋:《刑法解释的语言论研究》,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09-210页。
[65] 陈兴良:《婚内强奸犯罪化:能与不能——一种法解释学的分析》,在《法学》2006年第2期。
[66] 魏东:《刑法各论若干前沿问题要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135页。
[67] 参见陈金钊、焦宝乾、桑本谦、吴丙新、杨建军:《法律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6页。
[68] 魏东主编:《中国当下刑法解释论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69] 陈兴良主编:《刑法方法论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页。
[70] 陈金钊:《法律解释学——权利(权力)的张扬与方法的制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2页。
[71] 参见陈金钊:《法律解释学——权利(权力)的张扬与方法的制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4-125页。
[72] 参见严存生:《西方法哲学问题史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586-587页。
[73] 参见严存生:《西方法哲学问题史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585-586页。
[74] 参见严存生:《西方法哲学问题史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567-568页。
[75] 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00-221页;严存生:《西方法哲学问题史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582-583页。
[76] 参见严存生:《西方法哲学问题史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586-587页。
[77] 参见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页。值得注意的是,青年法理学者姜福东博士认为,萨维尼所提出的“经典法律解释学说里的法律解释包括了语法、逻辑、理事和体系等四项要素”,其中“体系”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体系”包括了外在形式逻辑体系和内在目的价值体系,而狭义上的“体系”是仅指内在目的价值体系。参见姜福东:《法律解释的范式批判》,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0页、第260-275页。
[78] 参见陈金钊、焦宝乾、桑本谦、吴丙新、杨建军:《法律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8页。
[79] 参见谢晖、陈金钊:《法律:诠释与应用——法律诠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页。
[80] 参见严存生:《西方法哲学问题史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587页。
[81] 参见李希慧、龙腾云、邱帅萍编著:《刑法解释专题整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37页。
[82] 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7版,第24页;赵秉志主编:《刑法新教程》(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版,第24页;魏东主编:《刑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10-11页。
[83] 参见王政勋:《刑法解释的语言论研究》,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94页。
[84] 参见曲新久:《刑法严格解释的路径》,载《人民法院报》2005年3月16日理论版。
[85]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五版)(上),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5版,第33-42页。
[86] 孙晋琪、蒋涛:《论刑法司法解释方法》,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87] 周光权:《刑法诸问题的新表述》,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312-316页。
[88] 姜伟、卢宇蓉:《论刑法解释的若干问题》,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3年第6期。
[89] 陈琦:《我国刑法解释与刑罚目的的实现》,载《研究生法学》2009年第4期。
[90] 程啸:《刑法解释方法及位阶关系》,载《人民法院报》2005年2月23日理论版。
[91] 屈胜肖:《刑事审判中的法律解释》,中国政法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政法大学2006年印制,第13-18页。
[92] 黄文琼、张小玲:《论正当刑法解释的获得路径》,载《金卡工程》2009年第11期。
[93] 龚培华:《刑法解释理论的基本问题》,载《法学》2007年第12期。
[94] 参见赵秉志、曾粤兴:《刑法解释方法研究》,载赵秉志、张军主编:《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2003年度)(第1卷):刑法解释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2页。
[95] 参见王政勋:《刑法解释的语言论研究》,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60-210页;徐岱:《刑法解释学基础理论建构》,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38-140页;赵运锋:《刑法解释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17-131页。
[96] 许发民:《论刑法客观解释论应当缓行》,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第23卷、2010年第3卷),第165—191页,法律出版社,2010。
[97] 参见魏东:《保守的实质刑法观与现代刑事政策立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
[98] 参见王政勋:《刑法解释的语言论研究》,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71-72页。
[99] 参见王政勋:《刑法解释的语言论研究》,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72-77页。王政勋教授在该书第76页指出,“张明楷后来放弃了自己曾经坚持的折中说,转而认为刑法解释应坚持和客观解释论密切相关的实质解释立场。”
[100]陈兴良教授称:“在刑法解释的立场上,我是主张客观解释论的。但在刑法解释的限度上,我又是主张形式解释论的,两者并行不悖。其实,主观解释论与客观解释论的问题,在我国基本上已经得到解决,即客观解释论几成通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的指导性案例中,也明显地倡导客观解释论。”参见陈兴良:《形式解释论的再宣示》,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4期。
[101] 参见许发民:《论刑法客观解释论应当缓行》,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第23卷、2010年第3卷),第165—191页,法律出版社,2010。
[102] 参见魏东:《刑法理性与解释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页。
[103] 参见魏东:《刑法解释保守性命题的学术价值检讨——以当下中国刑法解释论之争为切入点》,载《法律方法(第18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12月版,第220-236页。
[104] 参见刘志刚、邱威:《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辨析》,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魏东:《刑法理性与解释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5页。
[105] 参见刘志刚、邱威:《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辨析》,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106]魏东主编:《中国当下刑法解释论问题研究——以论证刑法解释的保守性为中心》,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22-123页。
[107] 魏东:《论社会危害性理论与实质刑法观的关联关系与风险防范》,载《现代法学》2010年第6期。
[108] 典型表现是《中国法学》2010年第4期同时发表了著名刑法学家陈兴良教授和张明楷教授的争鸣文章:陈兴良:《形式解释的再宣示》,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4期;张明楷:《实质解释的再提倡》,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4期。
[109] 赵秉志主编:《刑法总则要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80-95页。
[110] 刘艳红教授称:“在陈兴良教授的建议下,出版时我将题目修改为目前的‘实质刑法观’”,见刘艳红:《实质刑法观》,第25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同时又强调“应倡导实质的刑法解释观”,见刘艳红:《走向实质的刑法解释》,第2页(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对此,陈兴良教授曾经强调说,在中国刑法学者中,刘艳红教授是当时公开声明坚持实质主义刑法观立场的唯一的一位刑法学者。参见陈兴良:《走向学派之争的刑法学》,载《法学研究》2010年第1期。
[111] 陈兴良教授在本书序中称:“甫见《中国实质刑法观批判》这一书名,就令人眼前一亮,似乎嗅到了扑面而来的学术火药味,但我还是为之叫好。……以‘批判’一词而入书名的,不仅法学界没有,人文社会科学界也极为罕见。”邓子滨:《中国实质刑法观批判》,第1页(序),法律出版社,2009。
[112]该两篇文章是:张明楷:《实质解释论的再提倡》,载《中国法学》 2010 年第 4 期;陈兴良:《形式解释论的再宣示》,载《中国法学》 2010年第4期。
[113]参见魏东:《保守的实质刑法观与现代刑事政策立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3-10页。
[114] 参见魏东:《刑法理性与解释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5页。
[115] 参见魏东:《刑法解释保守性命题的学术价值检讨——以当下中国刑法解释论之争为切入点》,载《法律方法(第18卷)》,法律出版社2015年12月版,第220-236页。
[116] 参见(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195页。
[117]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五版)(上),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5版,第39页。
[118] 参见张明楷:《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8页。
[119] 金克木:《比较文化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43页。
[120] 参见张明楷:《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4-145页。
[121] 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3页。
[122] 李希慧:《刑法解释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页。
[123] 参见肖中华:《刑法目的解释与体系解释的具体运用》,载《法学评论》2006年第5期。
[124] 张明楷:《刑法理念与刑法解释》,载《法学杂志》2004年第4期。
[125] [德]汉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页。
[126] [日]福田平、大塚仁编:《日本刑法总论讲义》,李乔、文石、周世铮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页。
[127] 参见田维:《刑法目的解释的基础理论考察》,载魏东主编:《刑法解释(第2卷)》,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76-96页。
[128] [德]汉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页。该书指出“解释方法的桂冠当属于目的论之解释方法……其他的解释方法只不过是人们接近法律意思的特殊途径”。
[129] 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5页。
[130] 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底2版,第24页。
[131] 赵秉志主编:《刑法解释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5页。
[132] 陈兴良:《刑事司法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403页。
[133] 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年版,第272-289页。
[134] 参见王利明:《法律解释学导论——以民法为视角》,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724-725页;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8页。
[135] 王利明:《法律解释学导论——以民法为视角》,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724-725页。
[136] 赵秉志主编:《刑法解释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13页。
[137] 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33-42页。
[138] 周光权:《刑法解释方法位阶性的质疑》,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5期。
[139] 林维:《刑法解释的权力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2-144页。
[140] 劳东燕:《能动司法与功能主义的刑法解释论》,载《法学家》2016年第6期。
[141] 赵秉志主编:《刑法解释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5页。
[142] 李希慧:《刑法解释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6页、第132-133页。
[143] 陈兴良:《刑法的知识转型(方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1页。
[144] 梁根林:《罪刑法定视域中的刑法适用解释》,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3期。
[145] 时延安:《刑法规范的合宪性解释》,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146] 李国如:《罪刑法定原则视野中的刑法解释》,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198-200页。
[147] 暂定另文标题是《刑法解释方法的体系化及其展开》,专题论述刑法解释方法体系化命题的基本内容。
[148] 参见赵秉志主编:《刑法新教程》(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版,第22-24页;魏东主编:《刑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10-11页。
[149] 参见钟凯:《论刑事法“软法”及其刑法解释意义》,载魏东主编:《刑法解释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72-85页;罗豪才、宋功德:《软法亦法——公共治理呼唤软法之治》,法律出版社2009年11月版,第358页。
[150] 参见李立众编:《刑法一本通》(第十一版),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第十一版前言”;孟庆华、王法:《“意见”是否属于刑法司法解释表现形式问题探析》,载《临忻市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