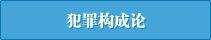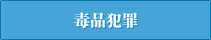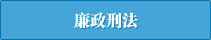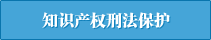桥爪隆:刑法总论之困惑(一)
【日】桥爪隆:《刑法总论之困惑(一)》,王昭武 译,载日本《法学教室》2014年 第4期。
编者按:日本东京大学桥爪隆(HASHIZUME Takashi)教授自2014年4月开始,以《刑法总论之困惑》为题,在日本《法学教室》(月刊)连载相关论文,对日本刑法总论中的部分难点,作了颇具个人色彩且具有相当理论深度的详尽论述。该连载每月一期,预计共十二期。蒙日本有斐阁出版社以及桥爪隆教授无偿转让版权,由苏州大学王昭武副教授翻译以飨读者,冀望能有助于我国刑法学界最快把握日本刑法学研究的当下动向与最新成果。鉴于本刊暂为季刊,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时效性,计划每期译载桥爪隆教授的两期连载。
作为危险之现实化的因果关系(1)
一、引言
对于刑法中因果关系的认定,传统通说持相当因果关系说;判例并未提出明确的判断标准,而是通过对具体案件进行实质性判断而逐步累积。一般认为,要认定存在因果关系,必须可以评价为,实行行为的危险性已通过结果而得以现实化(即结果实际实现了实行行为的危险性)。[1]在近年的最高裁判所判例中,对于“日航飞机危险接近[2]事件”(最决平成22年〔2010年〕10月26日刑集64卷7号1019页),最高裁判所认为,“本案危险接近,属于将本案的错误的下降指令的危险性予以现实化的情形,应该说,该指令与危险接近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里就明确使用了“危险的现实化”这一表述。[3]判例的这一立场得到学界的普遍支持,[4]甚至说“危险的现实化说”已经取得了学界通说地位,也并不夸张。
不过,就传统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与“危险的现实化说”之间的关系,仍有不少地方模糊不清。具体而言,相当因果关系说有哪些问题?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哪些地方经过修正之后,该说就可以接近“危险的现实化说”?这些都未必明确。为此,“危险的现实化说”究竟是完全不同于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全新学说,抑或不过是相当因果关系说的演变形式之一,对此尚无定论,从而也招致了理论上的混乱。
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有关危险的现实化的判断标准的学说之争,未必得到了充分的整理。只要是要求实行行为与结果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以存在法律上的关联性为必要,那么,就会要求是因实行行为的影响而发生了结果,也就是,要求是作为实行行为之危险的实现而发生了结果,那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其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因此,何种状况下应肯定实现了危险,对此问题的判断标准就不可或缺。当然,各种学说也充分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但仍然只是本能地使用诸如危险性、贡献度、异常性等关键词的倾向也并非不存在,因而有必要对这些概念的内容本身,予以进一步分析。
基于这种问题意识,本文意欲在分析相当因果关系说与危险的现实化说之异同的基础上,探究如何具体地判断“危险的现实化”。
二、传统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判断模式
(一)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基本内容
首先想简单梳理我国传统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基本内容。相当因果关系说主张,作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的内容,要求由行为引发结果这一进程具有社会一般观念上的相当性。其核心内容在于:(1)对相当性进行判断之际,在圈定属于判断之基础的相关情况(判断基础)的基础上,(2)以此为前提,判断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相当性。对于“判断基础”,长期以来存在激烈论争,现在主要是折中说与客观说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对立(根据论者的不同,也可能出现观点的某种变异):[5]折中说认为,应以一般人有认识或预见之可能的情况以及行为人本人特别认识或预见到的情况作为判断基础;[6]客观说主张,应以行为当时客观存在的所有情况以及行为后所发生的情况中有预见之可能的情况作为判断基础。[7]
原本来说,相当性存在与否的判断标准应该是更为重要的问题,但与学说之间的上述激烈对立相反,学界对该问题未必进行了充分的论争。而且,对于相当性的判断对象,学说是否有意识地进行了研究,也不无疑问。也就是,这里所谓“相当性”,究竟是指从实行行为到结果发生的因果进程本身应该具有相当性(通常性),还是说姑且不论因果进程的内容本身如何,只要是由实行行为引起该结果之发生是相当的即可(引起结果的相当性)呢?采取的观点不同,因果关系的判断模式也会随之不同,但两者之间的区别未必得到了明确。[8]可以说,这也是造成其后的研究状况混乱的原因之一。
(二)基于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因果关系之判断
1.介入了被害人特殊情况的情形
不过,设定了判断基础之后再判断有无相当性这种判断模式,是否总是有助于判断因果关系呢?
这里想通过具体案例来进行论证。首先是这样一种情形:通常情况下不会发生结果,但由于被害人存在特殊情况,受其影响发生了结果。例如,行为人实施了用被子捂住被害人这种轻微的暴力,正常情况下,该暴力不会致人死亡,但由于被害人患有严重心脏病,最终因急性心力衰竭而死亡;而且,被害人患有心脏病这一点,对一般人而言,几乎是不可能认识到的情况。对于该案,最高裁判所的判例判定,行为人的暴力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最判昭和46年〔1971年〕6月17日刑集25卷4号567页〔老妇捂被事件〕)。按照客观说的观点,只要将行为当时业已存在的心脏疾病这一事实纳入判断基础,由本案暴力行为导致因急性心力衰竭而死亡这一结果,在经验法则上就是正常的,因而会支持判例结论,肯定存在因果关系。反之,若采取折中说,就应该将一般人无法认识到且行为人本人也未能认识到的情况从判断基础中排除出去,那么,这里需要考虑的是,假定性地排除了患有严重心脏病这一事实的被害人因本案暴力行为而死亡,该因果进程是否具有通常性,因而原则上会否定存在因果关系?可以说,在此类案件中,对于因果关系之有无的判断,判断基础就属于决定性标准。不过,这种“二阶段”的判断模式究竟有多大意义,对此不无疑问。因为,最终而言,是根据是否将被害人的特殊情况纳入判断基础而得出结论,这种以判断基础为前提所做的因果关系的相当性判断,不过是为了对已经显示的结论加以确认的一个过程而已。[9]
2.实行行为之后的介入情况
不同于上一种情形,对于在实行行为之后介入了某种行为的案件,围绕判断基础的观点对立就基本失去意义。首先是介入行为属于通常所能预想到的行为的情形。例如,对被害人施以猛烈暴力,结果造成被害人在逃离过程中因摔倒而受伤。在该案中,被害人为了免遭进一步的暴力而逃离,在逃离过程中摔倒,可谓之为具有通常性的情况,因而属于一般人所能预见的情况,无论是采取折中说还是客观说,都会将该事实纳入判断基础。因此,折中说与客观说都会肯定存在因果关系。那么,下面的批判意见就应该是有道理的:最终对于此类情形而言,由于介入因素属于正常情况,只要直接肯定存在因果关系即可,没有必要特意经过设定判断基础之后再判断有无相当性这种“二阶段”的判断进程。[10]
其次是介入行为属于一般不可能预见的事态的情形。例如,暴力行为致被害人轻伤,由于运送被害人的救护车遭遇严重交通事故,被害人受其影响而死亡。既然救护车遭遇严重交通事故对一般人而言是不可能预见的情况,无论是折中说还是客观说,都会将该情况排除在判断基础之外,因而这种情形也未能显现折中说与客观说之间的对立。并且,作为相当性的内容,按照重视因果进程之通常性的观点,当然会(不经过设定判断基础这一过程)否定存在因果关系的相当性;亦即按照重视引起结果之相当性的观点,只要将救护车遭遇交通事故这一情况排除在判断基础之外,也会以致人轻伤的暴力最终导致被害人死亡的结果这种情况极为罕见为由,否定存在因果关系。进一步而言,起初的暴力致使被害人身受危及生命的重伤的,又应如何处理呢?按照重视引起结果之相当性的观点,由于该暴力完全有可能导致死亡结果的发生,也许会认为,能肯定存在相当因果关系。[11]但是,按照这种理解,只要发生了引起结果的具体危险性,无论后面出现了什么情况,(只要不能否定条件关系)都会肯定存在因果关系。应该说,这并不妥当。学界一般认为,所谓属于因果关系之判断对象的结果,并不是指一般的、抽象的构成要件结果(人的死亡),而应该是指在具体状况之下所发生的结果。[12]因此,通常的理解应该是,即便起初实施的是严重的暴力行为,仍然可以认为,由暴力行为导致“因救护车遭遇交通事故而引起的死亡结果”这一结果的发生不具有相当性,因而应否定存在因果关系。由此可见,是否将行为之后的介入情况纳入判断基础,对于因果关系的判断具有决定性意义,最终仍然是认为,介入情况的异常性即因果进程的通常性属于决定性标准。
三、相当因果关系的危机与转变
(一)大阪南港事件与结果的抽象化
众所周知,“大阪南港事件”(最决平成2年〔1990年〕11月20日刑集44卷8号837页)表明,不能总是以因果进程的通常性作为重要的判断标准。该案案情大致如下:被告人对被害人施加暴力,致被害人因内因性高血压性颅内出血之后,将被害人置于大阪南港的某处材料堆放点而自行离去,次日凌晨,被害人因内因性高血压性颅内出血而死亡,但存在被害人在该材料堆放点因被第三者数次殴打头部,引起颅内出血扩大,稍微提早了死亡时间这种可能性。对于该案,最高裁判所判定:“在因犯人的暴力而形成了属于被害人之死因的伤害的场合,即便其后因第三者所施加的暴力而提早了死亡时间,仍能肯定犯人的暴力与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由此可见,即便是介入了第三者的故意犯罪行为的情形,判例仍肯定存在因果关系。判例正是通过这种判决而清楚地表明,即便因果关系存在异常性,[13]仅此尚不足以总是否定实行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这种情况被称之为“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危机”[14]。
如前所述,作为相当性的内容,有观点要求存在因果关系之通常性,按照这种观点,只要介入了第三者的故意的暴力行为,就应否定存在因果关系。[15]反之,在要求具有引起结果之相当性的观点看来,应通过考察由本案暴力行为所引起的被害人颅内出血而导致死亡结果发生这一进程是否具有相当性,对于该案,肯定被告人的暴力行为(被害人的死因由该暴力行为所引起)与具体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当然,通过考察死因、死亡样态、死亡时间等而具体地把握死亡这一结果,对于该案也可以这样理解:如果第二暴力行为提早了死亡时间,那么,原本应发生的死亡结果(A)与实际发生的死亡结果(B)就属于不同的结果,为此,即便由实行行为导致 A 发生具有相当性,但不能说,导致 B 发生也具有相当性。[16]然而,如果被害人的身体状况等条件不同,死亡时间等也会多少有些变化,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此,即便 A 与 B 之间出现了若干偏差,仍然存在通过对此予以抽象化,进而抽象化地把握结果的余地。[17]通过这种“结果的抽象化”,对于“大阪南港事件”,肯定存在引起结果之相当性的观点也开始成为有力观点。
对于这种理解,还需要明确以下两点:第一,该学说的问题意识进一步凸显出,将行为之后的介入情况纳入判断基础之后再判断相当性之有无这种判断模式毫无意义。就“大阪南港事件”而言,按照这种判断模式,会将第二暴力作为不可能预见的情况而从判断基础中排除出去,即便如此,仍然会肯定实行行为与引起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将第二暴力排除在外,不过是为了判断下述情况而已:通过比较实际发生的具体的死亡结果与在没有介入第二暴力的情况下可能会发生的(假定的)死亡结果,看究竟造成了多大程度的不同,并判断这种不同在法律评价上具有多大意义。概言之,为了判断实行行为对引起结果施加了何种程度的影响,作为一种思维模式上的实验,而假定性地排除了异常的介入因素。[18]如果是这样的话,原本只要起始便考察实行行为的影响力的程度即可,特意采取限定介入因素之后再判断相当性这种模式,就鲜有必然性。基于这种理解,就无需针对行为之后的介入因素设定判断基础,只要直接以实际的因果进程为分析对象,探讨实行行为对引起结果所施加的影响的内容及其程度即可。
第二,需要明确“将结果予以抽象化”的含义。结果的抽象化这一思考过程,最终而言,无外乎是验证实行行为对结果的影响程度的过程。例如,在能认定死因的同一性的限度之内,学界有力观点认可结果的抽象化。[19]具体而言,如果是由实行行为形成了死因,就完全可以将该实行行为评价为引起(被抽象化的)结果的行为;反之,如果是由介入行为形成了死因,则意味着,实行行为并不具有引起“因该死因而死亡”这种死亡结果的影响力,应否定存在因果关系。这完全是根据抽象化的标准,来判断实行行为是否存在对结果的影响力。为此,将结果予以抽象化的标准,即判断实行行为是否存在对结果的影响力的标准,在因果关系的判断中就属于重要问题。对于这一点,就前述实行行为形成了死因,介入行为也并未大幅提早死亡时间的“大阪南港事件”,最高裁判所的决定虽肯定存在因果关系,但并未明确表示,仅以死因作为决定性标准。
由上可见,以“大阪南港事件”为契机,相当因果关系说转变至这样一种理解:以实行行为对结果的影响力为标准来判断因果关系之有无。这就正是“危险的现实化说”这种理解。
(二)因果进程的通常性的定位
1.是否以因果进程本身的通常性为必要
相当因果关系说的这种转变,与此前的论争的决定性区别在于,在介入了异常的介入因素的场合,也就是,即便因果进程本身异常,仅此尚不能否定因果关系。在将相当性理解为“引起结果的相当性”的观点看来,这种区别尚不能谓之为本质性修正;但在将相当性理解为“因果进程的通常性”的观点看来,这种区别就意味着决定性的改变。那么,在相当因果关系的判断中,因果进程的通常性是否属于不可或缺的要素呢?进一步而言,原本是基于什么根据而要求存在因果进程的通常性的呢?
对于这一点,学界有力观点从一般预防的必要性的视角,对于因果进程,重视通常人的利用可能性。也就是,对于那些由通常人一般不会采用的特殊因果进程而引发结果的情形,即便不予处罚,也不会出现试图通过采用这种手段而引起结果的人。因此,只要对那些通常人有利用之可能的通常因果进程的设定行为予以处罚即可。[20]然而,如前所述,[21]即便属于通常人一般不会采用的特殊的因果进程,如果行为人利用该因果进程而引起了结果,要否定对行为人的处罚,就明显缺乏合理根据。而且,如果像该观点所主张的那样,处罚对象仅限于那些“一般人可能会采取”的因果进程,(也许超出该说论者当初的设想)就会过度限定处罚范围。例如,被害人遭到暴力,在逃走过程中摔倒受伤,对此,一般的理解是,作为通常的因果进程而肯定存在相当因果关系。在此情形下,被害人不摔倒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也就是说,被害人是否摔倒完全具有偶发性。如果认为这种情形也属于通常人具有采取之可能的因果进程,利用可能性这种标准就几乎是可有可无、毫无实质意义(形骸化)。[22]正如林干人教授所举的例子那样,[23]劝人去树林,该人遭雷击身亡,若处罚这种情形,无疑是以极低概率的危险性为根据而限制行动自由,难言妥当,因为这种情形原本属于实行行为的危险性极低的案件,与是否具有因果进程的通常性毫无关系。如果认为,反正后来救护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因而对于用刀刺人这种行为,没有多大必要抑制,显然,这种观点绝对不可能被接受。[24]
林干人教授至今仍认为,实际的因果进程的通常性(预测可能性)属于相当因果关系的决定性标准。之所以如此理解,想必是因为林教授认为,所谓的贡献度、影响力这种概念的内容本身不确定,采取这种概念的理论性根据也不确切。[25]不过,对于像前述“大阪南港事件”那样,介入因素对结果的影响较小的情形,这种观点也是通过舍弃介入因素,而以因果进程的预测可能性作为前提(既然舍弃了介入因素,当然会肯定存在相当因果关系)。总之,(只要肯定“大阪南港事件”的结论)无论如何都无法不引入“对结果的影响力”这一视角。这样看来,就没有多大必要认为,因果进程本身的通常性(预测可能性)属于因果关系的不可或缺的要素。
2.是否不需要因果进程的通常性
尽管如此,也并不是说,作为判断标准,因果进程的通常性已毫无意义。毋宁说,结论正好相反。如果因果进程具有通常性,当然能认定实行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同样,在危险的现实化的理论架构内,因果进程的通常性也属于重要的判断视角。[26]那么,如何处理因果进程的通常性与实行行为的影响力(贡献度)之间的关系呢?有观点主张,应通过综合考察㈠实行行为的危险性、㈡介入因素的异常性和㈢介入因素的贡献度等三个因素,来判断有无因果关系(或者客观归属)。[27]然而,这并不是说,只要综合考察这三个因素,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例如,如同尽管㈡介入因素的异常性很小,但㈢介入因素的贡献度很高的情形那样,对于判断标准的评价之间存在不一致(相反)的情形,如果不提出明确的解决之道,作为解释论来说,就几乎没有意义。[28]
对于这一问题,有必要区别于实行行为对结果的影响力是否强烈这一点而另外考虑。首先是,像“大阪南港事件”那样,实行行为对引起结果施加了决定性影响,完全可以不考虑介入因素之影响的情形。如前所述,对于这种情形,并无考虑因果进程之通常性的必要,仅凭对于引起结果的影响力,就可以肯定存在因果关系。反之,在介入因素对结果具有影响力的场合,就必须能谓之为,实行行为通常会引起介入因素。例如,被害人为了躲避暴力行为,在逃跑过程中因摔倒而受伤。在该案中,被害人自己摔倒属于引起伤害结果的决定性原因,并非是由犯人的暴力行为本身造成了伤害。在此类场合下,仅限于实行行为完全有可能引起介入因素(被害人的摔倒)的情形,才可以肯定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限于可以想见实行行为会引起介入因素的场合。可以说,作为实行行为的危险性,其内容还包括诱发介入因素的可能性,因此,对于在该介入因素的影响之下而引起了结果的情形,也可以评价为,实行行为的危险性(通过介入因素)已间接地实现于结果。虽然采用的是危险的实现这一表述,但其内容与既往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并无不同。
针对上述论述,也许会存在这样的疑问:对于后一类型,从实行行为对于结果的影响力的角度,不是也可统一地加以说明吗?诚然,对上例而言,也完全有可能做出如下说明:正因为存在犯人的暴力行为,被害人才会慌不择路而摔倒,因而当初的暴力行为对于最终的伤害结果施加了重大的影响。负责“大阪南港事件”的最高裁判所调查官[29]的下述说明想必也正是如此旨趣:“行为对结果的影响,不仅是从医学的角度,还可以从物理学上、化学上、心理学上等各种角度进行考察。”[30]当然,影响力、贡献度这种词语本身就存在多重含义,出于何种旨趣来使用该词语,也是自由的。但毫无疑问,由逃跑过程中的摔倒而引起的伤害结果,是犯人当初的暴力行为所单独无法造成的结果。这一点与“大阪南港事件”存在根本区别:在“大阪南港事件”中,被告人的暴力行为本身,也能够单独造成基本相同的死亡结果。如果着眼于案件的这种性质差异,从实行行为能否单独造成具体结果这一角度,来理解是否存在对结果的影响或者贡献,要更为合适。[31]
由上可见,在介入因素对引起结果施加了重大影响的场合,往往是要求介入因素具有通常性,但这里的通常性,不限于“是否会经常出现这种情况”这种事实性的、盖然性的判断,而要求在与实行行为的关联性上进行相对判断,[32]届时也应该考虑介入因素的性质等规范性事实。[33]这一点后面还会谈到。
(三)危险的现实化的判断结构
作为对前述分析的整理,下面对危险的现实化的判断结构进行简要归纳。在实行行为的危险性实现于结果的场合,能认定存在因果关系。危险的实现,可以类型化地区分为
直接实现型与间接实现型这两种类型。[34]前者是指实行行为对引起结果施加了决定性影响的情形,“大阪南港事件”就是其适例。在该情形下,无需考虑因果进程的通常性。后者是指实行行为的危险性经由介入因素而间接地实现于结果的情形。在该情形下,介入因素对引起结果具有直接影响力,但由于能认定实行行为本身存在引起介入因素的危险性,因而能评价为,间接地实现了实行行为的危险。在这种情形下,要求存在介入因素的通常性。按照对于危险实现的这种理解(除去不具有结果避免可能性的例外情形),能否定存在因果关系的,仅限于下述情形:实行行为未对引起结果施加直接的影响,并且,对实行行为而言,介入因素的介入能被评价为异常事态。
另外,即便是能够否定存在“危险的实现”这种关系的场合,仍能认定实行行为与引起结果之间存在事实性因果关系(条件关系),这一点并无改变。尽管如此,这种场合下,为何又能否定针对结果的归责呢?原本来说,以危险的现实化作为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又是基于什么根据呢?要从理论上回答此问题,确实非常困难,而只能是做如下形式上的说明:既然实行行为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行为,限于与该危险内容相关而实现了结果的场合,才肯定结果归责,这样就更为妥当。这里与其说是进行理论上的限定,毋宁说重视的是这样一个视角:处罚到什么范围,作为刑罚权的行使才是适当的?亦即,之所以一般认为条件说不正确,并不是因为条件说作为刑法理论无法成立,而无非是认为,只要存在条件关系就必须处罚这种价值判断不妥当。[35]因此,以危险的现实化进行限定,更多的是基于刑法谦抑性的一种政策性判断。[36]当然,也不是说,只要是属于政策性判断,就可以任意地推导出任何结论,仍然需要比照社会一般观念进行合理的价值判断:将什么范围之内的结果,作为行为人的“所作所为”而予以归责是妥当的?[37]正因为如此,在因果关系理论中,为了确保稳定的判断结构,势必会更强烈地要求,将相关事实尽可能详细地予以类型化,并将具体判断标准予以明确化。[38]
四、实行行为的危险性的判断
(一)危险性的判断结构
下面具体探讨危险的现实化的判断标准。如果将危险的现实化的判断予以公式化,就属于这样的流程:首先,(1)明确内在于实行行为的危险性的内容,然后,(2)验证能否评价为,该内容通过实际的因果进程以及结果之引起而得到了实现。例如,在对被害人施加暴力的情形下,该实行行为当然包含着因暴力作用而致被害人受伤的危险,除此之外,还包括这样的危险:因受到暴力行为的冲击而摔倒受伤的危险,以及为了躲避暴力而在逃跑过程中摔倒,因撞到什么东西而受伤的危险。这样,从能够预想到实行行为会引起何种结果的角度,可以确定实行行为的危险的内容。并且,实际的因果进程以及引起结果的样态,如果能够评价为,属于所预想到的危险的实现过程,那么,就完全可以肯定危险的现实化。[39]因此,逃跑过程中摔倒受伤的,既然这种危险能纳入到实行行为的危险之中,就能肯定危险的现实化。[40]“大阪南港事件”的问题在于,因颅内出血而死亡的危险,这显然是能够被评价为实行行为的危险内容的,然而,对于因介入因素而稍微提前了死亡时间的情形,能否也可谓之为该危险实现于结果了呢?
按照上述理解,实行行为的危险性的内容之中,就不仅包括实行行为单独引发结果的危险性,还包括实行行为引起介入因素,在介入因素的影响下而引起结果的危险性。我们知道,实行行为也并非总是凭借其本身的作用而引起结果,因而这样理解也有充分的理由。并且,要将由介入因素引起结果的可能性纳入到实行行为的危险性的内容之中,正如前面已反复谈到的那样,就要求(从与实行行为的关系上看)能认定存在“介入因素的通常性”。因此,实行行为的危险性与介入因素的通常性,这两个概念并不能绝对区别开来,其内容是相互关联的。[41]
由上可见,作为实现危险之起点的实行行为的危险性,最终仍需要包括,与实际的因果进程以及所引起的结果相对应的内容。例如,向被害人开枪,子弹偏离,但由于被害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受到枪声惊吓,因急性心力衰竭而死亡。在该案中,流血死亡、器官损伤等针对生命的各种危险,显然内在于开枪行为之中。但是,由于这些危险并未作为具体结果而被现实化,因而对于因果关系的判断,这些情况就毫无意义。要肯定危险的实现,必须是实行行为的危险性的内容之中,包括引起被害人急性心力衰竭的可能性;并且,也只要能肯定这一点即可。[42]
(二)危险性的判断材料
1.判断基础的必要性
在判断实行行为的危险性之际,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如何设定危险性的判断材料呢(判断基础论)?
这一点与此前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完全相同,亦即,并不是说,因为采取的是“危险的现实化说”,所以完全不需要所谓判断基础论。[43]为此,(尽管未必进行了明确的研究,)即便是折中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的论者采取危险的现实化的框架,作为危险性的判断材料,仍然完全有可能在理论上维持折中说。如后所述,判例并非是持这种观点,但也并不是说,只有判例理论才是唯一正确的危险的现实化说。如果明确地主张这种观点,在危险的现实化说的内部,也会与客观说(以行为当时存在的所有情况为前提来判断实行行为之危险性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立,这对于今后研究的深入,应该是有益的。
2.被害人的特殊情况、外界的特殊情况
对于被害人的病变等特殊情况,判例的做法是,即便属于一般人所无法认识到且行为人本人亦无认识的情况,仍将该特殊情况纳入判断材料,肯定存在因果关系。在前述“老妇捂被事件”(最判昭和46年〔1971年〕6月17日刑集25卷4号567页)中,对于那种因被害人本人亦无认识的严重心脏疾病而发生死亡结果的情形,判例肯定暴力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最高裁判所做出了“即便能认定,如果没有被害人的严重心脏疾病这一特殊情况,被告人的本案暴力行为想必不会造成致死结果,而且,被告人在行为当时对该特殊情况并不知情,也未能预见到致死结果”,仍能肯定存在因果关系这种判旨的判决。该判决明确显示了判例态度:对于被害人的特殊情况,全部纳入因果关系的判断材料之中。[44]此外,对于下述案件,判例也肯定存在因果关系:脚踢被害人的面门,但被害人因脑梅毒而引起大脑发生病变,最终因脑组织遭到破坏而死亡(最判昭和25年〔1950年〕3月31日刑集4卷3号469页);由于遭受暴力的被害人的肺部存在结核性病灶,最终因服用类固醇(steroid)引起循环障碍而死亡(最决昭和49年〔1974年〕7月5日刑集28卷5号194页)。
不过,判例的相关案件都集中于被害人存在特殊情况的情形,至于如何评价行为当时的特殊情况,判例态度尚不明确。下面通过两个现实生活中不太会发生的案件来进行说明:被害人因遭受暴力而摔倒,但正好地下埋有“臭弹”,最后因“臭弹”爆炸而死亡;在运送被害人的救护车必经之路上,桥梁因年久失修实际已经老化,当救护车经过此地时,正好桥梁坍塌,造成死伤事故。如果彻底贯彻客观说,即便是一般人无法认识到的情况,由于这些情况仍要纳入到判断基础之中,因而会肯定存在因果关系。但这种结论是否妥当,不无疑问。
对此问题,曾根威彦教授基于传统的“客观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的立场,主张对判断基础进行区分。也就是,按照曾根教授的观点,除了行为当时的全部客观情况之外,还要将行为之后预见可能的情况也纳入到判断材料之中。诸如上述“臭弹”、桥梁老化等情况,并非是在实行行为阶段直接发挥作用,而是在行为之后才介入到因果进程,属于事后施加影响的情况,被定位于行为之后的介入因素。[45]如果进行这种区分的话,就是按照客观说的观点,也能够将“臭弹”、桥梁老化等情况作为一般人所无法预见的因素,从判断材料中排除出去。然而,诸如由于发生特殊病变,无法取得治疗效果而最后死亡的情形那样,对于被害人本身的特殊情况,也完全能够想到,会存在实行行为之后才对因果进程施加影响的情形。对这种情形与病变在实行行为阶段即直接发挥作用的情形区别理解,难言妥当。[46]
为此,佐伯仁志教授主张,应区分被害人的特殊情况与除此之外的其他外部情况。佐伯教授认为,“被害人不应作为一般人(一般的被害人),而应作为一个个具有自己个性的个人而得到尊重,因而,具有特殊体质的被害人,也应该作为该具有特殊体质的个人而受到刑法的保护”,主张将被害人的特殊体质等情况全部纳入到判断材料之中,在此基础上,对于除此之外的其他外部情况,则基本上支持折中说的观点。[47]这种将被害人的特殊情况予以特别考虑的观点,受到了学界的猛烈批判。[48]其中,佐伯教授主张的保护(患有特殊疾病的)被害人的必要性、重视当事人之间的公平分担风险等视角,更是成为批判的靶子。不过,即便不特别强调这种视角,也完全有可能推导出这种理解:让被害人作为被害人本身而成为保护的对象。例如,猎枪走火射向自家屋顶,没想到打死了正躲在天花板背后的小偷。对于此案,即便几乎不可能认识到小偷的存在,但仅此便直接否定存在因果关系,想必无法采取这种理解。对于结果归责的研究而言,被害人在那里、发生了结果,这些都应该是当然的前提。[49]这样,如果受害对象的存在属于客观的前提,那完全是说,受害对象属性的集合体就是其存在本身,因此,就存在这样理解的余地:受害对象的属性,全部属于因果关系的判断前提。
3.客观说、折中说
在限于被害人的属性(特殊情况),将全部客观情况作为危险性的判断材料的场合,对于与受害对象无关的其他外部情况,应如何考虑呢?实行行为是否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原则上应以客观情况为基础来进行判断。[50]以这种理解为前提,将所有客观情况均作为判断材料的观点(客观说),原则上,就应该是妥当的。然而,因谁也不会注意到的偶尔埋在地下的“臭弹”而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对于这种情形,也可以将死亡结果归责于行为人吗?当然,也可能存在这样的理解:(在肯定存在因果关系之后)还存在通过故意或者过失来限制处罚范围的可能性,因而没有必要特别限制因果关系。但是,在通说看来,要成立故意犯罪,无需对实际的因果进程存在认识,只要对能评价为相当因果关系(危险的实现)的事实存在认识即可;在过失犯罪的情形下,也只要对同样的事实存在认识可能性即可。为此,除去那些除了实际的因果进程之外几乎再没有引起结果之可能性的例外情形,要通过故意或者过失来进行限制,是很难做到的。[51]例如,就前述“臭弹”案而言,是存在被害人因后脑勺着地受到猛烈撞击而死亡的可能性的,如果对此类事实存在预见可能性,即便对“臭弹”的存在几乎不可能存在认识,仍然难以否定对死亡结果存在过失。是否将这些特殊情况纳入危险性的判断之中,不仅仅是说明方式的不同,更会给处罚范围带来很大的不同。
如果在以客观说为前提的基础上再意图限制处罚范围,就可以想到,取代全部的客观情况,通过科学的专业人士的认识可能性来进行限制。[52]亦即,对于按照现代的科学水平所无法认识到的情况,将其排除在判断材料之外。然而,如果进行彻底调查,“臭弹”也好,桥梁老化也好,这些都是可以查清楚的,因而,即便是采取这种标准,问题也仍然未得到解决。而且,本文以为,对于即便是专业人士也无法轻易发现的情况,如果行为人本人偶尔意识到了的,也应该将这些情况纳入到判断材料之中,肯定存在因果关系。[53]这样考虑的话,折中说(虽以一般人的认识可能性为基本,但同时例外地考虑本人所特别认识到的情况)是否更为妥当呢?
如前所述,因果关系理论属于政策性判断、价值性判断的色彩很强的领域,针对这种特殊案件,应该处罚到什么范围,这一点未必清晰。因此,采取客观说会使得处罚范围过大,担忧这种一般化已到什么程度,实事求是地说,笔者也不清楚。通过折中说来限制处罚范围,我个人虽感受到了这种解决路径的魅力,但同时也认为,对于仅限于这种场合行为人的认识才会对违法判断造成影响这一点,如何从理论上为其找寻正当化根据,仍然是一个问题。[54]这也是我的困惑之处,对此仍需进一步思考。
作为危险之现实化的因果关系(2)
一、引言
这里要讨论的主题是,实行行为之后再介入某种行为的情形,如何判断因果关系。首先,对于前面所探讨的“危险的现实化”的判断结构的内容,这里想做一个简要归纳。
在结果实现了实行行为的危险性的场合(即结果将实行行为的危险性予以了现实化的场合),就能认定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危险的现实化,采取的是二阶段的判断结构:(1)探讨能认定实行行为存在何种危险,在此基础上,(2)看直至引起结果的实际的因果进程能否被评价为该危险的实现过程。前一判断探讨的是,实行行为具有引起何种具体结果的危险,与此前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中的判断基础论一样,这里也存在以何种事实作为判断材料的问题。
与之相对,后者的危险实现过程,可以类型化地区分为直接实现型与间接实现型。前者是指实行行为对引起结果施加了决定性影响的情形,无需探讨介入因素的性质,即能认定危险的现实化。后者是指实行行为的危险性经由介入因素而间接地实现于结果的情形。亦即,作为实行行为之危险性的内容,在实行行为包含了引起介入因素的可能性的场合,就能评价为,实行行为的危险性(以介入因素为中介)间接地实现于结果。
尽管直接实现型与间接实现型不过是实行行为之危险实现的变化形式,但事实上,在因果关系的判断中,两种类型所重视的角度是不同的:对直接实现型而言,重要的是,实行行为是否对引起结果施加了决定性影响;反之,在间接实现型中,作为实行行为之危险性的内容,是否包含了引起介入因素的危险,也就是,介入因素的介入能否被评价为通常事态,就属于重要的问题。
下面依次探讨各种判断标准。另外,对于介入了行为人本人的其他行为的场合,如何考虑行为人的数个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也是需要特别研究的问题,因而也在后面单独进行探讨。
二、对介入行为的评价
(一)概述
如前所述,如果实行行为存在引起介入行为的危险,在实行行为经由介入行为而发生了结果的场合,也能认定存在危险之实现这种关系。要认定存在这种关系,介入行为的介入,必须是能被评价为,在与实行行为的关系上,不属于异常事态。学界存在介入因素的预见可能性、经验性通常性、盖然性等各种各样的表述,但不管如何,都属于介入因素的介入能否谓之为“完全有可能出现的事态”的判断标准,没必要特别关注表述上的差异。预见可能性这一标准,看上去似乎是依据行为人的主观能力,但毋宁说,这里追问的是,是否属于一般有可能预见的事态,因而与所谓通常性的判断并无实质性的不同。[55]不过,无论采取何种表述,对于介入因素的介入,不能要求存在高度的盖然性。在因果关系的判断中,最终要求的不过是,“避免将偶然的事态归责于行为人”,因此,要求结果发生具有高度的盖然性,这实际上并无多少必然性。举例来说,对未曾摸过枪的笔者而言,即便是从几米开外的地方向被害人开枪,要命中被害人身体的要害部位致其当场死亡,应该说,这种可能性是极低的(这一点无从实验,也许有百分之几或者更低的概率)。但是,即便如此,如果实际命中了被害人的要害部位,就完全不可能得出否定因果关系的结论。对于介入因素介入的盖然性,也应该做同样的理解。
是否属于异常事态,在介入了自然现象的场合,一定程度上是有可能做出明确判断的。[56]例如,劝说他人去树林,结果在树林中遭遇雷击,一般而言,这属于异常事态;在大型台风就要登陆之际,劝说他人去登山,该人因遭遇强台风而摔下山,这就属于完全有可能发生的事态。又如,在后述“夜间潜水事件”中,在作为潜水教练的被告人离开学员身边之后,学员被汹涌起伏的海浪冲向大海深处,虽然介入了被告人发现过晚这一情况,但如果以当天的恶劣天气等为前提,学员被卷入海潮这种事情尽管可以谓之为突发情况,但仍然可以说,这属于完全有可能发生的事态。[57]
反之,对于介入因素是他人行为的案件,主流观点主张,通过着眼于实行行为与介入行为之间的关联性,来判断有无因果关系。亦即,就介入行为而言,既有受实行行为的影响而提升介入可能性的情形,也有与实行行为毫无关系,而是因其他独立的原因而介入的情形。在探讨实行行为是否包含着引起介入行为的危险之际,二者之间的区别就尤其重要。佐伯仁志教授认为,同样是用救护车将身负重伤的被害人送往医院,与因救护车驾驶员的过失而遭遇交通事故最终致被害人死亡的情形相比,因急救医院的医师的不恰当的治疗行为而死亡的情形,就相对更容易认定存在因果关系。[58]具体而言,救护车遭遇交通事故,这属于完全有可能与实行行为毫无关系而发生的事态,但在后一情形下,急救医院的医师因为行为人的实行行为而不得不面临,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必须紧急抢救(完全陌生的)被害人的状态,因而医师犯错的概率也有可能大幅增加。因此,要将上述两者的区别予以正当化,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近年来,判例重视的是,介入因素是否由实行行为所“诱发”,对此,从上述角度来看,也能够理解。
不过,也不是说,只要是由实行行为所诱发,无论介入了何种因素,都能够肯定因果关系。例如,被害人为躲避暴力而采取逃避行为的,这可以说是由实行行为所诱发,但如果说,即便被害人采取了一般人无法想象的异常行为,由于是由实行行为所诱发,因而总是能认定存在因果关系,则事实上就已经回归至条件说。[59]实行行为的危险性要评价为含有引起介入因素的危险性,就要求作为一般性、类型性的评价,即诱发那种介入行为属于完全有可能的事态。对于后述“闯入高速公路事件”,最高裁判所也判定,被害人的介入行为“不能谓之为,明显不自然、不妥当”,可见也是考虑到了介入因素的通常性。
由上可见,对于介入行为,如果能认定(1)与实行行为之间存在关联性,并且,(2)该介入不具有异常性,就认定存在因果关系。如前所述,作为实行行为之危险性的内容,要求能认定存在引起介入因素的危险性,有鉴于此,第(1)点就属于本质性内容,这一点难以否认。[60]不过,尽管说第(1)点的视角很重要,但如果认为,只要实行行为与介入行为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性即可,那么,这种要求就不属于那么严格的要求,对于以因果关系存在与否作为主要问题的很多案件,也便会肯定因果关系。因此,本文以为,第(2)点的视角实际上也属于划定处罚范围的重要标准。
学术研究如果仅限于抽象的、一般性的论述,并无多大意义,因而下面结合近年的具体判例,进行具体探讨。
(二)被害人行为的介入
1.柔道康复师事件
本案被告是一名柔道康复师,被害人因为有点感冒而请其诊断治疗,被告人向被害人做出了提高热度、控制饮食与水分、在密闭的房间用被子包裹严实以利发汗等错误指示,即便遵其指示的被害人的症状逐渐恶化,再三出诊的被告人仍然对被害人重复做出同样指示。由于被害人一直忠实遵照被告人的指示,其病情不断恶化,在接受诊疗之后的第五天陷入脱水症状,最终死亡。对此,最高裁判所判定,“被告人的行为本身具有恶化被害人的病情,甚至难免不导致死亡结果的危险”,因而即便被害人本身也有过错,仍能认定被告人的指示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最决昭和63年〔1988年〕5月11日刑集42卷5号807页)。最高裁判所的本决定重视实行行为的危险性而肯定因果关系,但即便说实行行为是危险的,仅凭被告人的指示行为,是根本不可能致被害人死亡的。本案实行行为要引起死亡结果,由该行为引起被害人遵从指示这一介入因素,是绝对需要的。[61]因此,限于实行行为存在诱发被害人的介入行为的危险的场合,才能认定实行行为具有针对生命的危险。如此看来,批判该决定是仅凭实行行为的危险性就肯定因果关系,而没有考虑危险的实现过程的观点,[62]就未必是正确的。毋宁说,对于类似本案那样的案件,将实行行为的危险性与危险的实现过程分开判断,这并无意义。[63]
那么,能否认定本案实行行为存在引起被害人的相关反应的危险呢?按照本文观点,不能仅仅是引起了介入因素这一事实,还必须是完全有可能引起该事实。而在本案中,被害人持续遵从医学上明显错误的治疗方针,可以认为,这本身也属于异常事态,为此,就出现了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根据二审的事实认定,被告人与被害人一家一直关系亲密,尤其是被害人的母亲更是对被告人赋予了绝对的信任。因此,如果以这种关联性为前提,就可以认为,被害人忠实遵从被告人的指示这一过程,也就不是那么异常了。[64]但是,最高裁判所并未言及该事实,而直接肯定存在因果关系。由此可见,最高裁判所的该决定暗示了这样一种态度:在本案中,即便不存在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这种关联性,仍能认定因果关系。对于这一点,负责本案的调查官指出,被害人的行为是“直接源于被告人的指示”,“属于难以主张存在异常性的案件”。[65]想必最高裁判所的理解是,由于被害人是完全按照被告人的指示行事,当然能肯定因果关系。但是,如果彻底贯彻这种理解,即便是谁也不会接受的指示,但偶尔有被害人遵守了的,也要认定存在因果关系,这显然不妥。在本案的事实关系中,重要的是,被告人明明知道被害人忠实地执行着自己的指示,被告人仍再三出诊,且数次重复做出同样的指示。[66]也就是,以被害人忠实执行被告人的指示这一事实为前提,通过数次做出同样的指示,而相应地增加了被害人遵从其指示的危险,其结果就是,可以藉此否定介入因素的异常性。因此,如果案情改变——被告人在最初的诊疗之际做出了指示,其后未再与被害人接触,但被害人仍然持续忠实地遵从了被告人的指示,那么,就有否定因果关系的可能。
2.夜间潜水事件
本案被告是有氧潜水(scuba diving)训练的教练,在指挥助教安排学员实施夜间潜水练习的过程中,随意移动(观察)位置,使得助教与学员消失在自己的视野之外。遇到这种情况,本应该是在海面上待命,等待大家集合在一起之后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但助教一边寻找被告人一边指示学员继续进行水下练习。作为学员的被害人听从助教的指示,在未经确认水下呼吸器中的空气余量的情况下,继续进行水下移动训练,途中因氧气耗尽而陷入恐慌状态,最终溺水身亡。对于该案,最高裁判所认为,被告人从学员身边离开,使得学员消失在自己的视野之外的行为“本身具有这样的危险:对作为学员的被害人来说,如果没有教练的适当指示、引导,就有无法采取应对紧急事态的妥当措施之虞,存在难免不引起学员在海中氧气耗尽,且无法采取适当措施的情况下溺水身亡的危险,尽管无法否认,在看不到被告人之后,助教以及被害人本身也存在有失妥当的行为,但那属于被告人的上述行为所诱发的行为,无碍于肯定被告人的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最决平成4年〔1992年〕12月17日刑集46卷9号683页)。也就是,与前述“柔道康复师事件”一样,本案实行行为的危险性判断,不是指实行行为本身具有直接引起结果的内容,而是指实行行为具有引起被害人等的不当行为的危险。[67]而且,对于“诱发”这一表述,也不仅仅限于由实行行为引起了介入行为这一事实,而是以“这种介入因素的介入通常是有可能的”这种判断作为当然前提。[68]最高裁判所的本案决定也列举了被害人属于初学者技术尚不熟练、夜间潜水会助长不安感与恐惧感、助教作为教练资历尚浅经验不足等具体事实,这些事实都属于为本案介入因素的通常性奠定基础的事实。对于肯定因果关系,此类事实的重要性是决定性的。
而且,在本案那样的过失犯罪的场合,过失犯的注意义务的认定与因果关系的判断,在一定范围内是相互重合的。虽然对过失犯的成立要件尚存在争议,但在将违反结果避免义务且具有很大的实质性危险的行为作为实行行为来把握的场合,作为结果避免义务的内容,就要求事先避免那些预见可能范围之内的危险。并且,在实行行为很可能诱发介入行为的场合,可以说,对于通过介入因素而得以现实化的危险,也是存在预见可能性的,因此,避免这种结果的发生,也属于避免义务的内容。为此,在介入因素被评价为通常事态、能够肯定因果关系的场合,尽管被赋予了避免义务,但未能避免(以介入因素为中介的)结果发生,因而也能肯定违反了结果避免义务。这样,两者的判断就存在相互联动的关系。[69]不过,过失犯中的实行行为的判断与因果关系的判断,也并不总是保持一致。例如,如果本案被害人虽一度溺水,但被助教救起而得以保命,其后,在救护车将其送往医院的途中,遭遇交通事故,因交通事故而死亡,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就存在即便能认定存在违反结果避免义务的过失行为,仍应否定因果关系的余地。[70]而且,作为过失犯的预见可能性,一定程度上,要求必须是具体的且高度的预见可能性,因此,即便是能肯定因果关系的案件,也可能会否定行为人存在预见可能性。理所当然,因果关系的判断与过失的判断在理论上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事实上,也不过是部分考量因素有可能存在重合罢了。[71]
3.闯入高速公路事件
本案被告等人深夜断断续续地对被害人先后在公园、公寓房间分别实施了大约2小时10分钟、45分钟的激烈暴力,被害人乘隙从公寓房间逃出。由于对被告等极度恐惧,在逃走10分钟之后,为了躲避被告等的追踪,闯入高速公路,被疾驶的汽车撞死。对此,最高裁判所认为,虽然被害人的行为“本身属于极其危险的行为”,但同时“能够认定,被害人长时间受到被告等人的激烈且执拗的暴力,对被告等人抱有极度的恐惧感,在拼命谋求逃脱的过程中,是瞬间选择那种行动,因而不能说,作为逃离被告等人的暴力的方法,该行动特别不自然、不妥当”,进而肯定了因果关系(最决平成15年〔2003年〕7月16日刑集57卷7号950页)。
对本案而言,被害人的行为“不能说,作为逃离被告等人的暴力的方法,该行动特别不自然、不妥当”这一判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72]由于本案暴力极其执拗,被害人抱有极度的恐惧感,是在拼命逃离的过程中“瞬间”做出的判断,因此,考虑到这一点,对于很难谓之为通常的行为,也有可能降低其异常性,而将其评价为是由本案实行行为所可能诱发的事态。
针对上述理解,也有观点认为,仅凭被害人陷入极度恐慌状态这一事实还不充分,毋宁说所要求的是,被害人的行为在实行行为的影响之下,能被评价为“合理的”行为。[73]也就是,仅限于下述情形,才能肯定因果关系:尽管实际选择的逃离行为极其危险,而且,作为逃离手段另有其他更有效的选项,[74]但由于实行行为对被害人的心理层面所施加的影响,被害人对逃离手段的危险性、其他选项的判断等状况产生错误认识,其结果是选择了本案逃离行为,而选择本案行为对被害人而言,可以评价为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的确,如果过度强调被害人陷入了极度恐慌状态这一事实,那么,被害人采取任何逃离手段,都不能谓之为不可思议,从而也能肯定因果关系,但这显然不妥。[75]例如,被害人在高层公寓位于高层的室内受到激烈暴力,被害人(虽然知道位于高层)乘隙从窗户跳下而摔死,在此类情形下,就大多会否定因果关系。而且,在被害人当时的心理状态之下,如果能认定并无其他选项,那么,就完全可以谓之为,在与实行行为的关系上,选择该手段是必然的,对此当然能肯定因果关系。不过,要肯定因果关系,也并不是绝对需要属于“迫不得已”的选择。即便被害人没有被逼到如此境地,如果在与实行行为之间的关系上,完全可以理解被害人的该判断,那么,就可以认为,实行行为之中包含了引起该选择的危险,因而也存在肯定因果关系的余地。[76]本文认为,直接认定被害人的选择属于丧失了合理性的行为,在此基础上,探讨是否完全有可能因受实行行为的影响而出现这种错误选择,要更为合适。
另外,就本案而言,并非是由被告等人的暴力的物理性危险而引起了介入因素,而是可以谓之为,是由执拗的暴力所造成的心理性影响而诱发了不适当的逃离行为,因此,对于因果关系的判断,实行行为对被害人心理的影响程度,就具有决定性意义。为此,即便暴力程度并非如此严重,如果处于会给被害人施加同等程度的心理性影响的状态之下,也同样能肯定因果关系。例如,出于私刑的目的拘禁了被害人,即便是被害人因对遭受私刑极度畏惧而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仍然存在肯定拘禁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余地。[77]
(三)第三者行为的介入
1.过失行为的介入
对于介入了第三者的行为的情形,基本的视角与前面是相通的。为此,如果能评价为,属于实行行为通常会引起的事态,就能肯定因果关系。就介入了第三者的过失行为的情形而言,过失的程度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很多时候是,如果不是非常重大的过失行为,就会作为有可能由实行行为所诱发的情形,而肯定因果关系。反之,在过失程度极其严重的场合,很多时候则会作为异常事态而否定因果关系。
以上述一般论为前提,“汽车后备箱事件”(最决平成18年〔2006年〕3月27日刑集60卷3号382页)就属于与此多少有些不协调的案件。案情大致如下:某日深夜,本案被告将被害人关在普通轿车的后备箱内,开动汽车之后,为了与熟人会合而将车停在马路上,停车后没几分钟,第三人驾车因未留意前方而未注意到处于停车状态的被告车辆,以60公里的时速几乎从正后方撞上该车尾部,被关在后备箱内的被害人因受到撞击而死亡。对此,最高裁判所判定,“即便引起追尾事故的第三者的极其重大的过失行为,是被害人的直接死因,仍能肯定将被害人拘禁在停在马路上的普通轿车后备箱之内的拘禁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最高裁判所并未明示其论据。
本案实行行为是将被害人拘禁在汽车后备箱的行为,毋庸置疑,能认定该行为存在各种针对生命的危险,例如,被害人试图逃出而受伤的危险,因精神上的不安而自残的危险,炎热天气下中暑死亡的危险,等等。但是,本案的最终结局是,完全是因后续车辆追尾而造成了死亡结果,因此,拘禁行为中包含着因其他途径而死亡的危险,这对于本案因果关系的判断毫无意义。并且,仅凭拘禁行为本身绝对不可能发生这种死亡结果,为此,本案要认定因果关系,就必须能认定存在这样的关系:拘禁行为完全有可能引起第三者的追尾事故。对于这一点,负责本案的调查官认为,遭遇交通事故,这在社会一般观念来看,可以评价为“勉强有可能发生”。[78]的确,(很遗憾)交通事故本身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发生轻微的财物损毁事故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本案事故是以60公里的时速从正后方追尾,且能认定驾驶人存在“极其重大的过失”。也有学者提出,是由深夜在马路上停车的行为诱发了追尾事故,[79]但案发当时的停车地点是在笔直的马路上,且视野良好,[80]即便同时考虑深夜在马路上停车这一点,要将本案事故评价为“勉强有可能发生”,也很困难。并且,就算本案事故属于“勉强有可能发生”的事故,如果以60公里的时速撞击,即便被害人是被关押在车内后座(尤其是如果没有系安全带的话),被害人因撞击而死亡,也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为此,即便是在这种假定的情况下,也难以说不成立拘禁致死罪,但本文不认为这种结论是妥当的。[81]为此,就可以这样理解:即便考虑到本案实行行为提升了诱发追尾事故的可能性,本案的介入因素仍属于异常性很高的行为,而且,是由于该介入因素的直接作用而发生了死亡结果。因此,可以说,反对判例结论的观点也有充足的理由。[82]
不过,按照下述逻辑,则有可能肯定因果关系:生产厂家在设计汽车后备箱时,当然没有考虑到会有人在里面,后备箱不具有保护人身安全的功能,因而,即便是轻微的财物损毁事故程度的撞车事故,后备箱里面的人因撞击而死亡的可能性也是很高的;并且,如果深夜将车停在马路上,发生轻微的财物损毁事故程度的撞车事故,可以说,这种情况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按照这种理解,对于本案的拘禁行为,就有做下述理解的余地:存在因轻微的撞车事故而致被害人死亡的危险,为此,如果真的发生了轻微事故,且已经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就当然能认定实现了危险。由此看来,不管是轻微事故还是重大事故,总之是明明都存在被害人死亡的危险,却因为实际发生的事故程度偶尔严重,就不能将死亡结果归责于实行行为,这样难言妥当吧?毋宁说,两者最终都属于有可能以撞车事故这一形式予以抽象化的介入因素,因此,即便是因实际发生的重大事故而死亡,也是以所谓“举重以明轻”的形式显示,(即便是轻微事故,被害人也会死亡这种)实行行为的危险性潜在地得以现实化,这样的话,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将判例结论予以正当化。[83]
2.故意行为的介入
实行行为之后,介入了第三者的故意行为的,就需要加以特别考察。也就是,指向同一结果的故意且有责的行为,完全应该作为第三者自身的主体意思决定来对待,因此,就不应该评价为,是受到实行行为影响的介入行为。以一般原理的形式将这种设想予以归纳的,是溯及禁止论。基于“引起构成要件结果之原因的支配者是正犯”这一理解,山口厚教授认为,对于侵害结果介入了故意且有责的行为的,原则上应否定幕后者的正犯性。[84]因介入了故意且有责的行为,究竟是否定因果关系还是否定正犯性本身,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但考虑到共犯的处罚也以存在因果关系为必要这一点,否定正犯性可能更为妥当。[85]总之,实行行为之后,介入了第三者的故意且有责的行为的,按照这种理解,就会否定成立正犯的既遂犯。[86]不过,这仅限于是由故意且有责的行为直接引起了结果的情形,为此,溯及禁止论的设想就不适于实行行为对结果具有决定性影响,可以无视介入因素之介入的类型(直接实现型)。[87]
在本文看来,溯及禁止论的内容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正如山口厚教授本人也承认的那样,溯及禁止论并非绝对的标准,而不过是正犯性(或者因果关系)的一般倾向而已,也完全有可能存在例外情况。[88]限于篇幅,这里无法就此问题展开,但本文认为,如果故意且有责的介入行为与实行行为密切相关,且实行行为阶段能预想到该介入的,对于这种例外情形,就不适用溯及禁止的设想,可以将实行行为人作为既遂犯的正犯予以处罚。[89]反之,介入了独立于实行行为的第三者的故意且有责的行为,且由该介入行为引起了结果的,原则上很难作为危险的间接实现型,将结果归责于实行行为人。在该情形下,需要考虑的是,是否属于可以无视介入因素之介入的类型,亦即,是否属于直接实现型而导致了危险。
三、直接的危险实现
(一)概述
如果实行行为的危险直接实现于结果,就可以不考虑介入因素的性质,直接肯定因果关系。在该情形下,由于可以评价为,是实行行为创造了引起结果的决定性原因,是在实行行为的影响下发生了结果,因而可以无视介入因素的介入。并且,要具体判断实行行为的影响力程度,就应该通过比较实际发生的结果、假如没有介入因素的介入而想必会发生的假定上的结果,看这两个结果之间是否会存在质的变化。
按照这种理解,对于“美军肇事逃逸事件”(最决昭和42年〔1967年〕10月24日刑集21卷8号1116页),否定实行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就有可能得以正当化。该案大致案情如下:被告人驾车过程中,因未注意前方而将骑车的被害人撞飞,被撞飞的被害人碰巧落在汽车车顶,坐在副驾驶座的第三者看到被害人的手垂下来,因过于害怕,便拉住被害人的手往下拽,致使被害人栽倒身亡。对于该案,最高裁判所认为,“同乘的人从行进途中的汽车车顶往下倒拽被害人,致其栽倒在沥青路面这种情况,按照一般经验法则,并非通常可以预见;尤其是,在本案中,被害人的具体死因是头部伤情,但难以确定这究竟是因与汽车相撞而造成,还是在同乘的人将其拽下车顶而栽倒在沥青路面之时所形成”,并以此为根据,否定被告人的过失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是介入了第三者的故意行为的案件,问题在于,能否作为危险的直接实现型而肯定因果关系。在该案中,无法否定的是,介入行为本身也有形成属于最终死因之伤害的可能。[90]因此,如果假定性地拿掉第三者的介入行为来考虑的话,就存在因完全不同的死因,且在不同时间死亡的可能性,并且,从实行行为所造成的伤害程度来看,被害人不死亡这种可能性,原本也是无法否定的。这样,只要存在因介入因素而造成最终引起的结果发生实质性改变的可能性,就不能评价为,实行行为的危险已直接被现实化,因而应否定因果关系。
(二)对结果的同一性的判断
那么,尽管因介入因素而改变了结果,但仍因为所引起的结果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而肯定直接实现了危险的,是哪些情形呢?前述“大阪南港事件”凸显了该问题。以该案事实为前提来看,即便假定性地舍弃了介入因素的介入,被害人仍会因内因性高血压性颅内出血而死亡,并且,不过是存在死亡时间稍微延后的可能性。为此,就可以因为并没有实质性改变所引起的结果的样态、内容,而肯定直接实现了实行行为的危险性。[91]
进一步而言,是否存在对死亡结果的实质性改变,换言之,结果的同一性的判断标准究竟是死因还是死亡时间呢?对此,有力观点主张,在死因的同一性的范围之内肯定结果的同一性,[92]从判例的表述来看,“大阪南港事件”也似乎重视的是死因的同一性。然而,死因这一概念的范围相当广,死因的同一性这一概念本身也有结论先行之嫌。[93]例如,被害人因被告人的放火行为而全身烧伤入院治疗,碰巧因医院着火而再度烧伤,由此扩大、恶化了最初的烧伤伤情,最终死亡。在该情形下,既可以说被害人的死因是由最初的放火行为所引起,也可以说,因为加入了医院火灾所造成的烧伤,形成了新的死因。而且,即便因介入行为而大幅提早了死亡时间,仍然坚持只要死因相同就肯定因果关系,在本文看来,这种观点认定危险实现的范围似乎过宽。[94]学界也有有力观点基于这种理解主张,毋宁说应以死亡时间的同一性为标准来判断结果的同一性。[95]如果认为,存在人的生命的延续时间这一意义上的价值,主张若死亡时间相同,就并未实质性地改变结果,这也是有充分理由的。然而,本文仍对这种理解存在若干踌躇。按照这种理解,在“大阪南港事件”中,在被害人在材料堆放点因颅内出血伤情恶化,陷入濒危状态之后,即便是第三者出于杀人犯意突然瞄准被害人的心脏开枪,被害人由此死亡的情形,也能肯定第一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但这种结论显然不当。理由有二:其一,要认定因果关系,必须是由实行行为“引起了”死亡结果,但在死因已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还能说实行行为“引起了”该结果吗?对此略有疑问。其二,假定的死亡时间毕竟只是一种假设性判断,就算被害人陷入了不可能恢复的状态,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奇迹般活命的可能。尽管如此,因为被害人无疑会马上死亡,不管后来发生了什么也要肯定因果关系,这种研究就难保没有简单粗暴之嫌。[96]对此,小林充教授认为,对于已经身负基本不可能得救的致命重伤,确实马上就要死亡的被害人,因医师输血时弄错血型,结果致被害人死亡的,不能将死亡结果归责于实行行为,这种结论是不妥当的。[97]不过,在该情形下,存在理解为是由实行行为所造成的紧急状态诱发了医师失误的余地,因此,即便不讨论结果的抽象化的问题,也完全有可能在危险的间接实现的框架之内肯定因果关系。
这样看来,最终而言,无论是死因还是死亡时间,都属于重要的判断视角,很难仅从其中某一视角来把握结果。尽管最终仍然是一种不算明确清晰的结论,但在本文看来,还是应通过比较实际引起的结果与(假定性地舍弃介入因素之时)假设引起的结果,就各个构成要件分别进行探讨,考察在社会一般观念上,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实质不同。[98]
(三)不作为的介入
介入了不作为的案件,是危险的直接实现型的极端情形。例如,被害人遭受暴力身负重伤,但只要切实接受治疗,完全有恢复的可能,但介入了被害人拒绝就医,或者被害人家属不愿将其送往医院,甚至是送往医院之后主治医师并未实施必要治疗等不作为,其结果是,最初的伤害成为被害人的死因,且造成了被害人死亡。对于此类案件,能否肯定暴力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呢?对此,山口厚教授认为,即便介入了物理性贡献很低的作为,也不能否定危险的实现,那么,对于介入了没有物理性贡献的不作为的情形而言,当然应肯定危险的现实化,因而对于介入不作为的案件,原则上肯定直接实现了危险。[99]的确,即便介入了不作为,也不会由此改变死因,因而如果重视死因的同一性,就难以否定,实行行为的危险性原样实现于结果。然而,所谓实行行为的危险性,那也应该是在设想通常所能预见的因果进程的基础上进行判断。为此,即便是因实行行为而遭受重大伤害,如果属于若接受适当治疗就确实可以恢复,死亡的危险几乎可以解消的情形,对于实行行为,就应评价为,不过是存在这种程度的危险,因而是有可能否定危险的实现的。[100]
在这种观点看来,最决平成16年(2004年)2月17日刑集58卷2号169页之案就属于一个有趣的案件。该案大致案情如下:本案被告与共犯一道对被害人实施暴力,给被害人造成了因左后颈部刺伤而形成的左后颈部血管损伤等伤害。被害人立即赶赴医院接受紧急手术治疗,尔后,被害人的身体状况趋于稳定,主治医师也认为,不出意外大约3周后即可出院。然而,被害人的身体状况当天急转直下,之后,被害人因基于上述左后颈部刺伤的脑部循环障碍所引起的脑功能障碍而死亡。至于身体状况急转直下的原因,不能否定这种可能性:是因为被害人未经医师同意急于出院,自己强行拔掉了治疗用的管子等而引起。对于该案,最高裁判所重视的是,“被害人因被告等人的行为而遭受的上述伤害,其本身就属于可能造成死亡结果的身体损伤”,进而肯定暴力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最高裁判所的该决定没有言及实行行为与介入因素之间的关联性等问题,而重视的是,实行行为本身能否引起本案死亡结果,进而肯定了因果关系,由此可见,本案显然采取的是与前述“大阪南港事件”相同的判断模式。[101]对于判例的这种做法,有观点提出,在本案中,由于被害人的身体状况已经趋于稳定,且恢复健康的可能性也已经增大,因而不应该与死亡结果已不可避免的“大阪南港事件”做相同判断。[102]但是,本案被害人只是身体状况一度趋于稳定,而非完全脱离了生命危险。这样看来,实行行为的危险性虽然得以若干降低,但该危险仍如当初那样在持续,[103]因而本案属于有可能肯定危险的现实化的案件。[104]
四、行为人行为的介入
(一)基本视角
最后,想就介入了行为人本人行为的案件做些探讨。在由同一行为人的复数行为引起了结果的场合,对于能否将复数行为概括地认定为“一系列的实行行为”,近期展开了激烈的探讨。[105]这里无法就此问题展开讨论,但数个行为如果是基于同一主观内容,且时间上接近,就应该可以概括性地评价为一个整体行为。例如,驾车过程中,因没有注视前方,过失撞上被害人,并且,意欲逃离现场时又因操作失误而碾压了被害人。对此,仅将第一个过失行为评价为实行行为,而将第二个过失行为评价为介入行为,这当然也是可行的,[106]但仍然应该承认,存在将整体行为概括性地评价为一个过失实行行为的余地。并且,例如,出于杀人犯意用刀刺杀被害人,由于被害人并未丧命,又用绳索将被害人勒死的,对于这种连续实施故意行为的情形,显然,只要将整体行为概括性地评价为一个杀人罪的实行行为即可。
由此可见,对于连续实施故意行为、连续实施过失行为的情形,可以对行为整体进行概括性评价,因而对于因果关系的判断,不会出现特别的问题。[107]反之,在故意行为与过失行为竞合的案件中,由于行为人的主观意思不同,不可能对两个行为概括性地进行评价,因而应分别评价这两个行为。[108]在该情形下,原则上可以与介入了第三者行为的情形,按照相同视角探讨因果关系。不过,即便能认定,第一行为与第二行为都与结果发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也不应该就同一结果对行为人进行双重处罚。[109]在这种情形下,就应该通过罪数论来避免双重评价。
(二)故意行为→过失行为
故意行为之后,又介入了过失行为的典型案例是“吸入沙土事件”(大判大正12年〔1923年〕4月30日刑集2卷378页)。该案大致案情如下:被告人试图杀害被害人,用麻绳勒被害人的脖子,由于被害人身体不再动,遂以为被害人已死,为了防止罪行败露,将被害人扔在海边的沙滩上,致使当时还活着的被害人终因吸入沙土而窒息死亡。对于该案,大审院认为,出于遗弃尸体之目的的行为“不能切断因果关系”,判定成立故意杀人罪。要认定成立故意杀人罪,实行行为当然是能认定具有杀人犯意的勒脖子的行为(第一行为),但由于实际的死因是由过失行为(第二行为)所形成,要认定第一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作为危险的间接实现型,就要求由该行为诱发介入因素具有通常性。判断是否具有通常性,当然取决于具体案件事实,但基于下述几点考虑,本文认为,完全有可能认定因果关系:
(1)被告人杀害被害人之后,再试图遗弃尸体,这种情况是完全有可能的;(2)第二行为的介入,这属于介入过失行为的情形;(3)误以为被害人已死,继而实施第二行为,也是由第一行为所造成的心理状态所诱发;等等。[110]基于这种前提,就应认定第一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111]
不过,在该场合下,实际引起死亡结果的第二行为也并非完全没有意义。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假设第二行为是借助其他共犯的协助而完成,对该共犯,当然应处以过失致人死亡罪。为此,对于行为人本人实施第二行为的情形,难以否认,从构成要件上讲,该行为该当于过失致人死亡罪。然而,第二行为不过是为了完成杀人计划的行为的一环,也并非是基于新的犯意而实施,因此,第二行为所成立的过失致人死亡罪就被第一行为所构成的故意杀人罪所吸收,不能独立地进行评价。由此可见,如果能认定属于罪数层面上的吸收的一罪,就可以避免出现对死亡结果进行双重评价的问题。
(三)过失行为→故意行为
“猎熊事件”(最决昭和53年〔1978年〕3月22日刑集32卷2号381页)是过失行为之后,又介入故意行为的案件。该案大致案情如下:被告人误将被害人当作熊而举起猎枪射击,致被害人身负重伤处于濒死状态(第一行为),此后,被告人想让被害人早点摆脱痛苦,自己也好逃离现场,遂出于杀人犯意,再次向被害人开枪(第二行为),结果致被害人死亡。对于该案,二审判定,第一行为构成过失伤害罪、第二行为成立故意杀人罪,应数罪并罚。最高裁判所肯定了二审结论。本案案情未必清楚,似乎是第一行为已形成致命伤,即便没有第二行为,被害人不久也会死亡,因而第二行为只是提早了死亡时间。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本文看来,就应采取与“大阪南港事件”完全相同的判断模式,按理应该是成立业务过失致死伤罪。然而,按照这种理解,就会造成将同一死亡结果既归责于第一行为又归责于第二行为的结果。如前所述,如果能认定两罪属于吸收的一罪,就可以避免双重评价的问题,但一般认为,在本案中,第二行为是基于新的犯罪决意而实施的其他行为,难以评价为概括的一罪。[112]为此,裁判所可以采取这样的处理方式:虽坚持对两罪进行数罪并罚,但为了避免对死亡结果的双重评价,在业务过失致死罪中,仅限于死亡结果,由故意杀人罪所吸收,由此认定第一行为仅成立业务过失致伤罪。[113]对于这种处理方式,应该这样理解:没有否定第一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相反是在肯定因果关系的基础之上,出于避免双重评价的要求,仅将被害人的死亡结果评价为(属于更为严重犯罪的)第二行为的结果。[114]
【注释】
[1]参见山口厚:《新判例から見た刑法》,有斐閣2008年第2版,第8页;山中敬一:《刑法総論》,成文堂2008年第2版,第276页;大谷實:《刑法講義総論》,成文堂2012年新版第4版,第221页;高橋則夫:《刑法総論》,成文堂2013年第2版,第132页以下;川端博:《刑法総論講義》,成文堂2013年第3版,第154页以下;佐伯仁志:《刑法総論の考え方?楽しみ方》,有斐閣2013年版,第77页;等等。对此,永井敏雄已经指出,判例对于因果关系的判断,实行行为的“危险性……为死亡这一结果所现实化”,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参见财团法人法曹会编:《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昭和63年度),法曹会1991年版,第77页]。
[2]所谓“危险接近”(near miss),是指飞机之间未保持适当间距而异常接近,处于有发展至空中相撞之危险的状态。有时候,为了避免空中相撞,飞机需要做出急速的躲避动作,但这也会造成乘客死伤。美国联邦航空局(FAA)将危险接近定义为半径150米、高度间距60米以内的接近。——译者注
[3]参见西野吾一:《判解》,载《法曹時報》第65卷第3号(2013年),第209页。其后,就“三菱汽车轮轴脱落事件”,最高裁判所也是以“可以谓之为,是将基于两名被告人之上述义务违反行为的危险予以了现实化”为由,判定存在因果关系(最决平成24年〔2012年〕2月8日刑集66卷4号200页)。
[4]支持“危险的现实化说”的学者,参见山口厚:《刑法総論》,有斐閣2007年第2版,第60页;井田良:《講義刑法学?総論》,有斐閣2008年版,第116页;伊東研祐:《刑法講義総論》,日本評論社2010年版,第86页以下;高橋則夫:《刑法総論》,成文堂2013年第2版,第130页;等等。
[5]主张应限于行为人本人认识或预见到的情况的主观说,现在已经不再有支持者,但近年有学者虽以行为人的认识可能性为基础,但主张通过一般人的认识可能性对此进行修正(参见辰井聡子:《因果関係論》,有斐閣2006年版,第117页),该观点也受到一定关注。
[6]参见団藤重光:《刑法綱要総論》,創文社1990年第3版,第177页;大塚仁:《刑法概説(総論)》,有斐閣2008年第4版,第228页以下;大谷實:《刑法講義総論》,成文堂2012年新版第4版,第207页;川端博:《刑法総論講義》,成文堂2013年第3版,第163页以下;井田良:《講義刑法学?総論》,有斐閣2008年版,第127页;等等。
[7]参见内藤謙:《刑法講義総論》(上),有斐閣1983年版,第279页;松宮孝明:《刑法総論講義》,成文堂2009年第4版,第77页;曽根威彦:《刑法総論》,弘文堂2008年第4版,第74页;等等。
[8]也有学者明确指出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参见今井猛嘉等:《刑法総論》,有斐閣2013年第2版,第79页以下〔小林憲太郎〕;杉本一敏:《因果関係》,载曽根威彦、松原芳博编:《重点課題刑法総論》,成文堂2008年版,第25页;等等。
[9]当然,也有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形:不论是否存在特殊情况,均能认定存在因果进程的盖然性或者通常性(例如,在本文的案件中,行为人实施的暴力行为具有即便是一般人也会死亡的高度危险)。但在那种情形下,设定判断基础几乎没有什么意义,总之,“二阶段”的思考模式并无实际意义。
[10]原本来说,按照作为相当性的内容要求具有因果进程的通常性的观点,只要以因果进程本身作为判断对象即可,因此,将行为之后的介入情况设定为判断基础,再由此判断有无因果关系的相当性,这种工作毫无意义(这种判断基础理论的意义仅限于,将相当性的内容理解为引起结果的相当性的场合)。关于这一点,参见山中敬一:《刑法における客観的帰属の理論》,成文堂1997年版,第28页以下;小林憲太郎:《因果関係と客観的帰属》,弘文堂2003年版,第146页以下。
[11]有学者正面认可了这种理解,参见大谷實:《刑法講義総論》,成文堂2012年新版第4版,第224页。
[12]参见井田良:《犯罪論の現在と目的的行為論》,成文堂1995年版,第85页以下。
[13]另有学者指出,如果将被害人置于大阪南港而不管不顾,就不能说,没有遭受第三者之危害的可能性(参见前田雅英:《刑法総論講義》,東京大学出版会2011年第5版,第200页),但大阪真是如此恐怖的地方吗?与被告人毫无瓜葛的第三者的故意的暴力行为,还是应评价为异常的介入事态,对于这一点,学界观点原则上是一致的。
[14]参见井田良:《犯罪論の現在と目的的行為論》,成文堂1995年版,第79页。
[15]这种观点参见小林憲太郎:《因果関係と客観的帰属》,弘文堂2003年版,第214页注71。另外,也有学者立足于客观归属论的立场,重视第三者之故意行为的介入,而反对有关“大阪南港事件”的最高裁判所判决结论,参见齊藤誠二:《いわゆる『相当因果関係説の危機』についての管見》,载《法学新報》第103卷第2=3期(1997年),第761页以下;安達光治:《客観的帰属論の展開とその課題(4?完)》,载《立命館法学》第273期(2000年),第122页以下。
[16]这种观点参见塩見淳:《法的因果関係(1)》,载《法学教室》第379期(2012年),第53页以下;伊東研祐:《刑法講義総論》,日本評論社2010年版,第79页注6。
[17]参见山口厚:《判批》,载《警察研究》第64卷第1期(1993年),第52页;井田良:《犯罪論の現在と目的的行為論》,成文堂1995年版,第92页以下;等等。
[18]这种观点参见佐伯仁志:《因果関係論》,载山口厚等:《理論刑法学の最前線》,岩波書店2001年版,第16页。
[19]例如,井田良:《犯罪論の現在と目的的行為論》,成文堂1995年版,第92页以下。还有学者是作为结果的属性而重视死因(参见高山佳奈子:《死因と因果関係》,载《成城法学》第63期〔2000年〕,第178页以下),那是通过将形成死因本身作为结果予以把握,而试图维持传统的相当因果关系说。
[20]参见町野朔:《刑法総論講義案Ⅰ》,信山社1995年第2版,第164页以下;山口厚:《問題探求刑法総論》,有斐閣1998年版,第26页以下;高山佳奈子:《相当因果関係》,载山口厚编著:《クローズアップ刑法総論》,成文堂2004年版,第26页以下;松原芳博:《刑法総論》,日本評論社2013年版,第70页;等等。
[21]参见佐伯仁志:《因果関係論》,载山口厚等:《理論刑法学の最前線》,岩波書店2001年版,第12页以下;辰井聡子:《因果関係論》,有斐閣2006年版,第72页以下;等等。
[22]山口厚教授也承认,基于一般预防的理论根据,属于“很简单的内容”,“难以成为具体的标准”。参见山口厚等:《理論刑法学の最前線》,岩波書店2001年版,第17页。
[23]参见林干人:《相当因果関係と一般予防》,载《上智法学論集》第40卷第4期(1997年),第28页以下。
[24]参见島田聡一郎:《相当因果関係?客観的帰属をめぐる判例と学説》,载《法学教室》第387期(2013年),第9页。
[25]参见林幹人:《判例刑法》,東京大学出版会2011年版,第38页以下。
[26]有学者也认为,贡献度与预见可能性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对于相当性的判断,二者都属于不可或缺的要素(参见曽根威彦:《刑法における結果帰属の理論》,成文堂2012年版,第47页以下)。
[27]参见前田雅英:《刑法総論講義》,東京大学出版会2011年第5版,第196页以下。
[28]参见山中敬一:《刑法における客観的帰属の理論》,成文堂1997年版,第85页。
[29]最高裁判所调查官,是指隶属于日本最高裁判所的调查官,根据日本《裁判所法》,负责辅佐最高裁判所的法官审理案件。裁判所调查官原本不具有法官身份,而属于裁判所职员的一种,但最高裁判所的调查官则是由职业法官、法官(通常是东京地方裁判所的法官)担任。至2014年4月当时,最高裁判所有39名调查官。——译者注
[30]参见大谷直人:《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平成2年度),法曹会1992年版,第241页。
[31]当然,由于不过是词语使用上的问题,从影响力或者贡献度的角度来统一整理所有案件,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也有学者持这种理解,例如,鈴木左斗志:《刑法における結果帰責判断の構造》,载《学習院大学法学会雑誌》第38卷第3期(2002年),第285页以下;小林充:《刑法における因果関係論の方向》,载《白山法学》第1期(2005年),第16页以下。
[32]参见佐伯仁志:《因果関係論》,载山口厚等:《理論刑法学の最前線》,岩波書店2001年版,第20页以下。另外,西田典之认为,在由实行行为所“支配”或者“诱发”的场合,就存在介入因素的异常性得以缓和,进而转化为通常性的余地(参见西田典之:《刑法総論》,弘文堂2010年第2版,第107页)。
[33]反之,有学者试图排除规范性考虑,而完全从由某种可能利用的法则性而联系在一起的关系(合法则的条件判断)这种事实性角度,来为因果关系提供根据(参见林陽一:《刑法における因果関係理論》,成文堂2000年版,第231页)。
[34]参见山口厚:《基本判例に学ぶ刑法総論》,成文堂2010年版,第19页以下。另外,岛田聪一郎早在2007年便提出了这种类型化的分类(参见島田聡一郎:《判批》,载《ジュリスト》1332期〔2007年〕,第157页)。
[35]所谓“被精炼的报应思想”,实质上也是同样旨趣(参见西田典之:《刑法総論》,弘文堂2010年第2版,第102、106页)。还有学者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参见島田聡一郎:《相当因果関係?客観的帰属をめぐる判例と学説》,载《法学教室》第387期〔2013年〕,第12页)。
[36]也有学者指出,“姑且不论妥当与否,条件说本身作为一种学说是有可能成立的”,在法律上对因果关系进行限定,属于“有关刑罚权介入的抑制性政策判断”(参见山口厚等:《理論刑法学の最前線》,岩波書店2001年版,第37页)。
[37]有学者指出,“因果关系就是基于整合性(integrity)与道德直觉的反馈”(小林憲太郎:《因果関係に関する近時の判例理論について》,载《立教法学》第81期〔2011年〕,第251页),(也许)基本上指出的是同样的方向。
[38]有学者考虑到裁判员裁判制度下的刑法理论的走向,强调“标准之精致化”的必要性(参见亀井源太郎:《因果関係論に求められるもの》,载《法学研究》第83卷第8期〔2010年〕,第33页以下)。
[39]有学者通过“判断(1)在立足于行为当时所预测到的(事前判断)‘典型范围’之内,(2)是否包含立足于裁判当时所确定的‘实际过程’这种二阶段结构”来说明判例的立场(参见杉本一敏:《因果関係》,载曽根威彦、松原芳博编:《重点課題刑法総論》,成文堂2008年版,第27页),想必也是同样旨趣。另见杉本一敏:《相当因果関係と結果回避可能性(6?完)》,载《早稲田大学法研論集》第106期(2003年),第152页以下。
[40]不过,在实际的案件处理中,由于业已存在具体的因果进程以及所实际引起的结果,因而是采取时间性回溯的形式,考察这种危险性是否内在于实行行为。为此,只要探讨由实际引起的结果所实现的危险(例如,逃跑过程中的被害人的摔倒)是否包含在实行行为的危险之中即可,再探讨其他的危险内容,则毫无意义。
[41]关于这一点,参见松原芳博:《刑法総論》,日本評論社2013年版,第77页注31。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将实行行为的危险性与介入因素的异常性作为个别独立的要件而并列把握的做法,就未必合适。
[42]作为实行的着手之认定基础的危险性,当然是在结果被现实化之前进行判断,无论是什么内容,只要是在实行行为的阶段发生了具体的危险即可。反之,作为实现危险之起点的实行行为的危险,就仅限于与实际引起的结果相对应的内容。
[43]关于这一点,参见佐伯仁志:《刑法総論の考え方?楽しみ方》,有斐閣2013年版,第77页以下;島田聡一郎:《相当因果関係と客観的帰属》,载《法学教室》第359期(2010年),第8页。
[44]对相关判例的概述,参见西田典之等编:《注釈刑法(1)》,有斐閣2010年版,第313页以下〔小林憲太郎〕。
[45]参见曽根威彦:《刑法における結果帰属の理論》,成文堂2012年版,第38页以下。
[46]指出此问题的学者还有,佐伯仁志:《因果関係論》,载山口厚等:《理論刑法学の最前線》,岩波書店2001年版,第12页;山口厚:《新判例から見た刑法》,有斐閣2008年第2版,第267页注19。
[47]参见佐伯仁志:《因果関係論》,载山口厚等:《理論刑法学の最前線》,岩波書店2001年版,第14、25页。另见佐伯仁志:《刑法総論の考え方?楽しみ方》,有斐閣2013年版,第75页以下。
[48]例如,山口厚等:《理論刑法学の最前線》,岩波書店2001年版,第53页以下〔井田良〕;辰井聡子:《因果関係論》,有斐阁2006年版,第126页以下;今井猛嘉等:《刑法総論》,有斐閣2013年第2版,第84页〔小林憲太郎〕;塩見淳:《法的因果関係(2)》,载《法学教室》第380号(2012年),第74页;等等。
[49]驾驶小型四轮卡车的被告人因过失引起事故,造成坐在汽车后部货厢的被害人死亡,但被告人无法认识到被害人坐在后部货箱这一事实,对此,最高裁判所做出了认定被告人存在过失的判断(最决平成元年〔1989年〕3月14日刑集43卷3号262页),这显然是以存在因果关系作为当然的前提。参见安廣文夫:《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平成元年度),法曹会1991年版,第98页注释20。不过,也有学者基于重视引起结果的经验性、通常性的立场,认为在被害人的存在可以谓之为“经验法则上稀有的情况”的场合,有否定因果关系的余地(参见西田典之:《刑法総論》,弘文堂2010年第2版,第267页)。
[50]当然,在危险性的判断中,有时也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情况,但那(例如,是否存在开枪的意思等)属于“意图实施后续行为的意思”,而不是说,纯粹的事实认识本身会对危险性造成影响。
[51]参见佐伯仁志:《刑法総論の考え方?楽しみ方》,有斐閣2013年版,第65页注17。
[52]参见平野龙一:《犯罪論の諸問題(上)総論》,有斐閣1981年版,第41页;林幹人:《相当因果関係と一般予防》,载《上智法学論集》第40卷第4期(1997年),第38页以下;等等。
[53]参见山中敬一:《刑法総論》,成文堂2008年第2版,第268页;高橋則夫:《刑法総論》,成文堂2013年第2版,第125页;等等。
[54]关于这一点,参见山口厚等:《理論刑法学の最前線》,岩波書店2001年版,第39页。
*本文原载于日本《法学教室》2014年第5期(总第404期)。
[55]关于这一点,参见林幹人:《判例刑法》,東京大学出版会2011年版,第31页以下。
[56]参见辰井聡子:《因果関係論》,有斐閣2006年版,第114页以下;等等。
[57]二审判决(大阪高判平成4年〔1992年〕3月11日刑集46卷9号697页)也做出了同样的判断。另见井上弘通:《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平成2年度),法曹会1992年版,第228页注12。
[58]参见佐伯仁志:《刑法総論の考え方?楽しみ方》,有斐閣2013年版,第71页。
[59]松原芳博教授也指出了同样的问题,参见松原芳博:《刑法総論》,日本評論社2013年版,第78页。对此,佐伯仁志教授也指出,在被害人采取了不适当的行为的场合,要认定因果关系,“被害人等的行为的不适当的程度,属于通常有可能的程度,这一点很重要”。参见佐伯仁志:《因果関係論》,载山口厚等:《理論刑法学の最前線》,岩波書店2001年版,第22页。
[60]林阳一教授认为,未受实行行为之影响而介入的危险(一般性危险),如果单独引起了结果,对此应否定因果关系(参见林陽一:《刑法における因果関係理論》,成文堂2000年版,第276页以下),想必其旨趣在于,只有第(1)点的视角才是重要的。另外,小林宪太郎副教授也不承认第(2)点的视角存在独立意义(参见西田典之等编:《注釈刑法(1)》,有斐閣2010年版,第319页〔小林憲太郎〕)。
[61]就本案而言,事实上,也很难想象,另外还存在可致被害人死亡的其他因果进程。
[62]持这种批判观点的有,曽根威彦:《判批》,载《判例評論》第360期(《判例時報》第1294期)(1989年),第55页;町野朔:《犯罪論の展開Ⅰ》,有斐閣1989年版,第246页;等等。
[63]关于这一点,参见林陽一:《判批》,载《法学教室》第97期(1988年),第84页。
[64]重视该事实的观点,参见内田文昭:《判批》,载《ジュリスト》第935期(1989年),第142页;佐久間修:《判批》,载唄孝一等编:《医療過誤判例百選》,有斐閣1996年第2版,第221页;等等。不过,根据一审的事实认定,被害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建筑师,其妻在医院工作,是临床检查技师。如果考虑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的关系等具体事实,就有必要考虑这些凸显介入因素之异常性的事实,为此,因果关系的判断会变得更加微妙。
[65]参见永井敏雄:《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昭和63年度),法曹会1991年版,第273页以下。
[66]关于这一点,参见臼木豊:《判批》,载《警察研究》第61卷第1期(1990年),第55页。
[67]参见深町晋也:《判批》,载《ジュリスト》第1182期(2000年),第100页。
[68]参见佐伯仁志:《因果関係論》,载山口厚等:《理論刑法学の最前線》,岩波書店2001年版,第22页;塩見淳:《判批》,载《法学教室》第157期(1993年),第95页。
[69]井上弘通调查官也指出了这一点。参见井上弘通:《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平成2年度),法曹会1992年版,第235页以下。
[70]避免义务中的避免对象不是现实引起的结果,而是一般所能预想到的危险(或者结果),因而出现了这种不一致。正如井上调查官所举的例子那样(参见井上弘通:《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平成2年度〕,法曹会1992年版,第238页),如果被害人遭到正好在案发现场附近的鲨鱼的袭击,也存在否定因果关系的余地。
[71]在前述“日航飞机危险接近事件”中,(尽管判断内容实质上存在很大部分的重复)对于过失犯的实行行为性、实行行为与该案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发生的预见可能性,就是个别地加以认定。
[72]山口雅高调查官也认为,如果被害人的逃离方法特别不自然的话,即便是在被告人暴力的影响之下所选择的逃离方法,仍有否定因果关系的余地。参见山口雅高:《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平成15年度),法曹会2005年版,第427页。
[73]参见杉本一敏:《相当因果関係》,载松原芳博编:《刑法の判例〔総論〕》,成文堂2011年版,第17页以下。深町晋也也持该观点(参见深町晋也:《判批》,载《法学教室》第281期〔2004年〕,第149页)。
[74]在被害人逃离途中,附近有游戏厅、大规模的商业设施,似乎有不少适于被害人藏身的地方。参见山口雅高:《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平成15年度),法曹会2005年版,第423页注18。
[75]参见林陽一:《刑法における因果関係理論》,成文堂2000年版,第271页。
[76]山中敬一教授认为,本案被害人的行为“属于心理上受到准强制的不合理的行动,同时,作为与被害人的动机相关联的行为,又属于合理的行动”(参见山中敬一:《刑法総論》,成文堂2008年第2版,第290页)。
[77]当然,在这些场合,应该以对死亡结果的发生存在预见可能性为必要,为此,在被害人对自己已被逼到那种境地这一事实缺乏认识可能性的场合,对于加重结果,就有否定存在过失的余地。
[78]参见多和田隆史:《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平成18年度),法曹会2008年版,第233页。
[79]参见高橋則夫:《刑法総論》,成文堂2013年第2版,第141页;等等。
[80]并且,根据辩护人的上告意见(参见最决平成18年〔2006年〕3月27日刑集60卷3号390页),被告人当时可能打开了尾灯,本案的一审、二审也均未否定该事实。
[81]由于拘禁行为并非不可或缺,那么,还可以进一步设想这样的情形:被告人违章停车时,同乘的其他人并未一同下车而是继续留在车内后座,如果遭遇交通事故而造成了同乘的人死亡的,按照这种逻辑,似乎也难免不成立业务过失致死罪(如果追尾事故属于“勉强有可能发生”的事故,想必也能认定存在预见可能性)。
[82]参见松原芳博:《刑法総論》,日本评论社2013年版,第82页。另外,辰井聪子也从必须存在诱发或者利用介入因素的关系这一角度,反对最高裁判所的本决定的结论(参见辰井聡子:《判批》,载《刑事法ジャーナル》第7号〔2007年〕,第72页)。
[83]岛田聪一郎所谓的“行为人所设定的危险状况,会引起结果的发生”(島田聡一郎:《相当因果関係?客観的帰属をめぐる判例と学説》,载《法学教室》第387期〔2012年〕,第11页),实质上也是同样旨趣。另见井田良:《判批》,载西田典之等编:《刑法判例百選Ⅰ(総論)》,有斐閣2008年第6版,第31页;山中敬一:《刑法総論》,成文堂2008年第2版,第292页。
[84]参见山口厚:《刑法総論》,有斐阁2007年第2版,第68页。
[85]参见島田聡一郎:《正犯?共犯論の基礎理論》,東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版,第89页以下;高山佳奈子:《相当因果関係》,载山口厚编著:《クローズアップ刑法総論》,成文堂2004年版,第7页以下;等等。不过,如果认为正犯与共犯对因果关系的内容的要求可能不同,就完全有可能将溯及禁止论作为因果关系的内容来理解。
[86]接下来的问题是,否定成立既遂犯的正犯,那么,究竟是追究(如果介入行为在直至介入的阶段已经成立未遂犯的话)未遂犯的正犯的罪责还是既遂犯的共犯的罪责呢?不过,要认定成立共犯,必须是物理性地或者心理性地促进了第三者的故意且有责的行为,并且,还需要对此存在认识,但介入第三者行为的场合,大多缺少这些要件,因而不能成立既遂犯的共犯,而只能是成立未遂犯的正犯。关于这一点,参见島田聡一郎:《正犯?共犯論の基礎理論》,東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版,第99页以下。
[87]前述大阪南港事件就正是其适例。关于这一点,参见島田聡一郎:《正犯?共犯論の基礎理論》,東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版,第348页以下。
[88]那些承认故意且有责的行为的“背后的正犯”的明文规定,也是这种容忍例外的态度的体现。例如,现场从业人员实施了故意且有责的违反行为的场合,根据双罚制,该从业人员的管理者就作为过失正犯而受到处罚。作为溯及禁止论的例外情形,松宫孝明教授举了看守者援助脱逃罪(第101条)的例子(参见中山研一等:《レヴィジオン刑法3》,成文堂2009年版,第56页〔松宫孝明〕)。
[89]这里无法详尽探讨,但这种理解对于原因自由行为(尤其是在心神耗弱状态下实施了结果行为的情形)、构成要件的提前实现的问题,均有一定影响。
[90]调查官认为,从属于最终死因的伤害的部位来看,致命伤是由第三者的介入行为所引起的盖然性很高。参见海老原震一:《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昭和42年度),法曹会1969年版,第285页。
[91]假定我们还需要研究本案中的第二行为人的罪责,在该情形下,如果第二行为人的行为提早了死亡时间这一点很清楚,就要肯定成立伤害致死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对此理解,辰井聪子指出,一边认定提早死亡时间的行为与实际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却又认为该行为属于“影响力很小”的行为,这之间显然存在矛盾(参见辰井聡子:《因果関係論》,有斐閣2006年版,第186页)。然而,第二行为的影响力很小这一判断,完全是考虑到与第一行为之间的关系而进行的相对判断,这并不能左右第二行为本身引起了(死亡时间被提早的)死亡结果这一结论。
[92]参见井田良:《犯罪論の現在と目的的行為論》,成文堂1995年版,第89页以下;高山佳奈子:《死因と因果関係》,载《成城法学》第63期(2000年),第178页以下;等等。
[93]参见林陽一:《刑法における因果関係理論》,成文堂2000年版,第324页以下。
[94]参见伊東研祐:《判批》,载《判例評論》第391期(《判例時報》第1388期)(1991年),第64页;山口厚:《問題探求刑法総論》,有斐閣1998年版,第25页;等等。针对这一批判,也许存在这样的反驳:若死亡时间大幅不同,死因也自然不同。但这种理解本身无异于是说,死因这一概念未必是一个明确的法律概念。另见山中敬一:《判批》,载《ジュリスト》980期(1991年),第143页。
[95]参见山口厚:《判批》,载《警察研究》第64卷第1期(1993年),第51页;島田聡一郎:《正犯?共犯論の基礎理論》,東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版,第350页;西田典之:《刑法総論》,弘文堂2010年第2版,第108页以下;等等。并且,平野龙一也认为,在即便没有介入因素“想必也会马上死亡的场合”,应肯定因果关系(参见平野龍一:《犯罪論の諸問題(上)総論》,有斐閣1981年版,第42页)。小林充将此观点更进一步,承认抽象化到构成要件结果的层面(小林充:《刑法における因果関係論の方向》,载《白山法学》第1期〔2005年〕,第14页以下)。
[96]参见林陽一:《刑法における因果関係理論》,成文堂2000年版,第140页注13;井田良:《犯罪論の現在と目的的行為論》,成文堂1995年版,第85页;等等。
[97]参见小林充:《刑法における因果関係論の方向》,载《白山法学》第1期(2005年),第14页。该案是小林充教授担任法官之时实际负责的案件(东京地判昭和34年〔1959年〕8月29日判例集未刊登),关于判例的详细介绍参见该文第28页以下。
[98]参见小阪敏幸:《因果関係(1)》,载小林充、植村立郎编:《刑事事実認定重要判決50選(上)》,立花書房2013年第2版,第53页以下。另见中森喜彦:《判批》,载西田典之等编:《刑法判例百選Ⅰ(総論)》,有斐閣2008年第6版,第33页。
[99]参见山口厚:《新判例から見た刑法》,有斐閣2008年第2版,第14页。
[100]山口厚教授也承认存在这种可能性(参见山口厚:《新判例から見た刑法》,有斐閣2008年第2版,第14页)。而且,在该情形下,并不存在被害人死亡的危险,因而原本连未遂犯也不能成立;倘若考虑到,如果出现某种情况,就会出现无法接受适当治疗的事态,也完全有可能认定存在未遂犯的危险。
[101]参见島田聡一郎:《判批》,载《ジェリスト》第1310期(2006年),第172页。
[102]参见林幹人:《判例刑法》,东京大学出版会2011年版,第40页以下。基于这种理解,林干人教授认为,在被害人的行为可以纳入预见可能的范围之内的限度内,能肯定因果关系。反之,高桥则夫教授则认为,难以肯定因果关系(参见高橋則夫:《刑法総論》,成文堂2013年第2版,第138页)。
[103]关于这一点,参见前田厳:《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平成16年度),法曹会2006年版,第148页以下。
[104]另外,如果以不仅考虑死因也同时考虑死亡时间而判断结果的同一性的观点为前提,由于本案被害人尚未脱离死亡危险,存在因某种情况而引起身体状况急转直下的可能性,因而尚处于任何时间死亡都不奇怪的状态之下,为此,通过在一定程度幅度内,认定(假如没有介入行为之时)假定上的死亡时间,也有可能肯定因果关系。
[105]最近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仲道祐樹:《行為概念の再定位——犯罪論における行為特定の理論》,成文堂2013年版;深町晋也:《“一連の行為”論について》,载《立教法務研究》第3期(2010年),第93页以下。
[106]采取这种判断结构的判决,参见大阪地判平成3年(1991年)5月21日判タ773号265页。鉴于第一行为与第二行为的注意义务的内容不同,像这样将二者分别视为独立的过失行为的做法,也许更为合适。不过,即便如此理解,但最终仍应将两个行为理解为概括的一罪,因而与将二者视为一系列的过失行为相比,实质上并无多大差异。
[107]参见齋野彦弥:《基本講座刑法総論》,新世社2007年版,第93页。
[108]参见深町晋也:《“一連の行為”論について》,载《立教法務研究》第3期(2010年),第123页;仲道祐树:《行為概念の再定位——犯罪論における行為特定の理論》,成文堂2013年版,第77页以下。
[109]如果第一行为与第二行为是由不同的人所实施,就完全有可能让他们都对结果承担罪责。这里的问题在于,就同一结果,对行为人进行双重处罚是否妥当。反之,高山佳奈子教授则提倡下述解释论:(故意犯自不用说)对过失犯也应否定同时犯,将针对同一结果的正犯限于1名正犯(高山佳奈子:《複数行為による事故の正犯性》,载井上正仁、酒卷匡编:《三井誠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有斐閣2012年版,第179页以下)。
[110]参见佐伯仁志:《刑法総論の考え方?楽しみ方》,有斐閣2013年版,第276页。反之,曾根威彦则主张采取上述处理方式:分别认定第一行为属于故意的未遂犯、第二行为属于过失的既遂犯,然后按照数罪并罚来处理(参见曽根威彦:《刑法における結果帰属の理論》,成文堂2012年版,第290页以下)。
[111]当然,本案被告人还存在因果关系的错误的问题,但这里采取通说观点,即相当因果关系(或者危险实现)范围之内的错误不阻却故意。
[112]参见山口厚:《基本判例に学ぶ刑法総論》,成文堂2010年版,第19页。
[113]关于这种理解,参见樋口亮介:《判批》,载西田典之等编:《刑法判例百選Ⅰ(総論)》,有斐閣2008年第6版,第23页。另见塩見淳:《法的因果関係(2)》,载《法学教室》第380期(2012年),第76页。
[114]为此,按照广泛肯定混合的概括的一罪的观点,即便是介入了其他意思决定的场合,如果是同一机会之下针对同一法益的侵害行为,就认定属于概括的一罪(吸收的一罪),为此,就存在认定第一行为成立业务过失致死罪,然后再作为概括的一罪来处理的可能性。也有学者暗示属于概括的一罪,参见山火正則:《判批》,载《警察研究》第55卷第2期(1984年),第88页;山中敬一:《行為者自身の第二行為による因果経過への介入と客観的帰属》,载《福田平·大塚仁博士古稀祝賀刑事法学の総合的検討(下)》,有斐閣1993年版,第2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