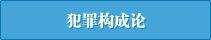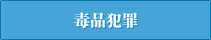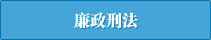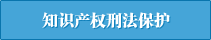克劳斯·罗克辛:对批判立法之法益概念的检视
克劳斯·罗克辛:《对批判立法之法益概念的检视》,陈璇 译,载《法学评论》2015年第1期。
内容提要: 刑法的任务在于法益保护。德国等国宪法法院的多个判决说明,批判立法的法益概念在确定某一罪刑规范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上,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尽管作为一种最高法律原则,法益概念必然具有抽象性,但它可以通过一系列规则得以明确化。承认法益概念具有批判立法的功能,这与立法者享有一定创造空间的事实之间并不矛盾。行动犯所侵犯的同样也是法益,而不是感情。法益概念不仅具有刑事政策上的意义,而且还会对立法者产生约束力。即合比例性原则是判定某一规定是否合宪的决定性标准,而该原则的内容需要通过法益概念来得到具体化。
关键词: 法益/立法/宪法法院/合比例性原则
我们能否把国家的刑罚权限制在对法益的侵害和危险之上,从而为其设定一条边界?最近十年间,这个问题在德国重新成为激烈争论的对象。①黑芬德尔(Hefendehl)②曾对2006年以前的最新发展状况进行过描述。但在此之后,相关争论的意义变得越发重要起来,因为联邦宪法法院③于2008年在一份判决中指出,法益原则无法为立法者的处罚权限划定边界。我在2010年④发表的《论关于法益之争的最新发展》一文中,对该判决详细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坚持认为法益思想具有批判立法的功能。
一、导言
刑法的任务能否被界定为法益保护?这个问题在国外也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和充满争议的反响。例如,巴西加卢波(Bacigalupo)⑤写道,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人们认为“法益概念发挥着关键性的合法化功能”。有一个事实能够证实该论断,即罗马诺(Romano)、⑥莱诺·纳瓦雷特(Polaino Narvarrete)⑦和金贝尔纳特(Gimbernat)⑧在2011年为我创作的祝寿论文中,对法益的功能展开了探讨。同样,该问题在希腊也广受讨论。安德罗拉基斯(Androulakis)⑨认为法益原则在限定可罚性方面不具有任何能力,但凯阿法-格班迪(Kaiafa-Gbandi)⑩却主张:“德国刑法学中有一种理论认为,法益是一种基本要素,它不仅能说明可罚性的根据,而且其主要作用是对可罚性加以限定;该理论……是德国刑法学为欧洲法律文化所奉上的最为重要的馈赠之一。”
不过,法益概念在别的一些国家,例如在法国和美国却毫无影响。但美国刑法学者杜贝尔(Dubber)(11)毕竟还强调,“假如美利坚合众国的学说、立法和判例能以一个体系统一的法益概念为其根据,那将会是令人鼓舞的。”盎格鲁撒克逊刑法所提出的“损害原则”(Harm Principle)(12)——即把刑法的制裁仅限定在制造损害的举动方式上——与法益保护原则具有相似之处。
由于本课题具有现实性,而且所有相关的问题又一如既往地极富争议性,所以我有理由再次涉足法益问题。当然,我不打算重复我先前已有的论述,故本文总体上只对新近文献中出现的、我必须对之表态的那些建议和批判点展开探讨。
在此,我给自己提出了四个问题:(1)刑法究竟是否具有(法益)保护的任务,还是说刑法应当仅仅确证规范的效力?(2)如果我们认为刑法的任务在于保护法益,那我们如何才能确定法益概念的内容,从而使其能够得出具体的结论呢?(3)行动犯(Verhaltensdelikt)(13)(保护情感的犯罪)的存在有其必要性,这种必要性是否说明法益理论是错误的?(4)刑法应当限定在对法益的保护之上,这一要求只具有刑事政策上的意义?还是说至少在某些情形中,该要求也能决定某一罪刑规定是否具有合宪性和在法律上是否有效?
二、刑法所追求的是法益保护还是对规范效力的确证?
要承认法益保护思想具有划定刑法界限的功能,首要的前提当然是要承认刑法的任务在于保护法益。但这样的观点也不是没有争议的。雅各布斯(Jakobs)(14)和他的弟子们主张,刑法保护的不是法益,而是规范的效力。例如,对于杀人罪来说,重要的“不是伤害被害人的肉体,或者消灭他的意识,而是行为隐藏着一种客观化的看法,即认为我们无需去尊重……身体和意识。这一看法对规范……进行了否定。因此,犯罪就是对规范的否认”。(15)据此,受到保护的并不是我们称之为法益的那个东西:作为经验性事实的生命,而仅仅是禁止杀人的命令(规范的效力)。“罪行是对规范效力的损害;而刑罚则是对规范效力的确证。”(16)
但这种观点是以一种夸张的规范主义为其基础的。(17)刑罚有助于稳固规范,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便说这——与雅各布斯的观点相左——并非刑罚的唯一目的。然而,我们不能为了稳固规范而稳固规范,稳固规范的作用实际上在于防止个人或者社会在将来遭受现实的损害(即法益侵害)。因此,对规范的稳固最终服务于法益保护,如果没有这个目的,它将变得毫无意义。
针对雅各布斯的构想,西班牙学者也提出了可供比较的批判。米尔·普伊格(Mir Puig)(18)写道:“刑事政策的法益概念认为,只有当某一罪刑规范的功能是保护那些值得保护的价值时,它才具有合法性;而雅各布斯的观点却以某种方式把这一基点颠倒了过来,并且使规范成了本身就具有合法性的、受到刑法保护的对象:规范本来是一种工具,其合法性必须来自于它所追求的目的,但现在规范却成了使其自己具有合法性的目的本身。”他正确地警告说,这样一来,法益保护思想所具有的限制作用就会荡然无存。即便是像波莱诺·纳瓦雷特(19)这样与雅各布斯持如此相近立场的学者,也提出了同样的论据,他说:“刑法保护法益,就是为了预防对该利益造成侵害,它由此也就确证了作为社会结构之组成部分的规范的权威性。”“规范所追求的目的……并不在于保护它自己,而是在于保护它所包含的利益与价值。”(20)
因此,对于那种以刑罚具有确证规范效力的作用为由,否认刑罚和刑法具有保护法益之功能的意见,我们可以搁置不谈了。
三、一个具有实际效用的批判立法的法益概念是否可能存在?
(一)对批判立法之法益概念的重述
我在自己的教科书(21)中曾说道:“刑法的任务在于,使其公民在由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获得维护的前提下,自由而和平地共同生活在一起。如果我们把这项任务归结为法益保护,那么法益指的就应当是所有的这些事实和目的设定,它们对于个人自由地发展自己,对于个人实现其基本权利,以及对于建立在该目标观念之上的国家制度发挥其作用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长期以来,这种观点——先不论某些差异点——都获得了许多著名学者的赞同,我在此处只能概括地提到他们。(22)但即便是在最近几年里,也再度出现了至关重要的支持者,其中我特别想提及的是许内曼(Schünemann)、(23)施泰因贝格(Steinberg)、(24)M.Heinrich(M.海因里希)、(25)弗里斯特(Frister)、(26)和卡斯帕(Kaspar)。(27)关于他们更为深入的思想,我在后文中还会加以讨论。
从这种法益理论出发,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个至关重要的、对自由起着捍卫作用的结论,即如果罪刑规定既不是为了保护个人的自由发展,也不是为了保护实现个人自由发展的社会条件(例如正常的司法和国家行政),那么该规定就不具有合法性。比如,弗里斯特也是从这个意义出发说:(28)“不论是个人的法益,还是公共的法益,它们在最终的结果上都是为了保障个体具有发展的可能性而服务的。唯一的区别仅仅在于,侵犯个人法益的行为直接损害了某个特定人的发展可能性,而侵犯某种公共法益的行为则间接地损害了所有人的发展可能性。”弗里斯特由此得出结论:(29)立法者的创造空间从以下这方面来看是存在界限的,即“一个绝不会对他人的发展可能性造成损害的举动,不能被评价为刑法上的不法”。
(二)这种法益概念是否过于不明确,以至于无法为刑法划定界限?
批判立法之法益概念的反对者经常提出的理由是,这一概念过于模糊,故不具有实际的效用。例如,杜贝尔(30)在对各种不同的、相互对立的构成要件进行整理后,得出结论:“罗克辛……关于法益的理论”“最终”被证明“确实不起实际作用”。2011年,施图肯贝格(Stuckenberg)还写道:(31)“‘法益保护’这个惯用语所追求的目标在于实现合理的刑事政策,以及实现自由和人道的刑法,这无疑是值得向往的。但是,它在学术上却并不是一个具有分析潜力的概念,相反,它是用来掩盖居于其背后之价值态度的工具,这些价值态度有时是混乱不清的,而且与其说我们精确地界定了它们,还不如说我们是感觉到了它们。”我将从四个方面对这种以及与之相类似的批判意见进行反击:
1.法益概念对于解决现实的法律问题所具有的意义
认为法益概念不具有任何重要的实际意义的论断,是错误的。我想通过六个例子来阐明这一点。在这些实例中,(不仅是德国的)立法或者宪法法院的判例都必须讨论刑罚是否得到允许的问题,而且其中有五个例子依然是今天人们讨论的焦点。
历史最为悠久的争议问题,涉及的是成年人之间同性恋举动的可罚性。一直到1969年,这种举动在德国都是受到处罚的。德国政府于1962年为创制新刑法典而拟定的刑法草案,试图保留该举动的可罚性,而且我们的宪法法院也确定这种可罚性是合宪的。(32)但显而易见的是,当行为人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在私人领域内实施这种举动时,该举动并没有损害到任何人的发展自由,也没有以任何的方式对人们自由的共同生活造成干扰。因此,对立法持批判态度的法益概念会提出一个要求,即成年人之间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所实施的同性恋行为不可罚。
德国的立法者对特别是由刑法备选草案的作者们所带来的改革思潮表示了赞同,(33)并于1969年废除了关于同性恋的罪刑规定。有批评者主张,之所以出现这种立法上的变革,不是因为批判立法的法益概念获得了承认,而是因为在同性恋行为是否当罚的问题上,公众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但是,金贝尔纳特从自身的观念出发(他当时身居德国),十分正确地否定了这一说法。(34)如果说观念在现今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这种变化是当时改革性政策所带来的结果,而不是其前提条件。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只有在刑罚的威吓不是以需要保护的法益,而是以某种纯粹的道德观为其基础的情形中,关于某种举动之当罚性的观念才能以相对较快的速度发生改变。对于针对身体和生命的犯罪行为,对于剥夺自由或者盗窃犯罪来说,观念的变迁会导致该类行为不可罚,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些犯罪都是以法益为其基础的,而社会无法放弃对这些法益的保护。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为了自用而持有某种毒品之行为的可罚性。(35)该行为同样也不会对其他人造成任何损害,故批判立法之法益概念的支持者们也普遍地认为该行为是不可罚的。我们的宪法法院也不得不对该问题加以研究,(36)它坚持认为该行为具有可罚性,但又附带指出,对于那些轻微的案件应当免除处罚。这一判决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但却产生了法律上的不明确性。假如宪法法院把该规定解释为无效的话,那么这种不明确性本来是可以得到避免的。与此相反,2009年8月25日,阿根廷的宪法法院判定,关于禁止为了自用而持有毒品的罪刑规定是违宪的。(37)
第三种情形涉及生者的器官捐赠问题,宪法法院同样也处理过这种案件。根据德国《器官移植法》(38)的规定,只有在为了救助有亲属关系和紧密关系之人的情况下,生者的器官捐赠行为才能得到允许。因此,如果某人基于利他主义,想通过捐赠一枚肾脏的方式去拯救一名陌路之人——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匿名的——的生命,那么这种捐赠是不被许可的。若某位医生违反该禁令摘取了器官,则对其应以犯罪论处。(39)由于在这种情形中,根本不存在对他人的损害,器官捐赠甚至特别有助于实现公共利益,故对该行为加以处罚的规定,缺少法益保护方面的合法性根据。
尽管如此,我们的宪法法院(40)还是认为该规定是容许的。按照法院的意见,虽然自陷危险的行为是“对基本权利之自由的行使”,但这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即“保护人们不对自身造成某种较大的人身损害,这是一个涉及公共福利的正当要求”。
然而,当这种观点被运用于解决具体案件时,就会出现双重错误。因为:一方面,没有任何人会主张,国家可以用刑罚去对某种有损健康的生活方式进行威吓。另一方面,只要某个捐献器官的行为是在经过了谨慎的医学检查和会商后进行的,那它就不会带来“较大的人身损害”。只有一枚肾脏的人,其寿命并不会比公民的平均寿命短。因此,宪法法院的这个判决受到了广泛的反对,它或许会导致法律条文的变更。
第四个,也是近来讨论得最多的情形涉及兄妹之间的乱伦行为,就这种情形而言,争论的中心就是批判立法的法益保护概念。根据德国法,这种乱伦行为是受到处罚的。(41)同样地,如果兄妹间的这种行为是在没有受到任何胁迫、完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进行,并且双方也具备完全的责任,那该行为就不可能对个人的发展可能性造成任何损害,故法益保护原则要求必须认定该行为无罪。
然而,我们的宪法法院在2008年做出判决,认为该罪刑规定“是与基本法相一致的”。(42)在该判决中,宪法法院首次针对法益保护原则可能具有的限制刑法的功能发表了看法。它认为,我们不能“援引……法益来限制”立法者的权限。(43)关于罪刑规范所追求之目的的要求,“是无法从刑法上的法益理论中推导出来的”。(44)但与此同时,法院又试图找出由该罪刑规定所保护的法益(家庭、性的自我决定权以及后代的健康),这种做法与上述见解是自相矛盾的。由于法院所提出的论据不堪一击,所以该判决遭遇了普遍的反对。(45)
第五个问题从法益保护的角度来看也同样极具争议性,它涉及的是否认历史事实的行为,有的国家在某些情形下对该行为加以处罚(例如否认纳粹对犹太人实施的大屠杀,或者其他种族灭绝)。根据刑法典第130条第3款的规定,对纳粹主义统治期间所出现的种族屠杀加以否认或者美化的行为,如果它能够对公共的和平造成破坏,或者它是在公共场合或在集会上实施的,那就应当受到处罚。欧盟于2007年做出的一项框架性决议(46)也要求,对于公开赞许、否认或者严重美化种族谋杀罪、反人类罪和战争罪的行为,应当予以惩处。
与此相反,西班牙宪法法院于2007年11月7日做出判决,认定对否认种族谋杀的行为加以处罚的做法,是违反宪法的。(47)法国的立法者认为,土耳其于1915—1917年间在亚美尼亚犯下了种族谋杀罪。2007年2月28日,法国宪法委员会,即该国最高的宪法机构认定,对否认该罪行的行为加以处罚,这样的做法侵犯了言论自由,并且不当地干涉了历史学的研究工作,所以是违宪的。
从批判立法的法益保护原则看来,对赞许这些罪行的行为加以处罚,这种做法完全是正当的。因为,对于那些如今依然生活在我们中间,并曾经受到该罪行残害的群体来说,这种行为对他们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但是在德国,根据刑法典第130条第1款的规定,这样的情形本来就已经构成针对某一部分公民挑起仇恨的行为,故应当受到处罚。相反,只要否认历史事实的行为不带有煽动和贬低的成分,那我们就只能认为该行为不具有法益侵害性。(48)因为,言论表达的自由包含了宣示荒谬观点的行为。假如这些情况在历史上是存在争议的,那么对其做出裁决的就只能是历史学,而不是刑法。反之,假如这些情况——例如纳粹主义犯下的暴行——已经得到了证实,那么考虑到社会的舆论环境,以令人信服的方法对怀疑这些事实的言论公开加以驳斥,这比对其处以刑罚要好,因为处以刑罚的做法会给大屠杀的否认者或美化者提供机会,让他们得以把自己装扮成烈士,或者使他们能够宣称,国家通过刑法压制了历史学领域内的争论。
我想谈到的最后一项与法益无关的规定,是青少年淫秽物品罪(刑法典第184c条)。这一构成要件是根据欧盟的框架性决议,于2008年引入到德国刑法典当中的。(49)我只想论及该条第4款的规定。根据这一规定,“若某人着手获取对反映某种事实情况的青少年淫秽文书的持有,或者持有了这种文书”,则应以犯罪论处。由于根据刑法典第11条第3款的规定,图片等同于文书,故如果一名已满18周岁的人在征得其17岁的女友同意后,从后者处获得了她具有露骨的性内容的照片,那么该行为是可罚的。(50)既然法律容许这两人发生性关系,那我们就难以理解,为什么这名女友不能允许其男友获得,或者直接向他赠送这些私密的照片呢?曼弗雷德·海因里希(51)正确地指出,这种做法“从法益保护的角度来看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类似的例子还会更多。在我看来,从上文所描述的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得出结论:杜贝尔的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即(52)“在罗克辛以法益为标准所进行的测试中被认定为不合格的那些犯罪构成要件,要么是少见的,要么是过时的”。与他的看法相反,上文所述的所有那些情形都属于学术上激烈争论的对象,而且,各个不同国家的宪法法院甚至也都对其进行了讨论,除了最后一个例子之外。对于我所举的关于青少年淫秽物品的情况,之所以还没有法院的判决,仅仅是因为这条规定生效的时间不长。在上文论述的这些犯罪构成要件中,只有一个是“过时的”,因为成年人之间同性恋行为的可罚性已经被取消了。但是,批判立法的法益概念得到了立法者的认可,这当然不能成为反对这一概念的理由。
2.最高法律原则必然具备的抽象性
针对那种认为批判立法之法益概念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的观点,我的第二个反击理由是,我们无法从一个具有涵摄能力的(subsumtionsfhig)概念中获得最高的法律原则,实际上,最高的法律原则指的仅仅是一种指导性的标准,我们需要在法律的素材中对该标准具体化地加以展开。我在上文(第三部分第〈一〉点的开始处)对法益所进行的描述仅仅旨在提出这一标准,而在对我所举的那六个例子进行简要分析的过程中,该标准已被证明是适当的。
为了寻得具体的解决方案,我们还必须求助于最近由曼弗雷德·海因里希(53)所提出的“法益保护的三阶层模式”(Drei-Stufen-Schema)。根据这一学说,对于任何一条在合法性方面存在疑问的具体罪刑规定来说,我们都必须精确地考察,它保护的应该是什么,它保护的应该是谁,以及它所抵御的又应该是什么。只有在这一分析结束的时候,我们才能认定,被法律犯罪化了的举动是否会对个人的自由发展,或者个人自由发展的社会条件造成损害。
除此之外,我毕竟已经为法益原则的具体化提出了九条有效的准则,(54)这就降低了对法益原则进行具体化的难度。在此,我无法一一详述这些准则,但至少可以用关键词的方式把它们罗列如下:恣意的、纯粹建立在意识形态之上的刑法条文,或者违反基本权利的刑法条文所保护的绝不是法益;不道德的或者值得谴责的举动本身,还不能作为认定成立法益侵害的根据;侵犯自身人格尊严的行为,并不属于法益侵害;只有在因为胁迫而产生了现实的恐惧时,我们才能认为,对感情的保护是对某种法益的保护;对他人有意识的自陷风险予以协助或者支持的行为,并没有侵犯(他人的)法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象征性的刑法规范不具有法益保护的功能;禁忌并非法益;若保护的对象抽象得无法让人把握,则该对象也不能被看做是法益。此外,格雷科(Greco)(55)不久前针对集体法益提出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看法。他认为,“如果对某种集体法益的损害,总是同时以某种个人法益受到损害为前提,那就”不允许“把该集体法益认定为受某一特定规定保护的利益”。
我想,以上述准则为基础,法益概念在说明刑法规定的合法性方面完全能够发挥建设性的作用。米尔·普伊格(56)曾就法益概念正确地指出:“事实上,所有普遍性的原则都需要通过公开讨论的方式来得到具体化。诸如民主或者人人平等法则之类的原则都具有高度的普遍性,所以我们可以对其展开完全不同的具体化,但没有任何一个理性的人会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宁可不去援用这些原则。”
3.承认立法者享有一定的创造空间,这并无损于法益概念的价值
米尔·普伊格的评论说明,法益概念的批判者往往忽视了一点,即被认定为法益的东西,并没有绝对泾渭分明和“清晰”的边界;实际上,某一规定与法益之间关联性的明显程度可高可低。当这种关联还能完全显现出来的时候,立法者的创造空间就体现为决定予以处罚,这种空间同样也可能体现为创制某种秩序违反性或者放弃实施任何制裁。我想通过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这些例子我是从最新的文献中获知的。
例如,罗马诺(57)在对我的学说展开批判时主张:立法者应当坚守在“以法益为指导的刑事政策”的框架之内;如果某个罪刑规范“实际上根本不保护任何东西”,那该规范是不被容许的。但他又认为,立法者“对摩托车驾驶者课以佩戴头盔的义务,或者对汽车驾驶者课以系安全带的义务”,并规定一旦驾驶者违反该义务,则“处以罚金或罚款”,尽管此类义务首先保护的是司机自己,但这种做法也是可以被接受的。(58)“法学上的家长主义(Paternalismus)模式在盎格鲁撒克逊的法律体系中并不少见,在我看来,对适度的家长主义采取断然拒绝的态度,这是不值得赞同的。”
我完全赞成罗马诺的结论,但同时又认为,通过制裁来保障驾驶者履行系安全带或者佩戴头盔的义务,要说明这种做法的正当性,不能借助驾驶者的自陷危险,而应当借助该行为对他人造成损害的可能性。罗马诺曾认为,这种损害体现为社会为“提供医疗和住院服务”而支付的费用。当然,仅此这一点是否就足以证明处罚具有合法性,我对此深表怀疑。因为,假如遭遇车祸的人自行支付这些费用,那上述论据就不再成立了。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后果都是由疾病或事故保险来规制的。没有任何立法者会认为,由于某种有损健康的生活方式或者危险的体育活动可能会带来一些费用的支出,故需要对之处以刑罚。
但是,与系了安全带的司机相比,未系安全带的司机更容易失去对其汽车的控制,从而导致其他人受到损害,故关于系安全带的义务具有正当根据。这一点也适用于汽车同乘者,因为有的时候,他们会因为没系上安全带而被抛出车外,从而遭受损害。同时,未系安全带的乘车者以及未戴头盔的自行车和摩托车的驾驶者,也会给事故中的其他参与人带来危险,使他们可能会因为犯了过失致人死亡或者严重致人伤害罪而受到处罚;但如果驾驶者使用了安全带或者头盔的话,那就不会出现身体伤害,或者只会产生轻伤结果。防止第三人遭遇承担责任的危险,这一点就已经使该义务具备保护自由和法益的属性了;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就能够保护第三人免受因他人的疏忽而带来的损害。
因此,立法者的这种介入,依然处在法益保护的框架之内。不过,由于这些规定具有家长主义的成分,所以和那些“纯粹的”法益保护犯相比,法益保护在这里显得没那么鲜明。因此,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来看,把这些举动当作违反秩序的行为来处理会更好一些。但究竟是规定有限度的罚金刑还是完全放弃制裁性的规制手段,这属于应由立法者去裁量定夺的事情。所以,在德国,法律还没有对自行车驾驶者课以佩戴头盔的义务。
相似的原理也适用于上文已经探讨过的关于否认纳粹大屠杀的情形。罗马诺说道:(59)“我也认为,试图借助罪刑规范来解决虚无主义(Negationismus)问题的做法是不合适的。”但他同时又提出,“如果法律规定,受到禁止的那些举动方式(对大屠杀的罪行加以赞许、否认或者美化),只有当它们从时间和地点上来看,会给公共的和平造成具体的危险状态时,才应当受到处罚”,那么这是可以接受的。
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是,在他所说的这类情形中,又明显存在着法益侵害的危险。按照我的看法,只有那些“不带任何煽动成分的单纯否认行为”才不应受到处罚;(60)如果某人“对此类谋杀行为加以赞许,或者……声称,这些事情都是犹太人为了诽谤德国人而杜撰出来的”,那么我认为,对该行为加以处罚是妥当的。这种煽动的言论会危及生活在德国的犹太人的自由和安全;而这才是罗马诺想要考虑的情形。在我看来,批判立法的法益思想对于这些情形来说也没有任何不当之处,恰恰相反,它为合理的区分提供了可能。
第三个例子也能说明这一点。根据刑法典第184b条第4款第2句的规定,持有儿童淫秽文书或图片的行为应当受到处罚。有一部重要的刑法注释书(61)认为,“我们很难看出,处罚这种行为的理由究竟何在”。防止该类物品的传播,这并不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因为物品的接收者并不会受到损害;在制作这些物品的过程中会发生严重的奸淫儿童的行为,但在此刻该行为已经出现过了。
不过,如果我们认为,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出现对儿童淫秽物品的制作予以促进的行为,从而防止发生与之相联的奸淫儿童的行为,那么以此为出发点,我们就可以——与上文探讨过的青少年淫秽物品的情况不同——为惩罚找到一个能够提供合法性根据的法益关联。我在另一篇文章(62)中对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施罗德(Friedrich-Christian Schroeder)(63)的观点表示了赞同,并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此,我只能指出其中的基本思想,即我们通过对购买儿童淫秽物品的行为加以处罚,能够降低人们对该物品的需求。这一思想在此处——和持有毒品的情况不同——是合理的,因为该物品的制作者并不是在广阔无边的国际网络中实施行为,正如施罗德所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以私人“小企业主”的模式从事着活动,所以非常依赖有购买愿望的顾客。但无论如何,利用刑法去实现这种法益保护的意图,这种做法处在立法者所享有的创造空间的范围之内。
4.从属性原则是对法益保护思想的不可或缺的补充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要求必须存在法益侵害或者法益侵害的危险,这还不是对可罚性进行限定的唯一原则。由于民法、公法,特别是违反秩序法都在保护法益,所以当某种法益受到损害时,总是会出现一个问题,即究竟是应当通过刑法,还是应当通过其他的法律规制手段(例如损害赔偿、批准义务或者控制措施)去防止这种损害的发生呢?
多数学者的观点是,刑罚的威吓是影响最为深刻的一种制裁手段,只有当较为轻缓的规制手段力有未逮时,才能考虑动用刑罚。这被称作从属性原则,它作为划定刑罚界限的准则,具有与法益保护原则完全相同的地位,而且从刑事政策上来看,它至少也和法益保护原则一样重要。因此,我们可以把刑法的任务说成是“从属性的法益保护”。(64)最近,阿亨巴赫(Achenbach)(65)提出“在经济刑法中存在超个人的法益”,进而强调,法益理论在此“无法为区分合法和不合, 法的刑法构成要件提供真正有效的标准”。但这种见解并不能成为反对法益保护原则的理由。阿亨巴赫本人就曾提及从属性原则的功能,因为他曾说:“对于我而言,关于刑法之替代手段的理论始终都是经济刑法中核心的一章。”(66)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要求除了法益理论之外,还应当发展出一门独立的“从属性科学”。早几年前,我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67)这就意味着,何种规制机制能够以尽可能有效、同时又维护自由的方式,为社会上符合预期的法益保护提供可能,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展开跨学科和机构化的专门研究。这是一个极其复杂而且远未弄清的问题领域,我在此无法对其做进一步的探讨;但在涉及立法者的处罚界限时,我们必须始终对这一问题保持关注。某些核心问题是特别具有争议的。例如,蒂德曼(Tiedermann)曾提出过以下命题:(68)刑罚威吓所带来的不利后果,可能会比某种严重限制行为自由的控制体系要小。另外,泰勒(Theile)(69)提出的关于“刑法之社会操控权”的命题也亟待讨论。在经济法领域中,该命题会促使人们去创设一种由刑法来加以保护的崭新法益,(70)而又有别的一些学者意图借助从属性的原则去坚决地压制刑法。最近,特伦德伦堡(Trendelenburg)(71)“以经济刑法为例,对未来的从属性科学展开了广泛的先期研究”。
四、行动犯存在的必要性是否说明批判立法之法益理论的基本思想是错误的?
有一种反对思潮之所以否定法益理论,不是因为它认为该理论无法清晰地划定刑法的界限,而是因为它在刑罚威吓的合法性问题上持一种根本不同的方案。在德国最近的研讨中,施特拉滕韦特(Stratenwerth)(72)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根据他的看法,“惩罚的根据并不在于行为对特定法益所造成的侵害;只有行为人针对对于社会的基本合意来说具有基础性意义的行为规范所表示的蔑视,才可能成为这一根据。”(73)据此,决定行为是否具有可罚性的,是“得到社会和立法者认可的一种基本态度,即想要维护某种特定的规范,或者从另一方面来说,完全不想去实施某一举动”。(74)针对这一观点,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反驳。
第一,多数国民不愿意对他们所厌恶的举动加以容忍,从这一事实出发并不能得出结论认为,即便该举动没有损害任何人的发展自由,也应当对之施以刑罚。尽管沃勒斯本人对于法益理论确实持批判态度,但他正确地质问道,(75)“假如我们向‘法益教义学’挥手作别,是不是就能够完成合理地说明刑法规范的根据这一任务呢?”同时,他也正确地强调说:(76)“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一种信念‘在那儿’,就当然地认为它是值得保护的。”泽尔曼(Seelmann)也认定:(77)“只有当某人……作为行为人贬损了某个他人,即被害人的法律地位时,才能认为刑罚…是必要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政府当年制定的1962年刑法草案(78)曾认为,“根据普遍的信念”,成年人之间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实施的同性恋行为是一种“下流的举动”;即便在那个时候,对该行为加以处罚的做法,也——与联邦宪法法院的观点不同——不具有合法性。
第二,在我们当今这个文化多元的社会中,如果某一特定举动不会造成法益损害的话,那么是否需要对该行为加以处罚,我们对此已完全不再可能确定出一个“基本合意”来。光是上文(第三部分第〈二〉点中的第1点)已经讨论过的那六个示范性的情形,就已经足以说明这一点。在这些情形中,虽然立法者大都坚持认为无法益的行动犯也具有可罚性,但对所有这些情形的处理方式却都极富争议性。
第三,即最后,对于不损害法益之举动是否具有可罚性的问题,不可能存在“基本合意”,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真正的基本合意只有一点,即任何一个人,只要他不损害其他人的发展或者发展的法律条件,那么他可以根据其个人的优先权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人格。沃勒斯(79)正确地指出:“在一个建立在多元主义和规范个人主义价值之上的社会里,规范的基本合意……是指,关于利益的不同构想,可以在不受国家影响的自由的意见市场上相互竞争,国家所做的仅仅是对那些能够使该市场发挥作用的那些基本条件提供保障。”
施特拉滕韦特的观点赢得了一位新的支持者,他就是福尔克(Volk)。(80)福尔克从刑罚目的的理论出发,为该观点增添了一条新的论据。他以积极一般预防的刑罚目的为基础,把自己的观点(81)与我所提到的“信赖效果”(Vertrauenseffekt)联系在一起。“如果公民目睹法律得到了贯彻”,那就会产生这种效果。他还把自己的观点与“满足效果”(Befreidigungseffekt)联系在一起。“当公众的法意识因为某种违反法律的行为受到了制裁而归于平复时”,该效果就会随之显现。他由此得出结论:“刑法的目的在于保护感情。对被激发出来之法意识的信赖和满足,……不过就是感情而已。这种刑罚目的理论完全可以与法益理论协调一致。没有什么会比违反禁忌的举动更能引起人们不安的感觉……。”因此他并不想(82)——就这一点来说,他和施特拉滕韦特的观点有所不同——抛弃法益的概念,而是想把这一概念的外延拓展到感情之上。他主张,应当“敞开”法益概念的大门,将“对禁忌、以伦理为基础的期望以及‘感情’的保护,也看作是合法的国家任务”。但与此同时,他又“不想自然而然地”要求刑法去保护这些感情。福尔克也认为应当对刑法介入措施的合法性加以论证,只不过,他想把这种论证放在“别处进行,即放在合比例性或者从属性原则中进行”。“这样做有一个特别的优势,即它能与刑罚目的的理论相协调,而后者的目标就在于实现社会的意识,以及……强化‘感情’。”安德罗拉基斯(83)在对“愤怒原则”(Entrüstungsprinzip)进行辩护时,也说过与此相似的话。针对这一论证,有两条反对理由。
第一,积极一般预防的目的并不在于,从某些任意的感情和期待出发,去实现信赖和满足的效果。公民能够相信的只有一点,即他的安全及其制度性的前提条件会得到保障,而且只要没有以不被容许的方式损害到其他人的发展自由,那么任何事情他都可以去做。用刑法去保护除此以外的其他期待和感情,这并不能产生任何满足的效果,因为它限制了其他人的行为自由,从而会引起社会的冲突。
第二,不是把论证的基点放在缺乏法益损害上,而是把它放在从属性和合比例性上,这种做法会使一个本来在刑事政策上很清晰的要求(“不损害法益的举动方式必须无罪”),变得认定起来具有严重的不确定性。因为,一旦我们允许用刑法去保护感情,那么这种保护手段在什么时候是不合比例的,什么时候能够为其他的法律规制手段所代替,或者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干脆放弃一切的保护措施,在这些问题上都会产生无穷无尽的争议。
另外一些学者虽然也信奉法益思想,认为对感情进行一般性保护的做法应当受到否定,但是在一些例外情形,或者超出了合法的安全需要的特殊情形中,却又想赞同这种做法。例如,黑芬德尔是批判立法之法益原则最为重要的支持者之一,(84)但他也认为应当允许存在例外情形,即“如果某种举动虽然并未造成损害,但却违反了植根于社会之中的同一价值观念和行为观念”,那么该行为应当受到处罚。
虐待动物罪对于法益理论来说始终都是一个难题。借助黑芬德尔的学说,我们可以对诸如该罪之类的构成要件做出大致令人信服的解释。(85)但是,金贝尔纳特(86)对黑芬德尔所提出的反对意见是有道理的,他指出,这样一来,“假如在一个社会中,多数人都怀有一种感情,认为同性恋是值得谴责的,那么刑法上禁止同性恋的规定也同样具有正当化的根据”。这一反对意见也获得了黑芬德尔自己的证实。因为他认为,之所以要对同性恋实行无罪化,其理由在于,(87)“当反对该种举动方式的意见已经不再占据‘社会的统治地位’时”,就应当实行这种改变。
但是,法益思想的自由功能恰恰就在于,它能够保护少数人免遭多数人意见的主宰。而且我们应当考虑到,公众关于不侵害法益的举动方式是否可以容忍或者是否值得谴责的意见,即他们关于政治、宗教或者性方面的观点,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之中,而且还可能受到人为的操控。因此,没有任何一项理性的刑法政策能够以这种意见作为其根据。
近来,金贝尔纳特进行了一个十分具有独创性的尝试,他试图在法益理论的框架内,对感情保护的问题加以区别对待。(88)他明确表示信奉“法益理论”,并且在结论上也完全赞同我所主张的观点。但在某些情形中,他的结论却是以这样一种观点作为其依据的,即“合法的感情”可以作为法益来加以保护。于是,无论在西班牙还是在德国,可罚的虐待动物的行为都会产生“令人不适的感情”,(89)这种感情就是一种合法的感情,所以“禁止对动物实施暴行的一般性命令”就是正当的。其合法性的来源在于,1986年在欧洲内部达成的协议规定了一种义务,即我们应当对所有的脊椎动物都“表示尊重,并且适当地考虑其感知痛苦的能力以及记忆的能力”。(90)从德国的情况看还不仅限于此,因为基本法第20a条也明确宣示了对动物的保护。
同样地,在西班牙和德国,“破坏死者安宁”(刑法典第167a和168条)的行为都是可罚的。在此,“该类构成要件保护的法益,是由这种毁坏坟墓的侵袭行为所引起的不适感或者愤怒感”。(91)因为“对死者的尊重”,是宪法所保护的“意识形态上或者宗教上自由(同时也是无神论意识形态的自由)”的一种表现形式。最后,在西班牙,系安全带和佩戴头盔的义务处于行政法制裁的保障之下,这些义务保护的不是“违反规范者的生命和健康,而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合法的感情。基于这种感情,当交通运输活动中受害人的数量增多时,广大公民会感到不安……”。(92)相反,对诸如同性恋、亵渎神明或者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问题上编造谎言的行为加以处罚,这种做法则是错误的,因为由这些行为所引起的愤怒感是不合法的。之所以说其不合法,理由在于,宪法已经承认公民享有从事性活动的权利(93)以及言论自由和表达意见的自由,而上述感情跟这一规定是对立冲突的。
这一看法非常有趣,而且从宪法的价值判断上来看也很值得赞同。但问题在于,“感情”真的能成为保护的对象吗?其实,禁止虐待动物的命令首要的并不是想照顾我们的感情,而是想使动物免受不必要的痛苦。(94)一切关于动物保护的法律规定,都是对动物的保护,而不是试图避免使人们产生激动的情绪。否则,一旦虐待动物的行为不是公然实施,并且也无人对此感到恼怒,那该行为本来就不应受到处罚。由于动物受到了欧洲协议和德国宪法的保护,所以我确信无疑,应当把动物的痛苦感看作受到保护的法益。我们与高级动物之间是能够进行交流的,而且它们的痛苦感也和我们的相同,既然我们把这类动物视为我们生命世界中值得保护的组成部分,那么顺理成章地,我们也应当把人给它们造成的痛苦认定为对法益的侵害。(95)
不过,这样一来,有着严格边界的纯粹人本主义的法益理论——因为动物所得到的保护与人所享有的保护,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微乎其微——就被扩展成了一种“生物的”(geschpflich)法益理论,即我们把动物看作“共同生物”,并对之加以保护。但前述欧洲和德国的相关规定可以为这种做法提供正当化根据。金贝尔纳特(96)反对此种看法,其理由在于,“动物不能享有任何的主观权利”。但是,对法益的损害并不必然以主观的权利受到侵害为前提,例如环境犯罪就说明了这一点。
同样,我们也必须把充满敬意地对待逝者看作是我们社会中合乎人类尊严之生活的组成部分。掘墓或者侮辱尸体的不法举动,损害了共同的生活,也损害了逝者继续有效的人格权。感情上的反应只不过是这种损害的表现而已。关于戴头盔和系安全带的义务,我在前文中已经试图说明,在这种情形中刑法对真实法益的保护范围究竟有多宽。
因此,在我看来,在上述情形中,局外人合法的愤怒感并不是法益本身,而只是人们对法益遭受侵害所做出的一种正当的反应。
五、法益、刑事政策与宪法
即便我们以这样一种观点作为出发点(这就是我前面所试图阐明的),即批判立法的法益理论足以为我们提供清晰的结论,但还有一个话题是存在重大争议的,即对不损害法益的举动方式加以惩罚,这究竟会引发何种后果呢?法益原则的捍卫者们至今还未能充分地说明,关于法益损害的要求只是一个供立法者参考,但对他并无约束力的刑事政策上的准则呢,还是说某一罪刑规定会因为缺少与法益的关联性而归于无效呢,若是后者,则认定该规定无效需要满足何种条件呢?德国、法国、西班牙和阿根廷的宪法法院都已经对这类规定进行了研究,而且国外的法院在我所描述的那些情形中均认定相关规定无效,这些事实都说明,上述第二种备选方案并非从一开始就不合理。
(一)关于法益思想在刑事政策方面的意义
我本人曾经说过,(97)而且对此我和多数法益理论的支持者的观点也是一致的:(98)“批判立法之法益概念的捍卫者首先指向的是立法者,他们提出了一些刑事政策上的要求,但并不想使自己提出的建议在所有情形中都具有宪法上的约束力。”
即便是在那些断然否认自己的结论对立法者有约束力的学者中,也有很多人赞同法益理论具有这种刑事政策上的意义。例如,杜贝尔(99)赞成在北美洲采纳法益概念,他说:“即便证明,法益概念不是建立在宪法的基础之上,故在现代的民主法治国中不会产生破坏性的作用,但它在一般的刑法理论中也始终能够扮演建设性的角色,并且还能够成为——虽然并非必然——指导立法者和法院的准则。”
法益理论所具有的刑事政策的功能不容低估。因为,例如德国的立法者自1969和1973年开展刑法改革以来,至少已经从趋势上将先前所谓的风化犯(Sittlichkeitsdelikt)限定在了侵犯“性的自我决定权的”行为(刑法典第174条以下)之上,所以,由刑法备选草案所倡导的批判立法的法益概念就在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样,在其他那些经过宪法法院审判的争议性问题(例如毒品法、器官移植法以及兄妹乱伦的问题)中,批判立法的法益概念本来也能起到实质性的辅助作用。
(二)法益保护与宪法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即如果某一罪刑规定不保护法益,那么它能否归于无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莫衷一是。即使在今天,也还有不少学者完全否定法益概念对立法者具有约束力。例如,巴西加卢波(100)认为,我从法益原则中推导出来的结论,“从法律政策的角度来看是正确的”。“但可以确定的是,没有任何一个关于刑法保护对象的理论能够提出一个标准,借助该标准我们就能确定,在一个以自由为基础的社会中,用刑法手段对自由加以限制的做法,其边界究竟何在。”(101)“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是立法者的创造物。”
最近,施图肯贝格也表达了相似的意见:(102)“如果我们是从学术上的立场出发,试图规定立法者应当选择何种目标,不应当选择何种目标,那么这在关于(刑事)政策的讨论中,完全可以而且也有必要成为一种建议。在理想的状态下,这种讨论的发展方向取决于论据的说服力。但是,认为立法者在法律上有义务只处罚损害法益的举动,这种想法如果无法解释成令人信服的宪法上的论据,而这一点确实并不明显,那它就不符合民主体制下立法者的行动自由。既然这种想法会如此不受欢迎,那么从宪法上来看,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禁止议会经由多数决定惩罚‘单纯不道德的’举动。”
以上见解道出了关键点。因为,毫无疑问,对立法者产生约束性限制作用的,不可能是教授们的观点,而只能是宪法。法益理论的支持者们对此并无异议。例如,人们可以读到我在引用施特希林(Stchelin)和哈塞默(Hassemer)的论述时曾说过的一句话:(103)“这类罪刑规范是不被允许的,该判断在宪法上的连接点是从合比例性原则推导出来的禁止过度这一要求。”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像魏根特(Weigend)(104)所想的那样,用合比例性原则去代替法益保护原则。他说,作为批判立法的概念,法益“从属于一个以宪法为根据的惯用语,即国家的介入应当合乎比例”。实际上,这两者是相互补充的,正如舍恩克(Schnke)与施罗德(Schrder)的刑法注释书(105)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刑法的立法能够追求实现何种目的,在这个问题上,法益理论和宪法上的要求……是相互交错的;作为关联点,合比例性原则本身是以存在某种应当得到保护的利益作为其前提的,而法益理论就可以为此提供依据,但同时又避免出现在进行宪法判断之前就已经产生结论的现象。”(106)
卡斯帕在他奠基性的专著中,针对合比例性原则(107)也得出了一个结论,即我们应当把这两个原理连接在一起。在此过程中,“法益理论的实质性要求也能够完整地植入到宪法判断之中。对合比例性原则的判断做这样的理解,至少可以免于这样一种责难,即合比例性原则没有为刑法条文的内容提供任何标准。”
别的什么构想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不存在为了比例性的比例性,我们必须将刑法的介入与由此所追求的目标这两者拿来比较。在比较的过程中,法益保护的方式和范围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将批判立法的法益理论与宪法联系起来,这种做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目前已经为通说所承认。例如,弗里斯特强调,(108)“如今,在刑法学当中,人们也是从宪法的角度出发来定义法益概念的”。根据施泰因贝格的观点,(109)当今赞同批判立法之法益理论的学者们“在目标上已经达成了广泛的一致,即他们无意建构一个自外于宪法的概念,而是想在刑法领域内,通过贯彻法益概念,从而对宪法本身的内容加以具体化”。
我们宪法法院的这个说法(110)是有道理的,即我们不能用立法之外的机构来限制立法者的创造权。(111)“实际上,立法的边界——在刑法领域内,正如所有其他领域一样——只存在于宪法自身当中……。”但宪法法院却错误地认为,批判立法之法益理论的赞成者们所持的是与此不同的另一种观点。(112)虽然法益理论也可以在宪法之外提出它在刑事政策方面的设想,并将其提供给立法者。但毋庸置疑的是,只有在某一规定违反了宪法的情况下,法益理论才能认定该规定是无效的。
因此,争议的焦点就在于以下这个问题,即当某项罪刑规定不是为了保护他人的发展可能性及其制度性条件——即不是为了保护法益免受侵害或者侵害的危险——时,我们能否认定该规定是违宪的,如果能,那么在满足了何种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这样做呢?如上所述,在施图肯贝格看来,对此问题,“令人信服的宪法上的论据……并不明显”;我们的宪法法院也认为,(113)法益理论“没有提供任何必然可以为宪法所采纳的实质性标准……。”
然而,上文所提到的那些批判立法之法益思想的支持者们,大都提到了一点,即国家的介入应当遵循合比例性这一法治国的基础性原则(有用性(Geeignetheit),必要性(Erforderlichkeit),适当性(Angemessenheit))。一条罪刑规定,如果它不保护任何法益,那我们就可以认为对公民自由的这种介入是不适当、过度和不合比例的,进而认定该规定违宪。当然,究竟在什么时候可以具体认定这一点,这个问题还没有弄清。对于主张法益思想不仅具有刑事政策上的功能,而且还具有宪法上意义的观点而言,这——到目前为止——就是它的软肋所在。因此,诺伊曼(Neumann)的观点(114)理应获得完全的赞同,他说:“当然,我们有必要提出不同的论证模式,这些模式使得合比例性原则能够运用到具体的情形中去。”
我们不能说,对不侵害法益的行为加以处罚的做法违反了合比例性原则,所以它是违宪的。例如,如果某人“公开地实施了性行为”,从而引起了他人的愤怒(刑法典第183a条),那么他并未侵害其他人的法益;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发展可能性会因此受到损害。因此,如果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来看,把该举动当作违反秩序的行为来处理会更为适当一些。但是,对该举动适度处以刑罚,这并不违反宪法。因为,当违反道德和有伤礼仪的行为是以引起他人反感的方式公然出现时,我们就不能禁止立法者对该行为加以制裁。该观点的一个依据是基本法第2条第1款的规定。依照这一规定,我们可以借助“道德法则”对人格的自由发展加以限制。(115)相同的道理也适用于对所谓拒斥态度(Konfrontation)加以保护的法条(刑法典第184条第2款第6项),该条文规定,在未受要求的情况下向他人交付淫秽物品的行为应当受到处罚。
但与之相反,针对不少条文,我们在经过权衡后得出结论认为,用刑罚介入其中的做法是不合比例的。例如,与联邦宪法法院的观点(116)相左,对有偿放映淫秽影片的行为加以处罚的做法就是这样;因为在这种情形中,如果观看者事先已被告知了影片所属的种类,那该行为就没有迫使任何人违背其意愿去观看淫秽的影片。该条文的目的据说是为了保护青少年,但这个目的通过检查证件就能轻而易举地得到实现。同样,刑法典第184a条规定,向他人提供动物淫秽的文书或者图片的行为应当受到处罚,这一条文也是不合比例的。因为如果某个成年人自己想要看看这种东西,那么没有任何的物和人受到损害,故用3年以下有期徒刑去威吓这种行为的做法,明显违反了禁止过度的要求,特别是在个人与动物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完全不可罚的情况下。在上述这两个情形中,我们也不能援用“道德法则”来论证该处罚具有合宪性,因为淫秽物品本身是受到容许的,而且无人对这样的事件表示反感。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上文曾提及的一种情况,即某人持有其17岁女友的具有露骨之性内容的照片。
生者基于利他主义捐献器官,只要捐献的对象不是亲属或有紧密关系的人,那么该行为就受到禁止,并且是——虽然仅限于对实施器官移植的医生来说——可罚的(上文第三部分第(二)点的第1点中第三种情形)。在我看来,这种做法也不合比例,是违宪的。因为,这种行为没有对参与者的个人发展自由造成任何的侵犯。至于说可能出现参与者并非基于自愿,或者导致器官买卖的危险,这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消除。但是,这种拯救生命的行为无论从社会还是伦理方面来看都富有价值,用刑法来防止这种行为的做法,与立法者所追求的目的之间完全不成比例。
从合比例性原则的视角出发,对所有不能体现法益侵害的条文的合宪性一一加以检验,这在本文的篇幅内是无法做到的。但上述这些例子足以表明,对所有可予考虑的条文进行细致的分析,这能够提出令人信服、持之有据的解决方案,并且在某些情形中,也能够得出相关规定违宪的结论。(117)
此外,人们还忽视了一点,即对不损害法益的举动方式加以处罚的做法,在宪法上还受到其他一些限制。这些限制在所有的权衡中都没有得到考虑,实际上它们对立法者的约束力甚至比合比例性原则还要强。这一点特别适用于对“私人生活安排的核心范围”的介入,联邦宪法法院从人的尊严出发推导出了这一概念,并认为这一范围是不可侵犯的。(118)因此,立法者介入该核心范围的做法就违反了宪法。
私人生活安排的核心范围无疑也包括人的性行为,只要它不是公然实施,也不是在违反他人的性的自我决定权的情况下实施。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对成人之间的同性恋关系,以及兄妹之间的乱伦行为都不允许加以处罚。
但该思想也包含了这样一个命题,即像《麻醉剂法》第29条第1款的规定那样用刑罚去威吓仅仅为了自用而持有毒品的行为,这是违宪的。(119)因为,就像某人为他本人而去使用容易上瘾的物品(例如酒精和烟草)一样,为了自用而持有毒品的行为是他个人对生活所做的安排,并且涉及其核心的范围,因为这是他自我实现的一部分。正如上文所述,阿根廷的宪法法院也判定,用刑罚来禁止为了自用而持有毒品的行为,这种做法是违宪的。法院认为,该做法违反了阿根廷宪法第19条的规定,这一规定指出,私人的举动方式仅仅是上帝,而不是刑法要管的事务。(120)
最近,格雷科(121)为了从宪法的角度出发对国家的刑罚权加以限制,提出了“自治理论的论据”,并认为,这一论据“比法益理论更具优势”。(122)“对单个人自治权的尊重意味着,我们让他享有对某一范围的支配,有权对该范围做出决定的只有这个人。很明显,这一思想与……不可侵犯的私人生活安排的核心范围这一概念是高度一致的。”
认为关于核心范围的命题,能够说明某些与法益无关的罪刑条文违宪的根据,这是正确的。但法益理论并不会因此而变得多余。(123)因为:第一,要把某个行为归入私人领域的核心范围,前提是该行为未对他人的法益造成损害。第二,即便不是从对核心范围加以保障的人的尊严出发,而是从其他的宪法原则(即合比例性原则或者特别的基本权利)出发,也能说明对不损害法益之举动加以处罚的做法是违宪的。第三,在违反法益原则的行为并不违宪的场合,法益原则始终都具有重大的刑事政策上的意义。
还有另一个基本权利是言论自由。如果侵犯了这项权利,例如对“虚无主义”,即不带任何歧视和煽动成分的否认历史事实的行为加以处罚,那就可以认定该处罚规定是违宪的。罗马诺、(124)金贝尔纳特(125)以及上文提到的西班牙和法国的宪法法院,都明确援引了这一权利。
这就表明,我上文(第三部分第〈二〉点的第1点)论述了六种情形,以此为例说明不侵害法益之举动的可罚性极富争议,在所有这些情形中,我们都能够很好地论证相关规定的违宪性。其他的情形还有,例如,出于宗教上的动机处罚不损害法益之举动方式的做法,可能会对信仰自由造成侵犯。本文不可能对所有在合法性上存在争议的罪刑规定都一一加以分析。但黑芬德尔的看法(126)是有道理的,他说,“对法益理论进行真正的拓展,已指日可待了”。
本文的德文标题为“Der gesetzgebungskritische Rechtsgutsbegriff auf dem Prüfstand”,原文于2013年发表在德国《格尔特达默刑法档案》(Goltdammer's Archiv für Strafrecht)杂志(第433-453页),到目前为止,已先后被翻译为巴西葡萄牙语、英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本文的翻译和发表得到了作者的授权。文中的姓名翻译均以《德语姓名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和《西班牙语姓名译名手册》(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为准。——译者注。
以下这篇论文的缩减版,我曾以西班牙语分别于2012年6月20日在马德里的科学研究院,2012年10月30日在里约热内卢的Gama Filho大学做过演讲。本文的葡萄牙和巴西语翻译,已于2012年发表在“Revista dos Tribunais”,Vol.No.922,S.291-322.;本文的西班牙语翻译发表在“Revista Electrónica de Ciencia Penaly Criminologia”2013,S.1-27.;此外,本文的英文翻译发表在“European Criminal Law Review”2013年第1卷,S.3-25。
注释:
①对于这场争论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因素是2002年举办的关于“法益理论”的研讨会。该研讨会的报告和讨论,于2003年发表在由黑芬德尔(Hefendehl)、冯·希尔施(von Hirsch)以及沃勒斯(Wohlers)主编的论文集中。2007年,该文集又以扩充版的形式在西班牙出版。相关的讨论在2004年得以继续进行。后续会议的报告及讨论,于2006年发表在由冯·希尔施、泽尔曼和沃勒斯主编的题为《调节原则:在论证刑罚根据时的界限原则》(Mediating Principles.Begrenzungsprinzipien beider Strafbegründung)的文集中。
②Hefendel GA 2007,1ff.
③BVerfGE 120,224ff.
④Roxin,Festschrift für Hassemer,2010,S.573ff.
⑤Bacigalupo,Festschrift für Jakobs,2007,S.1ff.
⑥Romano,Scientia Universalis,Festschrift für Roxin,2011,S.155ff.
⑦Palaino Navarrete(Fn 6),S.169ff.
⑧Gimbernat,Festgabe für Claus Roxin zum 80.Geburtstag,GA 2011,284ff.
⑨Androulakis,Festschrift für Hassemer,S.271ff.他认为Manoledakis是“所谓发挥批判机能之法益概念的支持者”(S.272Fn 3)。
⑩Kaiafa-Gbandi,in:Eser/Hassemer/Burkhardt(Hrsg.),Die deutsche Strafrechtswissenschaft vor der Jahrtausendwende,2000,S.261ff.(263).
(11)Dubber ZStW 117(2005),485ff.(516/517).
(12)详见Roxin,Strafrecht,Allgemeiner Teil,BandⅠ,4.Auf.2006,§2Rn 123ff.
(13)“Verhaltensdelikt”一词,日本学者小林宪太郎译为“行态犯”(参见[日]小林憲太郎:《「法益」について》,载《立教法学》第85号(2012年),第483页)。考虑到这一概念强调的是,某一行动,虽然它不具有法益侵害或者法益侵害的危险,但与社会某种价值观或者情感相悖,故该行动本身就应当作为犯罪处理。为了凸显这类犯罪处罚的是某一行动本身,也为了与德国刑法理论中的行为犯(Ttigkeitsdelikte)以及我国刑法学通说中的举动犯概念区别开来,我倾向于将这个词译为“行动犯”。——译者注
(14)我只想提及雅各布斯发表在Festschrift für Saito,2003,S.780ff上的论文,标题是:“刑法保护的是什么:法益还是规范效力?”。我对其观点的批判,以及关于雅各布斯论文的更多引证,见我发表在GA 2011,678ff.(688-692)上的论文。
(15)Jakobs(Fn 13),S.765/764(日文版的页数是倒过来排列的).
(16)Jakobs(Fn 13),S.762.
(17)详见Roxin,GA 2011,678ff.(690ff.).
(18)Mir Puig GA 2003,863ff.(866).
(19)Polaino Navarrete(Fn 6),S.176.
(20)Polaino Navarrete(Fn 6),S.181;Scheinfeld(Fn 6),S.183ff.(187)也得出结论:“规范保护的刑法之益……不应得到赞成。”
(21)Roxin,ATⅠ,§2Rn 7.
(22)我教科书中的引证,ATⅠ,§2Rn 7,8,Fn 21,22.
(23)Schünemann,Mediating Principles(Fn 1),S.18ff.
(24)Steinberg,Festschrift für Rüping,2008,S.91ff.
(25)M.Heinrich(Fn 6),S.131ff.
(26)Frister,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5.Aufl.2011,3.Kap.,Rn 21,29ff.
(27)Kaspar在其2011年的教授资格论文《预防刑法中的合比例性与基本权利保护》(Verhltnismigkeit und Grundrechtsschutz im Prventionsstrafrecht)中如是说。
(28)Frister,AT,Rn 21.
(29)Frister,AT,Rn 32.
(30)Dubber ZStW 117(2005),510.
(31)Stuckenberg GA 2011,653ff.(657).
(32)BverfGE 6,389ff.
(33)1968年的性犯罪备选草案影响巨大。
(34)Gimbernat GA 2011,286.
(35)§29Abs.1BtMG.
(36)BverfGE 90,145ff.
(37)参见Greco,in:Hefendehl,Grenzenlose Vorverlagerung des Strafrechts?,2010,S.73ff.
(38)§37Abs.1S.2TPG.
(39)§19Abs.1TPG.
(40)NJW 1999,3399ff.对此详见Roxin,in:Hberle(Hrsg.),60Jahre deutsches Grundgesetz,2011,S.65ff.(72f.).
(41)§173Abs.2S.2StGB.
(42)BverfGE 120,224ff.
(43)BverfGE 120,242.
(44)BverfGE 120,242.
(45)我发表在StV 2009,544ff上的论文,对该判决展开了详细的批判。
(46)参见M.Krau,LK,12.Aufl.2009,§130Rn 25.
(47)详见Gimbernat GA 2011,292f.
(48)详见Kühl,in:Bernsheim/Ulsenheimer(Hrsg.),Bochumer Beitrge zu aktuellen Strafrechtsthemen,2003,S.103ff.
(49)关于这个包含了五款之条文的具体内容,见Manfred Heinrich(Fn 6),S.135ff.
(50)Fr.-Chr.Schroeder GA 2009,217.
(51)M.Heinrich(Fn 6),S.135.
(52)Dubber ZStW 117(2005),508.
(53)M.Heinrich(Fn 6),S.148.
(54)Roxin,ATⅠ,§2Rn 13-49.
(55)Greco(Fn 6),S.199ff.(213).
(56)Mir Puig GA 2003,866.
(57)Romano(Fn 6),S.168.
(58)Romano(Fn 6),S.164.
(59)Romano(Fn 6),S.165.
(60)Roxin,ATⅠ,§2Rn 41.
(61)Sch/Sch/Perron/Eisele,StGB,28.Aufl.2010,§184bRn 15.
(62)Fr.-Chr.Schroeder ZRP 1990,299; ders.,NJW 1993,2581; ders.,Festschrift für Kaczmarek,2006,S.570.
(63)Roxin,Libro en homenaje a Eberhard Struensee,Buenos Aires,2011,S.505ff.(527ff.).现在发表出来的只有本文的西班牙文版。
(64)详见Roxin,ATⅠ,§2Rn 97ff.
(65)Achenbach StraFo 2011,422ff.(425).
(66)Achenbach StraFo 2011,426.
(67)Roxin,Schlussbericht zu:Neumann/Prittwiz(Hrsg.),Kritik und Rechtfertigung des Strafrechts,2005,S.175ff.(183f.).
(68)目前,对这一命题的全面引证见Trendelenburg,Ultima ratio?,2011,S.172-200.
(69)Theile,Wirtschaftskriminalitt und Strafverfahren,2009,S.5ff.
(70)对此持批判态度的有Achenbach StraFo 2011,426.
(71)Trendelenburg(Fn 67).
(72)Stratenwerth,in:Hefendehl/von Hirsch/Wohlers(Fn 1),S.255ff.
(73)Hefendehl(Fn 1),286做出了这样的总结。
(74)Stratenwerth(Fn 71),S.300.
(75)Wohlers,Festschrift für Amelung,2009,S.129ff.(138).
(76)Wohlers(Fn 74),S.137.
(77)Seelmann,Festschrift für Jung,2007,S.897.
(78)Bundestags-DrucksacheⅣ,650,376.
(79)Wohlers(Fn 74),S.139.
(80)Volk(Fn 6),S.215ff.
(81)Volk(Fn 6),S.220.
(82)Volk(Fn 6),S.224.
(83)Androulakis(Fn 9),S.279.
(84)Hefendehl(Fn 1),S.128.
(85)对此,参见下文对Gimbernat观点的批判。
(86)Gimbernat GA 2011,289.
(87)Hefendehl,Kollektive Rechtsgüter im Strafrecht,2002,S.57.
(88)Gimbernat GA 2011,284ff.
(89)Gimbernat GA 2011,288/289.
(90)Gimbernat GA 2011,288/290.
(91)Gimbernat GA 2011,288/290.
(92)Gimbernat GA 2011,292.
(93)Gimbernat GA 2011,289.
(94)参见Greco,Festschrift für Amelung,S.3ff.(15):“虐待动物罪的构成要件所保护的……是动物,而不是我们。”
(95)格雷科(Fn 93)提出的依据是,由于动物具备有限的自我决定的能力,故它们是需要保护的。
(96)Gimbernat GA 2011,289.
(97)Roxin(Fn 4),S.584f.
(98)仅参见我所指示的许内曼和施特恩贝格-利本(Sternberg-Lieben)(Fn 4),S.585Fn 71,72.的论述。
(99)Dubber ZStW 117(2005),516.
(100)Bacigalupo(Fn 5),S.12.
(101)Bacigalupo(Fn 5),S.14.
(102)Stuckenberg GA 2011,653ff.(658).
(103)Roxin(Fn 4),S.586(关于施特希林和哈塞默的引证,同Fn 76,77).
(104)Weigend,LK,12Aufl.2007,Einleitung Rn 7.Androulakis(Fn 9),S.277ff.也持同样的看法
(105)Sch/Sch/Lenckner/Eisele,StGB,Rn 10 avor§13.
(106)同样,Greco在ZIS 2008,238上撰文说:“总体来说,关于合比例性的检验就是以法益理论作为其前提的,因为我们在判断某一介入是否有用、必要和适当时,需要一个关联点。”
(107)Kaspar(Fn 26),S.168.
(108)Frister,AT,3.Kap.,Rn 32.
(109)Steinberg(Fn 23),S.102.
(110)BverfGE 120,242.
(111)参见上文第三部分第〈二〉点第1点中的引注。
(112)Frister,AT,3.Kap.,Rn 32.也持这种看法。
(113)BverfGE 120,242.
(114)Neumann,in:von Hirsch/Seelmann/Wohlers(Fn 1),S.136.
(115)安德罗拉基斯——在未与刑法典第183a条相联系的情况下——特别指出了这一点,(Fn 9),S.274,281Fn 36.
(116)BverfGE 47,109ff.
(117)赫恩勒(Hrnle)在2005年出版的《严重有伤风化的举动》(Grob anstiges Verhalten)这部专著中,提出了丰富的论证材料;专门针对刑法典第184条和184a-d条的根据和界限进行的论述,见Greco,in:Rechtswissenschaft,2011,S.275ff.
(118)特别是在关于“大规模窃听”的判决(BverfGE 109,279ff.)中。对此详见Roxin,Festschrift für Bttcher,2007,S.159ff.
(119)格雷科在新近的分析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Fn 36),S.73ff.。
(120)对此,详见Greco(Fn 118).
(121)格雷科在发表于ZIS 2008,234ff.的论文中做了如是论述。在该文中,他对联邦最高法院关于乱伦的判决进行了批判。对于格雷科的论点,也参见Kaspar(Fn 26),S.181ff.
(122)Greco ZIS 2008,234ff.
(123)格雷科也没有这样认为(ZIS 2008,238)。
(124)Romano(Fn 6),S.165.
(125)Gimbernat GA 2011,292f.
(126)Hefendehl,in:Hefendehl/von Hirsch/Wohlers(Fn 1),S.290.身危险性大小进行选择的过程,但无论怎样选择,都必须在刑法条文规定的法定刑的幅度内,不能超越”[18]的合法性理解,并不符合立法和司法实际。事实上,从立法和司法来看,刑法分则的规定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刑法规范。在立法上,它只是关于具体犯罪的特别犯罪构成要件和一般刑罚处罚的规定而已,并没有对具体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和可能适用的全部处罚方法( 刑罚处罚、非刑罚处罚、不给任何刑罚或非刑罚处罚) 做出规定。在司法上,这些不完整的规定,需结合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才能予以正确和准确的适用。仅就量刑而言,刑法分则关于抽象个罪的法定刑规定(立法),只是为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