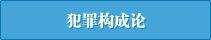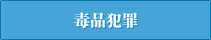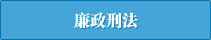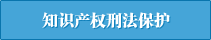弗朗西斯科·维加诺:意大利反恐斗争与预备行为犯罪化
[意]弗朗西斯科·维加诺(著) 吴沈括(译):《意大利反恐斗争与预备行为犯罪化——一项批判性反思》,载《法学评论》2015年第5期。
一、引言:全球化与意大利有组织犯罪
晚近以来,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意大利境内人员、商品、服务与资本的自由流动不断增强,为大规模谋利性犯罪活动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例如犯罪组织贩卖人口(尤其是妓女)、毒品、武器与儿童色情物品等以及相关的洗钱问题,而这一切往往都呈现跨国性色彩。
当然,意大利的特殊性在于有组织犯罪的“本土”传统由来已久,因为当地广泛存在强大的黑手党组织,他们将全球化视为千载难逢的黄金机会,使其能够扩张活动、增大收益.
此外,过去二十年间,移民不断涌入意大利,导致滋生特定族群以不同方式与传统黑手党合作的犯罪形式。贩毒几乎是在意大利活动的所有犯罪集团共有的特点,而拐卖妇女和强迫卖淫则主要由东欧和非洲移民犯罪集团实施。
然而,近年来,作为全球化发展的产物,在意大利最令人担忧的犯罪现象是源自极端势力的恐怖主义。到目前为止,意大利本土还未遭受恐怖分子的袭击,然而警方的调查一再表明,极端势力基层组织正在全国范围内渗透,主要是为亚洲和北非国家的大型恐怖组织提供后勤保障(尤其是制作假证件以及招募新“战士”送入训练营)。意大利和西班牙当局进行的一项调查还表明,2004年3月马德里爆炸案的制造者与意大利基层组织之间明显存在联系;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意大利存在原教旨主义洗脑中心,并且可能还存在军事技术应用培训中心;与此同时,当局查获了制造炸弹和其他爆炸装置的物资。这些事实首次表明存在针对意大利的具体袭击的预备行为,而在此之前,只有窃听到的一些零散对话内容,证明存在模糊笼统的袭击计划,这些对话源自负责招募“战士”并将其送往国外的个人。
面对有组织犯罪的威胁,刑法的重点由侧重于就已然造成的侵害科加“处罚”的传统逐渐转变为“预防”对作为整体的人民或社会造成进一步的损害[1]。细加审视,西方刑法制度——意大利也不例外——具有各种犯罪化规定,把为实施进一步(具直接侵害性的)犯罪而进行的单纯预备行为定为犯罪,从而使刑事执法机关能够及时干预,阻止罪犯实现其犯罪计划[2]。在此情形下,当事人会因发生在过去的罪行被逮捕和定罪;但判定其违反刑法规定的根本理由仅仅是为了预防其未来实施会对人民或社会造成实际损害的犯罪。使危险个体丧失犯罪能力而非实现罪有应得,这是该领域刑罚的主要目的。
这种模式在恐怖主义犯罪领域尤其明显。在基于恐怖主义目的对个人或社会造成实际损害的犯罪以外,意大利以及其他国家都制定了许多规定,把为进一步实施侵害性恐怖主义犯罪而进行的单纯预备行为定为犯罪。此类规定对刑事执法机关阻止恐怖主义犯罪图谋至关重要,可有效保护人民安全。
另一方面,预备行为入罪一直为法学学者所诟病。经典的刑法范式是反应式的:就本质而言,刑罚是并且应当是一项反应措施,其针对的是就造成的侵害承担责任的个人所实施的行为,而不是一项预防措施以防止行为人造成其尚不应承担责任的侵害。有人据此认为,预防是警方和情报部门应处理的问题,而不是检察官和刑事法院应处理的问题,后者的任务是判定已过去事件的法律责任,而不是防止危险。
这些反对意见正确吗?刑法是否应当放弃任何预防范式——或者,至少不将单纯的预备行为定为新罪,不将其作为抗制恐怖主义威胁的新工具——并坚持反应式模式,将预防任务留给其他组织承担?
基于晚近以来源自极端势力的恐怖主义所造成的威胁,通过分析意大利刑法采用的预备行为犯罪化立法技巧,考察预备行为犯罪化进路相较警方、情报机构预防犯罪策略有哪些优势和劣势,本文将对一系列根本问题予以相应的阐析。
二、 意大利有关预备行为的一般制度设计
(一)《意大利刑法典》中的原则和基本规则
根据《意大利刑法典》,预备行为原则上不具有可罚性。
《意大利刑法典》(以下简称:《刑法典》)第56条规定“任何人如果做出相称(‘idoneo’)并明确指向犯罪的行为,则应根据犯罪未遂的规范予以处罚”。尽管第56条并没有明确提及曾被拿破仑刑法典和几乎所有19世纪意大利刑法典采用的传统二分法“预备行为/实施行为”,大多数学者仍然认为,单纯的预备行为(例如为了后续杀人而合法购买武器)不属于犯罪未遂,因为此类行动应被视为“不明确”。
支持这一结论的普遍性观点是:首先,购买枪支可能不是为了故意杀人;其次,即使能够证明购买枪支的确是打算作为武器来故意杀人,但这种行为与实施应处以刑罚的犯罪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因为在此之前有足够的时间可以重新考虑,并且有可能放弃犯罪计划。只有特定犯罪的实际实施例如向被害人射击、下毒、意图抢劫时使用武器威胁他人等,才可被视为“明确”并可能作为犯罪未遂行为予以处罚。
第56条背后的法理在于,个人不得因坏的想法受到处罚,而应当因其所做出的危害行为而受到处罚。更准确而言,被告人实际造成社会侵害或者至少是发生该侵害的直接危险,通常被视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principio di offensività,即侵害性原则)[3]。本原则蕴含了三个基本判断,也即:
(1)刑法唯一合法目的是保护具社会意义之利益(beni giuridici,即法益),而不是推行道德准则;
(2)法院只有在其审理的特定案件中确信法益受到被告人的实际侵害,或者至少因被告人而处于危险之中时,才能适用为保护法益而制定的刑事规范;以及
(3)在法院确信法益因被告人而处于危险中时,该危险的性质必须是“可以合理预计被告人的行为将造成直接侵害”。
判断(2)及判断(3)均与《刑法典》第56条规定的犯罪未遂相关:“相称”要求是指被告人的行为必然会造成现实风险进而损害相关刑法规定所保护的法益(《刑法典》第49条从反面确认了这一点,明确排除了对不能犯未遂的处罚);而“明确指向”要求通常被解释为对法益造成直接威胁,从而排除了单纯预备行为所造成的远端威胁情形。
相较于犯罪既遂,犯罪未遂应受的处罚较轻。根据《刑法典》第56条,犯罪未遂的刑罚必须在犯罪既遂的刑罚基础上减少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如果因犯罪既遂被处以无期徒刑,则犯罪未遂的刑罚必须为12年至24年有期徒刑。强制减轻犯罪未遂刑罚的规定表明立法者关注的重点在于被告人行为的后果而不是意图:从这一角度来看,相较于产生实际侵害,仅造成发生侵害的危险应从轻处罚,即使行为人的犯罪意图在两种情况下是相同的[4]。
根据《刑法典》第115条一般规定,原则上,煽动和共谋本身不具有可罚性(“除非另有特别规定,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合意实施犯罪,而该犯罪实际上未实施,则其中任何一人不得因单纯共谋受到处罚……。如果未实施犯罪,同样的规则还适用于煽动实施犯罪……”)。煽动和共谋通常被视为单纯的预备行为,不会立即带来任何侵害,也不会造成发生侵害的直接危险。另一方面,只要主犯实际实施犯罪或者至少犯罪未遂,煽动和共谋均可能以共同犯罪的形式受到处罚。
(二)例外情形
当然,《刑法典》和意大利整体刑事法制框架下的某些规定并未遵循上述模式。
首先,刑法经常将特定犯罪的未遂行为本身规定为一种犯罪。这发生在所谓的“攻击罪(delitti di attentato)”领域,由有关刑法规定描述为“指向实施”特定犯罪的行为,或者概括而言就是企图造成特定侵害的“未遂行为”。例如《刑法典》第280条涉及“出于恐怖主义目的或颠覆目的,实施杀害或伤害他人的未遂行为的个人”;该罪的应处刑罚根据行为的实际后果而有所不同,但通常比杀人未遂的基准刑罚更为严厉。此类规定未明确规定“相称 ”和“明确指向”要求(这两项要求通常描述《刑法典》第56条涉及的犯罪未遂),并且在理论上可以诠释为也包括预备行为。不过,这两个基本要求被学者和司法判例视为默示要求[5]。因此,根据《刑法典》第280条,为杀害国务卿而购买枪支的人,在实际将枪指向被害人射击之前,不被视为有罪。
其次,对我们的考察更具意义的是,意大利《刑法典》和其他法律有许多刑事规定会对以下行为科处刑罚:该行为对法益的侵害性完全基于一项推断,即该行为造成了被告人或他人在未来实施进一步犯罪的危险。因此,上述规定应视为将预备行为上升为犯罪。在最后一个例子中,尽管为杀害国务卿而私自购买枪支的人没有造成实际侵害,也没有产生使任何人死亡或受伤的直接危险,但该行为人将被视为犯有非法持有武器罪:枪支购买者本人或第三人可能在以后使用枪支非法杀人的危险(非法持有枪支造成这种危险的程度明显高于合法购买武器的情形),通常被视为使刑法有充分理由在一开始就遏止这种苗头,进而预防未来犯罪。最近针对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的立法中,很大程度上已趋向这样的刑事责任模式,将招募、培训、制造或持有伪造的文件等活动规定为犯罪,并处以严厉的刑罚。
再次,毋庸置疑的是,诸项参与犯罪组织罪(《刑法典》第416条:犯罪组织;《刑法典》第416-bis条:黑手党组织;《刑法典》第270-bis条:恐怖组织或颠覆组织;等等)实际上都是预备行为入罪的示例。上述罪名成立的基本要求是,被告人或参与了该组织的犯罪活动(但不一定是实施了特定犯罪:例如提供犯罪工具包括武器、现金、车辆、手机等,或者付诸一般的犯罪预备行为),或已为犯罪组织完成了任何其他活动(与犯罪的实施没有直接相关性:例如藏匿恐怖分子,或者为其提供“正式”工作掩盖非法活动)。上述所有活动被视为与犯罪有关的理由在于,犯罪组织本身只要存在就会造成危险,也即组织成员随后会进一步实施犯罪(即所谓的“最终犯罪”),这与前段所述活动入罪的理由基本相同[6]。
最后,《刑法典》和其他法律的诸项规定——与《刑法典》第115条规定的一般规则相反——把为实施往往比较严重的特定犯罪而进行的单纯煽动或共谋定为犯罪。例如,煽动他人实施危害国格罪(《刑法典》第302条)是一项独立的罪名,参与共谋实施危害国格罪,但随后未实施或实施未遂的,共谋也构成独立的罪名(《刑法典》第304条);上述煽动和共谋行为面临严厉的刑罚(共谋最高判处6年有期徒刑,煽动最高判处8年有期徒刑)。另一方面,《刑法典》第414条规定,公开煽动犯罪和公开颂扬已实施犯罪的,最高判处最高5年有期徒刑;在最近出台的反恐法令(2005年第144号法令)中,当煽动或颂扬的犯罪是恐怖主义行为或者危害人类罪时,刑期可以提高到7年半。
三、 “恐怖主义”与“恐怖主义罪行”的概念
正如我们所见,预备行为无刑事意义的一般原则有不少例外情形,其往往涉及恐怖主义罪行。因此在进一步分析这些罪行的相关细节之前,阐明意大利法律体系中“恐怖主义”的含义至关重要。
“恐怖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1978年意大利刑事立法中。在令人震惊的“红色旅”(Red Brigade)绑架政要阿尔多·莫罗(Aldo Moro)案发生若干天后,一项新的罪名被纳入立法,也即出于颠覆或恐怖主义意图的绑架罪(《刑法典》第289-bis条)。之后,刑法于1979年规定了出于恐怖主义意图而实施杀人或伤害未遂行为的犯罪(《刑法典》第280条),并于2001年911袭击仅一个月后将既有的参与颠覆组织罪扩张至具有恐怖主义意图的组织。最后,《刑法典》引入了新的第280-bis条,惩罚任何出于恐怖主义意图而使用炸药或其他致命装置造成财物损失的行为。
当然,在新规定颁布之前,所有上述行为均已受到处罚,但规定的主要目的在于根据相关犯罪实施者的特定意图加重处罚。例如,根据《刑法典》第56条和第575条,杀人未遂通常判处7至14年有期徒刑,而根据《刑法典》第280条,具有恐怖主义意图的杀人未遂将至少判处20年有期徒刑。客观行为和杀人故意在这两种情况下的确是相同的;因此,之所以对后一情形予以更严厉的制裁,其差别性依据只能是行为人所追求的特定目的。
此外,只要行为实施者具有恐怖主义意图,就构成强制加重刑罚的依据(1979年第625号法令第1条),无论任何犯罪均是如此,而不仅限于狭义的典型恐怖主义犯罪。因此,
如果极端势力恐怖主义基层组织的一名成员为了资助其组织活动而犯盗窃罪,那么简单的盗窃罪就可能成为“恐怖主义”犯罪,会受到比普通盗窃罪更为严厉的制裁。
尽管“恐怖主义”的概念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但在2005年之前,意大利刑事法体系没有对其作出任何规范性界定[7]。由于之前恐怖主义被视为国内问题,这一缺陷并未引起相应重视:“红色旅”之类的国内组织兼具恐怖主义和颠覆特性,当时无人注意到分类问题。但是,当检察官和法官必须处理极端势力恐怖主义基层组织的活动时,严重问题出现了:这些基层组织并没有计划在意大利进行任何恐怖主义活动,只是为国外特别是中东地区的大型组织提供后勤支持,尤其是招募成员、筹集资金等。事实上,意大利各法院之间出现了相当多的矛盾,争论的焦点在于,这些组织的活动能否被视为“恐怖主义”活动:尤其在它们的目的是在武装冲突背景下攻击军事目标(国防部的主张如此)还是兼有攻击平民的意图并未确证的场合中[8]。
2005年7月,一项法律对“具有恐怖主义意图的行为”作出了立法界定(《刑法典》第270-sexies条),以期权威性地解决争议。“具有恐怖主义意图的行为”被定义为根据性质或内容可能会对国家或国际组织造成严重损害的任何行为,同时具备以下意图: (1)恐吓人民,或(2)迫使公职人员或国际组织从事或不从事某种活动,或(3)动摇或摧毁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根本政治结构。
该定义也适用于对意大利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或其他国际规定界定为恐怖主义的任何其他行为。
上述定义很大程度上与2002年6月13日欧盟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框架决议(2002/475/JHA)所规定的定义保持了一致。主要区别在于,意大利的规定未详细列举属于恐怖主义定义范围的具体行为。这引起了评论家的一些批评,他们指出“根据性质或内容可能会对国家、人民或国际组织造成严重损害的任何行为”是非常宽泛的描述,由此导致了模糊性。
当然,应当注意到,大多数恐怖主义罪行的客观行为特征由相应刑法规范予以描述,如杀害或伤害他人的未遂(《刑法典》第280条)、绑架(《刑法典》第289-bis条)、参与恐怖组织(《刑法典》第270-bis条)等,因此“造成严重损害可能性”的要求最终将成为判定恐怖主义行为的客观限制之一。
四、 煽动和共谋犯罪
(一)煽动和共谋实施危害国家的犯罪
根据《刑法典》第302条和第304条,煽动和共谋实施“危害国格罪”(此类犯罪包含与恐怖主义最相关的犯罪,如《刑法典》第270-bis条、第270-ter条、第270-quater条、第270-quinqiues条、第280条、第280-bis条和第289-bis条等规定的犯罪)构成独立的犯罪。如前所述,这两项规范均在《刑法典》第115条的一般规则之外规定了例外情况,而第115条规定,如果后续没有实际实施犯罪,对煽动和共谋均不会判处刑罚。
特别地,《刑法典》第302条规定:“任何人煽动他人故意实施本编第一章和第二章(涉及危害国格犯罪)所规定的罪行,但后续没有犯罪行为实际实施的,应处以1年以上8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刑期不得超过所煽动实施之罪的一半”。
根据《刑法典》第304条,“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合意实施第302条规定的罪行,但最后没有犯罪事实,所有合意实施该项犯罪的人均应处以1年以上6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提出共谋的人应加重刑罚。但刑期不得超过所煽动实施之罪的一半”。
当然,如果煽动或共谋实施的罪行已经具备犯罪事实,即使该犯罪事实处于未遂状态,那么《刑法典》第302条和第304条均不适用。在这种情况下,煽动或共谋犯罪的人应作为共犯予以处罚,因此,根据《刑法典》第110条所规定的一般规则(参见上文),其应承担刑事责任,量刑与犯罪实施人相同。因此,如果A煽动B实施恐怖主义犯罪(如绑架政治家C,迫使政府释放被捕的恐怖分子),在B实施绑架行为前,A将根据《刑法典》第302条承担责任;而从B实施绑架行为之时起,A和B均会作为违反《刑法典》第289-bis条实施(未遂或既遂)犯罪的共犯承担责任。
当然,《刑法典》第302条或304条规定的法律责任在原则上与第270-bis条规定的恐怖组织成员犯罪责任并不冲突。因此,虽然在这一点上目前没有具体的司法判例,但有理由认为,如果A作为极端势力恐怖主义基层组织成员煽动B绑架政治家C进行恐怖活动,则A同时犯有第270-bis条和第302条规定的罪行。
(二)公开煽动犯罪
《刑法典》第414条第1款规定:“公开煽动他人实施犯罪的,应处以下列刑罚:(1)煽动实施重罪的,处以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2)煽动实施轻罪的,处以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206欧元以下罚金。”
根据2005年7月增加的第414条第4款规定,如果煽动实施的是恐怖主义犯罪或危害人类罪,则应加重刑罚。这项新规定很可能旨在作为一项工具,打击清真寺中的激进讲道者。他们经常煽动信徒对抗异教徒并加入全球圣战。不过据笔者所知,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因这一项指控被起诉,可能是因为意大利检察官在处理涉及宗教问题的事宜时非常谨慎,以避免造成针对某些宗教本身发动“宗教战争”的错误印象。
第414条第1款和第302条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所煽动的对象:第302条规定的煽动必须针对一个或以上的单个人,而第414条第1款要求煽动发生在公共场所,并因此产生有人可能在煽动后实施犯罪的危险。“在公共场所”不仅指在同一地方存在大量人员,也指新闻或其他的通讯方式(《刑法典》第266条)——是否包括互联网网站值得商榷。
与第302条的罪行不同,是否有人实际实施所煽动的犯罪并无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公开煽动犯罪的人理论上有可能既应根据《刑法典》第414条第1款或第3款承担责任,又因受众中有人实施犯罪而根据共谋规定作为煽动者承担责任。
五、对恐怖主义犯罪的预备行为予以犯罪化的其他规定
(一)招募
2005年7月7日和21日伦敦爆炸案之后立即颁布的《刑法典》第270-quater条规定:“除第270-bis条规定的特定情况外,出于恐怖主义目的,招募一人或多人实施暴力行为或破坏基础公共设施,包括针对外国、机构或国际组织实施上述行为的,应处以7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
该规定未阐明“招募”的含义;在没有相关司法判例的情况下,首先对该法做出评论的学者认为,A推动B加入武装集团,成为集团新成员时,就表示A招募B。值得注意的是,只有A构成这项罪名,而B则可能构成《刑法典》第270-bis条规定的另一项罪名,即参加恐怖组织罪。另一方面,该规定不得与《刑法典》第270-bis条的罪名同时适用。在实践中,如果证据不足以证明A本人是武装团体或任何其他恐怖组织的成员,则适用第270-quater条。
在上述情况下,与2005年《欧洲理事会防止恐怖主义公约》宽泛的第6条相比,《刑法典》第270-quater条的适用范围狭窄得多。《公约》第6条规定:“恐怖主义招募”也指招揽他人实施或参与实施恐怖主义犯罪,或加入任何恐怖主义社团或团体(不一定是武装团体)。如前所述,对这种招揽行为应根据《刑法典》第302条或第414条第1款判处刑罚,具体依据哪一条规定取决于该行为是私下实施还是公开实施。
(二)培训
2005年生效的第270-quinquies条规定:“除第270-bis条规定的情况外,为实施暴力行为或破坏基础公共设施,就制造或使用爆炸物、枪支或其他武器、有毒或危险化学品或生物物质提供培训或指导,或者就其他方法或技术提供培训或指导的,包括针对外国、机构或国际组织实施上述行为的,应处以5年以下10年以上有期徒刑。对接受培训的人员适用相同刑罚”。
该罪名成立不取决于受训者(或接受指导的人)是否实际实施了其他恐怖主义犯罪。如果受训者使用从培训者处学到的方法或技术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则受训者将承担第270-quinquies条的罪名(连同培训者一起)以及恐怖主义行为本身的责任。但第270-quinquies条的罪行不能与参加恐怖组织罪同时适用(《刑法典》第270-bis条):如果A是恐怖组织成员,并为同一组织的成员B提供爆炸物使用指导,则A和B均只承担第270-bis条的罪名。
《刑法典》第270-quinquies条适用于培训者和受训者,以及任何提供指导的人员;对于简单接受讯息的人员并没有明确的刑事规定。因此,可以认为,个人如果仅仅持有显示军事方法或技术的视频,则不具备刑事意义,除非控方能证明此人目前正在受另一人的“培训”(即确证他与特定培训者处于稳定的个人关系中)。同样地,如果A在某个场合中向熟人B提供了一些视频,而警方在突击检查中从B的住处发现了这些视频,那么只有A应当为这一罪行承担刑事责任。
《刑法典》第270-quinquies条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欧洲理事会防止恐怖主义公约》(2005年)第7条的精神。
(三)伪造出国证件(《刑法典》第497-bis条)
与此同时,2005年与上述两项条文一并颁行的《刑法典》第497-bis条规定:“被发现持有伪造的有效出国证件的,应处以1年以上4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制造和生产虚假证件或出于非个人使用目的而持有的,前文规定的刑期应增加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实践表明,极端势力恐怖主义组织成员经常需要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以实现恐怖主义目的。2005年的立法出台了这项规定,打击这种使恐怖分子能够避开警方控制而跨越国境的行为,即伪造或以其他方式制作虚假身份证明文件。为增强该规定的预防作用,立法机关已将其适用范围扩大至只持有(无论是个人使用或用于其他任何目的)虚假证件而没有参与制作或生产虚假证件的人员。
六、与恐怖主义组织相关的犯罪
如前所述,意大利刑法中有不少规定涉及犯罪组织。尽管共谋入罪是意大利刑法制度的例外性规定(如《刑法典》第302条的情况),并且对于意大利检察官和法官来说也还较陌生(据笔者所知,还没有人根据《刑法典》第302条因共谋实施恐怖主义犯罪而被起诉),但涉犯罪组织的罪名在实践中往往成为打击有组织犯罪的重要法律手段:对犯罪组织嫌疑成员可以适用偷录和窃听等侵入式侦查手段,以及更长期拘留和特别程序规则;并且,如果审判认定其有罪,则会根据参加犯罪组织罪以及代表该组织实施的犯罪而对其科处刑罚。
(一)参加恐怖主义组织(《刑法典》第270-bis条)
在上述各项规定之中,《刑法典》第270-bis条规定的罪行涉及带有恐怖主义或颠覆目的的组织,它规定:
“推动、建立、组织、指导或资助意图实施暴力行为以实现恐怖主义目的或破坏民主秩序的组织的,科处7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
参与此类组织的,科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在刑法范围内,恐怖主义目的应涵盖针对外国、机构或国际组织的暴力行为”。
通常而言,有关犯罪组织的规定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处罚标准,分别针对一般成员和“特别”成员(如推动组织建立的人员,组织领导人等);其中更为严厉的处罚标准的适用范围已扩展到资助犯罪组织的人员(不要求必须是组织成员)。
刑事法院应评估组织的“恐怖主义”性质。法院不受任何恐怖组织官方名单的约束,如联合国或欧盟制定的名单。控方需证明整个组织意图实施具有恐怖主义或颠覆目的的暴力行为,至于暴力行为针对的是国内还是国外目标(如外国或国际组织)则不具决定意义。如我们所知,有关“恐怖主义”目的的定义在《刑法典》第270-sexies条之中。
学者和司法判例一般认为,一个组织的恐怖主义目的不能只停留于思想层面:申言之,《刑法典》第270-bis条不应成为使单纯思想异议入罪的手段;相反地,相关组织在整体上必须追求特定的犯罪计划。如果检方能够证明极端主义分子A、B、C定期举行会议,严厉批评美国和欧洲的国际政策,认为西方国家是“猪”,颂扬极端势力的“烈士”,甚至表达了为全球圣战而死的愿望,但这一情况仍然不足以支持按参与恐怖组织罪定罪,因为被告人的恐怖主义目的仍然过于模糊,并且可能被视为单纯的意识形态异议,而表达意识形态异议在意大利宪法第21条的保护范围之内。为支持对A、B、C以参与恐怖组织罪定罪,需要有证据证明存在具体犯罪计划(例如,在Y市X地铁站引爆炸弹)或至少存在为未识别的恐怖罪行而实施的预备行为(例如,集资或者 ——如意大利法院最近处理的各类案件——招募战士送到中东训练营)[9]。另一方面,不一定需要证明该组织已经实施恐怖行为——虽然此类证据(如果存在的话)的确有利于起诉。
除要求在性质上具有“恐怖主义”目的外,意大利法律没有对恐怖组织的特征做出其他严格要求。尽管一般犯罪组织至少需要具有三名成员(参见《刑法典》第416条,该条规定了参与犯罪组这项一般罪行),但在司法判例中可以找到一些决支持两名成员足以形成恐怖组织的假设;尽管学者们主张犯罪组织必须具备组成结构,并且成员之间具有明显的分工,但法院一般都愿意接受更低的标准,承认即使在无等级划分、无明确分工、无稳定组成结构的个人团伙也可能成立“恐怖组织”。
个人只要得到组织本身接受并分享其犯罪目的,就被认为是恐怖组织成员。在目前司法判例中尚不完全明确的是,以“参与者”的名义定罪是否还需要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在承担组织分配的具体角色时实付诸了积极活动。最高法院予以维持的一些判决坚持认为——对于黑手党——这种参与基本上是一种状态,可通过正式加入组织(根据其规则和礼仪)而取得;因此,如果有足够证据表明,被告人在双方同意基础上成为该组织的成员,则检方不必提供被告人付诸活动的证据[10]。该原则也适用于恐怖组织,特别是在没有证据表明被告人完成了特定活动时,只要能够明确表明被告人盲目服从组织领导者(即使是在领导者发出自杀式袭击命令时)[11]。
如前所述,不是恐怖组织成员、但明知该组织的犯罪目的而支持其活动的个人原则上应承担恐怖组织共犯的刑事责任,根据有关共谋的一般制度(《刑法典》第110条),刑罚层面应当适用第270-bis条针对单纯参加恐怖组织罪规定的相同处罚强度。
(二)协助恐怖组织成员(《刑法典》第270-ter条)
《刑法典》第270-ter条规定:“为第270-bis条所述组织的一名或多名成员提供庇护或食物、接待、交通、通讯手段的,应处以4年以下有期徒刑。持续提供协助的,刑罚予以加重。作为亲属而实施上述行为的,不承担责任”。
该条文对第270-bis条设立的一般规定进行了补充,规定的刑罚强度比适用于恐怖组织实际参与者的刑罚强度较轻。第270-ter条适用于并非恐怖组织成员,但为一名或多名成员提供了食物、手机等协助的个人,当然,前提是该人员不能构成整个组织的共犯。如前所述,如果该人应承担共犯罪名,则应根据共犯一般规定,按照第270-bis条规定的刑罚标准予以处罚。
七、 将表达或传播思想或观点(尤其是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思想与观点)定为犯罪
(一)颂扬(《刑法典》第414条第3款)
除《刑法典》第414条第1款规定的公开煽动犯罪的罪行外,该法典还对颂扬某项(已实施之)罪行的行为处以刑罚。
《刑法典》第414条第3款规定,公开颂扬一种或多种罪行的,应科处第1款规定的处罚(1年以下5年以上有期徒刑)。
根据2005年7月生效的第4款规定,如果颂扬涉及恐怖主义或危害人类罪的罪行,则应加重刑罚(刑期最高可达7年半)。
“颂扬”是指为犯罪辩解甚至称赞犯罪行为或犯罪人。对于这项罪的犯罪行为,法律并未作出更精确的表述,而犯罪意图必须是故意。对此类行为定罪的目的在于避免煽动(即使是间接煽动)实施同一性质的罪行。
但颂扬罪一直受到某些学者的严厉批评,他们多年来不断指出,该罪名使意大利宪法第21条规定的思想言论自由受到威胁[12]。事实上,意大利宪法法院在1970年的一项判决中认定这一定罪是合宪的,但补充指出,不应将颂扬理解为纯粹而简单的思想表达,在考虑到案件情况时,应该将其理解为可能引发犯罪的沟通交流(宪法法院1970年第65号判决)。因此,意大利宪法法院从根本上支持了一项最早出现在美国宪法判例法中的标准,也即只有为了阻止“明显而现实的犯罪危险”时才允许对言论自由加以限制。
后续司法判例大部分遵循了意大利宪法法院所秉持的立场,要求即使不确定存在实施犯罪的即时危险,基于事实情况,至少也要具备相关沟通交流后会出现犯罪行为的合理可能性。一方面,显而易见的是,该标准容易将激进讲道者在清真寺、网站或者以任何印刷或影音形式发表的演讲、陈述等(这些演讲和陈述旨在颂扬“战士”在对抗西方世界的全球圣战中的行为)包括在内。另一方面,法律的模糊措辞容易使相关规定适用于即使在极端势力范围之外也非常普遍的一种思想表达,即以正当防卫为由对指向以色列、美国和整体西方政策的恐怖主义行为作出正当化解读。当然,应该指出的是,到目前为止,意大利检察官非常谨慎,避免对单纯的异议表达提出任何指控。
(二)传播意识形态仇恨(1975年第654号法律第3条)
在此背景下,同样值得注意的是1975年第654号法律第3条规定的罪行(由1993年第122号法令修正),其明文规定:“除非当事人犯有更严重的罪行,否则:(1)传播种族或民族优越性或仇恨思想,或者煽动实施种族、民族、国家或宗教歧视行为的,应处以18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者6000欧元以下罚金;(2)以任何其他方式煽动他人实施,或者自己实施种族、民族、国家或宗教暴力行为或者暴力挑衅行为的,应处以6个月以上4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项规范处罚的不是明确具有恐怖主义性质的罪行;但制定这项规范在理论上可以涵盖针对不同宗教或民族群体的仇恨和暴力的煽动与传播——这种煽动和传播行为在极端主义者群体中非常多见。
八、 恐怖主义罪犯罪的刑罚
至于刑罚制度,学者和司法判例根据宪法规定的平等原则(宪法第3条)得出的犯罪严重性与刑罚轻重之间的比例原则通常要求,对单纯实施预备行为科处的刑罚应该轻于对直接造成损害的行为所科处的刑罚。这一主导性原则由意大利立法者广泛采用,但近年来有关国际恐怖主义的立法大大加重了单纯预备行为的处罚。
例如,参加恐怖组织(《刑法典》第270-bis条第2款)以及出于恐怖主义目的实施招募和培训(《刑法典》第270-quater条和第270-quinquies条)将处以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建立、组织或资助恐怖组织的将面临7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典》第270-bis条第1款)。此外,正如所见,助长恐怖主义行为属于加重情节,适用于不以这一目的为构成要件要素的任何犯罪(1980年第15号法律第1条)。
另一方面,涉及恐怖主义罪行的个人如果与警方或司法部门合作,刑罚会大幅度减轻,直至免于追究刑事责任。自1930年生效以来,《意大利刑法典》一直规定,在危害国格罪的案件中(正如我们所见,包括所有恐怖主义罪行),如果共谋者和犯罪组织成员在共同犯罪之前退出共谋或组织,或者以其他方式阻止共同犯罪,将对其免于追究责任(《刑法典》第308条和309条)。1979年第625号法令(后成为1980年第15号法律)第4条规定,对于与警方或司法部门合作以阻止恐怖或颠覆活动的个人,或者协助警察和司法部门收集相关证据以识别或逮捕共犯的个人,可以减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更彻底的是,该法第5条规定,对于阻止恐怖主义或颠覆性共同犯罪并同时提供必要证据以准确再现事实并确定共犯身份的个人,将免于追究责任。
普通罪犯和恐怖主义罪犯之间在刑罚层面更重要的差异在于监禁处遇。以恐怖主义罪行定罪的罪犯会置于特殊的监禁制度之下,该制度最初设计用于黑手党式组织成员。在该制度下,能否享有普通权利例如监外工作、短期离监、日间离监,缓刑等,通常取决于罪犯在查明共犯方面与警方和司法部门的合作情况(1975年第354号法律第4-bis条,后经2002年第279号法律修正)。如果罪犯不合作,则将一直在刑罚执行机构内服刑直至期满。
因涉及犯罪而被拘留或监禁的犯罪分子,如果与犯罪组织已经建立稳固联系,则会根据1975年第354号法律第41-bis条的规定,受到“强硬监禁”制度的管制:这是一项由司法部长根据个别案件情况签发命令的特殊监禁制度,旨在最大限度减少犯罪分子和犯罪组织之间相互交流的可能性,特别是采取强行限制与亲属联系、单独监禁、检查信件等方式。这项特殊监狱制度最初是针对黑手党成员,但最近已扩大到恐怖主义犯罪分子。
九、 刑法之外防止恐怖主义犯罪
即使在911事件以及马德里和伦敦爆炸案以后,在意大利法律制度中,打击恐怖主义主要仍然依赖刑事规范,由诸多独立的机构负责具体实施。因此,和多数欧洲国家一样,意大利并没有跟随美国路线采用战争模式来打击基地组织恐怖主义。相反地,尽管恐怖主义非常严重并且极其危险,意大利仍将其作为一种犯罪形式进行处理,通常采用刑法手段予以应对[13]。
在此图景下,与意大利宪法第13条的精神相符,上述事实意味着:如果有重大理由相信恐怖分子实施了犯罪,那么只有法官可以命令将其拘留,而警方则无权将其扣留超过48小时。
当然,在没有重大理由相信已实施特定犯罪的情形下,意大利法律设计了一些针对恐怖主义活动嫌疑人的预防措施。
如果当事人实际上已实施“指向(……)恐怖主义犯罪的预备行为(……)”(1975年第152号法律第18条,经2001年第374号法令修正),则法院可以下令采取其中某些措施。法院可以凭借低于刑事诉讼要求的证据标准下令采取措施限制人身自由,例如禁止在一个或多个城市或省份居住,或者不得离开居住城市(1965年第575号法律第2条)等。同样的程序和较低证据标准也适用于和财产相关的预防措施,例如:在恐怖分子嫌疑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资产价值与其声称的收入或经济活动不相称时,或在有充分理由相信该资产是非法活动所得时,可以没收资产(1965年第575号法律第2-ter条)。所有这些预防措施最初主要用于打击黑手党相关犯罪,在2001年911事件后扩展到恐怖主义分子。但该扩展只是理论上的扩展,因为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在抑制恐怖分子的危险性方面没有效果,而且,因为可以采用冻结资产的手段,没收资产的规定就显得多余。在欧盟层面,冻结资产是打击资助恐怖主义的手段,它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司法控制之外。
更为有效并且实践层面广泛应用的手段是针对在意大利合法或非法居住、涉嫌进行恐怖主义活动的外国人所应用的行政措施。2005年第144号法令第3条规定了驱逐令,其适用对象是实施恐怖主义犯罪预备行为的外国国民以及被认为在意大利能以某种方式协助恐怖主义组织或活动的外国人。驱逐令可以由内政部签发或者由省督代为签发。该命令产生立即生效并且无需经司法性批准,这一点与普通情况下签发的其他驱逐令不同。这项规定即使对刑事法院宣告无罪的人员也经常适用。因此某些学者对其提出了严厉批评,指出对驱逐出境的依据完全不作司法审查会带来风险,并且可能将被驱逐人置于或许会对恐怖主义嫌疑人实施刑讯逼供的国家的警察机关手中。在最近几个月,欧洲人权法院实际上已经多次要求意大利政府不要驱逐恐怖主义嫌疑人,理由正是他们在目的地国家可能会受到欧洲人权公约第3条所禁止的酷刑或处遇。
十、批判性反思
(一)与宪法保障和基本权利的协调性
如引言中所述,意大利反恐怖主义立法与一般有组织犯罪的刑事立法一样,受到了某些学者的强烈批评[14]。
基于上文述及的法益“侵害性原则”,也即引入刑事立法规定仅旨在阻止发生损害的直接危险,他们甚至质疑将预备行为入罪的合宪性。同样具有争议的是对单纯参与犯罪组织的刑事处罚,因为将仅有共同犯罪意图的情况规定为有罪具有风险性。同样受到严厉批评的是有关机关仅仅因为普通犯罪伴随恐怖主义目的就对其加重刑罚的做法,有论者认为这也违反了直接危险的要求,因为加重情节凭借的依据只是一种心理状态。此外,许多学者批评了上述规范的模糊表述以及现行《刑法典》第270-sexies条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最后,针对恐怖主义分子的特殊监禁制度是否符合宪法第27条第3款规定的刑罚再教育功能,也有学者表达了强烈的保留意见。
在与受宪法保护之基本权利的协调性层面,最大的问题可能存在于前述《刑法典》第414条中所规定的颂扬罪。适用该规定最明显的风险在于可能过度限制宪法第21条所保护的思想自由。
最近,在总结上述批评和其他相关批评时,许多学者担忧意大利刑法制度可能滑向德国刑法学者甘瑟·雅各布斯(Günther Jakobs)所描述的“敌人刑法”(Feindstrafrecht)模式,这一模式对涉及的个人不认定为普通罪犯,而是根据其意图和目的认定为敌人——当然,由此隐含的实践结论是,对敌人不应“改造”,只能“打击”[15]。
雅各布斯的言论在意大利引起了激烈争论[16]。人们一般拒绝采用恐怖分子-敌人模式,而对于是否有可能为打击恐怖主义而调整宪法保障和基本权利,意大利学者持不同的态度:有论者重申,即使是在涉恐案件中也要完全遵循“经典的”刑法原则(例如,拒绝对单纯的预备行为定罪并采取不同的监禁服刑方式),而其他人则更倾向于适当放宽上述原则,以保护公共安全免遭恐怖主义袭击,但同时应当坚持“公正审理”蕴含的基本保障和个人基本权利的核心价值——包括免受酷刑和未经司法审理不被剥夺自由的权利。
直至今日,意大利宪法法院的判例几乎都支持特殊反恐法律(反映在实体刑法、监狱法以及刑事诉讼法等诸多规范之中)。宪法法院在1980年的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判决中申明,在紧急情况下,允许通过特殊法律对基本权利加以重大限制,前提是这种紧急情况有时间限制,不会变为“永无止境”的紧急[17]。对于颂扬罪,如前所述,意大利宪法法院的判决认为,该罪行只要适用于可能引发犯罪的沟通交流,就符合宪法。无论如何,意大利宪法法院目前似乎不大可能宣布前文所述的任何特殊规范完全不符合意大利宪法确立的保障原则以及基本权利。
(二)改革建议
公开批评现行反恐刑事立法的人士只是要求撤销所有特殊规定,恢复刑法的一般原则。他们认为刑法的一般原则足以应付恐怖主义威胁,要求取消为恐怖分子保留的的特别监禁制度,同时也批评对同法律合作的人所做出的让步。
虽然上述批评在学术界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但他们在政治和舆论层面的影响不大;相反地,主流的声音是应当尽可能强化这些手段保障公众安全,进而应对源自极端势力的恐怖主义威胁。
据笔者所知,自最近2005年7月的立法改革(引入了本文分析的诸多措施)以降,没有人提出改革实体刑法领域现行规范的具体要求。相反地,加强恐怖主义相关调查活动之协调的诉求增多:目前,涉恐调查由25个专业辖区检察机关进行处理,这种协调在事实上可通过建立国家反恐检察官办公室来实现,具体运作模式可参照目前反黑手党检察官办公室予以细化。
(三)结语
在打击严重有组织犯罪尤其是恐怖主义时,预备行为的广泛入罪引出了有关刑法作用的基本问题。“经典”刑法的特点是被动反应模式,即事后介入,对已实施并造成法益侵害的行为予以制裁,而这种模式在今日时代背景下已陷于危机之中:一种不同的预防性模式似乎已呈现取而代之的发展态势,这种模式首先要求刑法防止损害的发生,在犯罪者实施犯罪计划之前即予以介入。
从前一模式到后一模式的转变在全世界的刑法学者中引起了激烈额争论,这些学者不仅观察到了这种现象,而且也提出了猛烈的批评。着重于预防的刑法必然会诉诸侵犯个人隐私的侦查手段(通讯窃听、便衣警察等)以搜集证据证明存在预备行为,即使预备行为仍然远离潜在被害人的“领域”。不可避免的是,这一模式会将更多的权重放在个人犯罪意图而非侵害被害人利益的外在行为。
另一方面,从前一模式过渡到后一模式的过程中,传统上赋予刑罚的功能也产生了显著的改变:刑事干预的焦点不再是威慑(人们断定对愿意牺牲性命的恐怖分子而言,威慑影响不大),也不是对侵害(尚未造成)的报应,甚至也不是改造罪犯(人们断定对于认为自己在与科处刑罚的国家进行战争的个人,改造是徒劳的),而是着眼于及时打击危险个体——首先必须阻止其侵害社会。在此图景下,与其说根本角色定位在于惩罚,不如说是在于审前防护,这一功能倾向于从单纯服务于审判需要的手段转变成为保护社会免遭危险个人攻击的真正前哨。
刑法学者提出的各项保留意见虽然可以理解,但是似乎已不太可能阻止刑事司法体系从被动模式转变为主动模式。保护公共安全(注意:它已越来越多地被视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因其本身性质逐渐倾向于这种转变,因为根据传统的犯罪未遂规则,要求刑事有权机关必须在刑事攻击开始后才能介入干预,这对民意和政治家来说并不合理。毫无疑问,人们期望通过对单纯预备行为以及参与恐怖组织行为作出犯罪化处理,从而尽量避免恐怖袭击,哪怕会以犯罪发生前就对(潜在的)行为人限制其人身自由为代价。
此外,必须注意的是,相较于可以想象的其他替代性预防手段,刑法能够提供更多的保障。试想,在意大利法律制度中,因受到犯罪(即使只是预备行为)指控而被拘留的个人,在拘留开始后便对指控和证据来源享有知情权,而且在被逮捕几天后便可以在法官面前实际行使自我辩护的权利;随后,他能够根据与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相符的程序性规则,在合理的时间期限内获得公平的审理。而在对嫌疑人无期限行政拘留这一相反模式中,则完全没有上述保障:在911事件之后发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布什政府正是采用了这一模式。
在此意义上,捍卫刑法和刑事司法在打击恐怖主义中的角色——哪怕以接受某些明显偏离“经典”模式的做法为代价——将意味着捍卫被告人以及所有人身自由受到国家机关限制之人士的一些基本权利。在目前形势下,基于预防的刑法模式或许是同时满足公共安全保护需要以及维护个人权利和保障之核心内容的最佳妥协。[18]
[1] 参见Hassemer, W. Sicherheit durch Strafrecht, HRRS 2006, p. 130。
[2] 另见Viganò, F, Incriminazione di atti preparatori e principi costituzionali di garanzia nella vigente legislazione antiterrorismo, ius17@unibo.it, 2009, 1, p. 171。
[3] Marinucci, G., Dolcini, E., Corso di diritto penale, 3d ed., 2001, p. 528。
[4] 同前注,第529页。
[5] 同前注,第577页。
[6] 关于这一点亦可参见De Vero, G., Tutela dell’ordine pubblico e resasti associative, Riv. it. dir. proc. pen., 1993, p. 93。
[7] 关于这一点另见Valsecchi, A., Il problema della definizione di terrorismo, Riv. it. dir. proc. pen., 2004, p. 1150。
[8] 参见Viganò, F. Terrorismo di matrice islamico-fondamentalistica e art. 270 bis c.p. nella recente esperienza giurisprudenziale, Cass. pen., 2007, p. 3953。
[9] 参见Viganò, F., Il contrasto al terrorismo di matrice islamico-fondamentalistica: il diritto penale sostanziale, in De Maglie, Seminara (eds.), Terrorismo internazionale e diritto penale, 2007, p. 136。
[10] 参见Viganò, V., Riflessioni conclusive in tema di ‘diritto penale giurisprudenziale’, ‘partecipazione’ e ‘concorso esterno’, in Picotti-Fornasari-Viganò-Melchionda (eds.), I reati associativi: paradigmi concettuali e materiale probatorio. Un contributo all’analisi e alla critica del diritto vivente, Padova, 2005, p. 315。
⑪ 参见Viganò, V., Il contrasto al terrorismo di matrice islamico-fondamentalistica: il diritto penale sostanziale, in De Maglie, Seminara (eds.), Terrorismo internazionale e diritto penale, 2007, p. 147。
⑫ 进一步的文献参见Pelissero, Delitti di istigazione e apologia, in Palazzo-Paliero, Trattato teorico-pratico di diritto penale, IV, 2010, p. 234。
⑬ 参见Viganò, F., Terrorismo, guerra e sistema penale, Riv. it. dir. proc. pen., 2006, p. 659。
⑭ 相关讨论与文献亦可参见F Fasani, F. Terrorismo islamico e giustizia penale, 2014, p. 334。
⑮ 亦可参见Jakobs, G, Bürgerstrafrecht und Feindstrafrecht, HRRS, 2004, p. 88。
⑯ 参见Donini, M., Il diritto penale di fronte al “nemico”, Cass. pen., 2006, p. 735。
⑰ 宪法法院1982年第15号判决。
⑱ 更广意义上,可见Viganò, F., Terrorismo, guerra e sistema penale, Riv. it. dir. proc. pen., 2006, p. 679。
∗本文意大利原文为La lotta contro il terrorismo e la criminalizzazione degli atti preparatori in Italia,系作者(意大利名字为Francesco Viganò)原创。该文系中国首发。本文的翻译受北京市社科联青年社科人才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4SKL007)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15CFX035)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