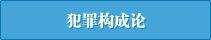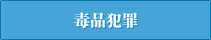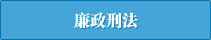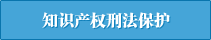Emilio Dolcini:意大利法律制度中的犯罪:概念及其体系论
【意】Emilio Dolcini 著, 吴沈括 译:《意大利法律制度中的犯罪:概念及其体系论》,载《清华法学》2016年第1期。
【摘要】在意大利法律制度中,当法律针对某一行为规定一项刑罚时,该行为构成犯罪:犯罪成立以及与其它各类非法行为相区别的基础仅是一项唯名论标准。历史地看,犯罪学与刑法学理论都试图超越形式定义努力找寻犯罪行为的实质内涵,也即不是基于刑罚处罚而是反映犯罪内在属性的本质界定。有关犯罪的各种实质概念表面看起来仅具有描述性特质,但事实上它们追求的是明确的意识形态性功能,也即使现行刑法具备或者丧失合法性以及推动某一方向的规范演进。当前历史语境下,无论是在犯罪构成的建构层面,抑或是在罪刑规范的内容层面,引导意大利立法者选择的不再是若干模糊的本体论标准,而是作为普通法律之上位法渊源的宪法。此外,研究犯罪时还应当补充不同的考察进路也即分析型进路,有必要区别分析每个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并依据精准的逻辑-系统顺序予以排列。
【关键词】犯罪 体系论 违法 有责 可罚
一、犯罪的形式概念
在意大利法律制度中,当法律针对某一行为规定了一项刑罚(pena)时,该行为构成犯罪:犯罪成立以及与其它各类非法行为相区别的基础仅仅是一项唯名论标准(即立法者冠以“刑罚”之名)。[[1]]
当然,并非所有的刑罚都具备确定犯罪的功能。事实上,这一任务只赋予各项主刑(pene principali)也即:(意大利刑法典[[2]]第17条规定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罚金、拘役和刑事罚款;此外,还包括军事犯罪领域的军事有期徒刑(由意大利和平军事刑法典第22条规定)。
至于死刑,在1994年10月13日第589号法律之前,曾被战时军事刑法规定为主刑。目前,意大利宪法第27条第4款,经2007年10月2日第1号宪法性法律依循2002年于立陶宛维尔纽斯签订、2003年生效的《欧洲人权公约第13号议定书》修正后,明确规定绝对禁止在意大利法律框架内重新引入死刑制度。
此外,针对和平法官(Giudice di Pace)有权管辖的各类犯罪,在2000年导入了新的主刑种类,也即居所监禁(permanenza domiciliare)以及公益服务(lavoro di pubblica utilità):然而,这两项刑罚并没有发挥确定犯罪的功能,因为它们总是被规定为罚金或刑事罚款的替代刑罚(见2000年8月28日第274号法令第52条)。
一项主刑的规定有助于犯罪与行政不法行为之间(illecito amministrativo)的彼此区分。特别地,当法律科处罚金(适用于重罪的金钱罚:刑法典第18条)或者刑事罚款(适用于轻罪的金钱罚:刑法典第18条)时,相关事实成为一种犯罪行为,而所有未被规定为罚金或刑事罚款的其它金钱罚则具有行政处罚的属性。
另一方面,在意大利法律制度中,行政金钱罚并没有对应的技术性名称。包括《刑事制度修改法》(1981年11月24日第689号法律)在系统规定由金钱罚处罚的行政不法行为(而不是纪律与金融违序行为)时,同样采用了相对笼统的措辞也即“支付一笔款项的行政处罚”(见该法第12条)来界定法律的“适用范围”。更为晚近的2001年6月8日第231号法令,针对依附于犯罪的行政不法行为按比例科处金钱罚时,所遣用的表述是“行政金钱罚”(见该法第9条及以下):从而进一步强调了此处涉及的“新型”单位责任的非刑罚性质。[[3]]
同样地,相较民事不法行为(illecito civile),确定犯罪的唯一标准仍然是主刑这一形式符号:如果某一行为构成民事不法,但同时并没有受到一项主刑处罚,那么这一行为毫无疑问处在刑法规制范围之外。当然,同一行为可以既构成一项犯罪又构成一项民事不法。在此情形下,意大利法律做出了特别的制度安排。为了缓和犯罪受害人的报复行为,将损害赔偿的范围扩展及于“非财产性”损害,同时为此目的规定了各类民事性质的处罚,具体包括“返还”(restituzioni,刑法典第185条第1款)、“损害赔偿”(risarcimento del danno,刑法典第185条第2款)以及“公布有罪判决书”(pubblicazione della sentenza di condanna,刑法典第186条)等。
二、对犯罪实质概念的无结果的探索(以及刑法与道德之间的涵摄关系)
一直以来,犯罪学理论与刑法学理论都试图超越犯罪的形式定义,努力找寻犯罪行为的实质内涵,也即不是基于刑罚处罚而是反映犯罪内在属性的本质基础。[[4]]
历史地看,犯罪学家最早开始对犯罪实质概念的探究,希望在本学科范围内找到一项有关犯罪的不受国家法律制度条条框框束缚的概念。[[5]]
对犯罪做出实质界定的首次尝试出现在犯罪学肇始阶段:加罗法洛(Garofalo)针对“自然犯罪(delitto naturale)”的定义是“对表现为利他、正直与怜悯等诸多情感的那部分道德意识的损害,这一损害事实伤及[...]这些情感[...]最共通的部分,后者被认为是社会共同体中每一个体不可或缺的道德财富”。[[6]]此外,晚近以来则更多地倚重“越轨行为”(condotta deviante)这一社会学概念,后者勾勒的是偏离公认行为模式、与社会期待不相符的行为。[[7]]
然而,这些尝试都没有获得成功,因为各自提出的犯罪概念均有失于笼统且模糊。[[8]]有关“越轨”的现代概念也只是一项空洞的表述,本身并不能表达犯罪行为的特殊属性。事实上,任一犯罪都由“越轨”行为构成(因为其不符合刑法规范所描述的行为模式),但不是每项越轨行为都会构成犯罪[[9]]:只有立法者有权在诸多越轨行为中遴选他认为值得和需要予以刑事处罚的行为。
有关犯罪更为丰富多样的实质定义见诸于刑法学理,其中大部分是基于刑事规范与道德-社会规范彼此交织的理念:任何犯罪都可能是对“最低道德”、“文明规则”以及“社会道德”的违犯。
秉持此类观点的论者包括两位20世纪权威刑法学者:他们是意大利的文森佐·曼齐尼(Vincenzo Manzini)和德国的汉斯·威尔兹尔(Hans Welzel)。
根据曼齐尼的见解,“刑法是维系某一政治-社会组织的必需条件所不可或缺的、充分的道德量的最低限度(是底限的底限)”。[[10]]
威尔兹尔的主张是:“所有罪刑规范都禁止不道德的行为(也即在社会层面有违伦理道德的行为)”。 [[11]]在此意义上具有典型意义的示例是乱伦、嫖娼以及公职人员积极腐败行为的犯罪化处理;另外,有关盗窃的规范也同样包含着对不道德行为的禁止:威尔兹尔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所有规范的一般无价值内容就是因为在社会层面不道德而受到禁止的行为”。
然而,与犯罪行为是对特定社会中“最低道德”之违犯的理念相抵牾的事实是,实践中存在一些不具有刑事意义的行为,绝大部分社会成员认为其严重违犯道德;而有的行为具有刑事意义,但却不产生或者仅产生微弱的道德-社会影响,[[12]]甚至有些犯罪化处理与特定社会的全部或部分道德规范相背离。[[13]]曼齐尼本人也认识到了这种背离,并承认,与其它国家法律制度一样,在我国法律制度中,“最低道德”有时会受到某些刑法规范的践踏,这些刑法规范建构的基础是“畸形的绝对国家体制,或者已是昨日黄花的其它暴政[...],故而确实存在不道德的法律,因为它们与我们文明的根本原则相违背(这正如那些反犹太人士的法律)”。[[14]]
晚近以来,以卢曼(Luhmann)建立的法律“功能主义”理念为基础,[[15]]出现了认为刑法应该发挥“社会融合”功能的看法。在此意义上,刑罚的功能应当是“促进规范的认知”,催生“对规范的信任”、“对法律的忠诚”以及违反它们的“后果担当”[[16]]:换而言之,“刑罚的任务是维持规范从而确保其作为社会关系的指导范式”。
这一主张隐含的前提是卢曼认为刑法在各复杂社会形态中充当着社会规范的投影以及维持社会稳定的工具。[[17]]而其他学者则明确突出了这一逻辑前提,赋予刑法以“支持”社会规范的功能。[[18]]
基于这一思想逻辑,犯罪被定义为“一种负态功能现象,它阻碍或者使人们难以解决同维护社会存续有关的各项问题”。[[19]]
当然,从经验事实的角度而言,认为刑法具有“社会融合”的功能,并据此始终只惩治同时违反刑事规范和社会规范的行为的主张,并不能经受住任何具体时空情境的考验。事实上,在某个特定社会中,可以同时存在许多相互抵牾的价值判断;而立法者在将此行为或者彼行为予以犯罪化处理时,总是需要做出政治层面的选择,使一种价值判断优于另一种价值判断。一位伟大的意大利刑法学家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指出,[[20]]“任何刑事立法都是基于一定的道德理念,但这些道德理念正是占统治或特权地位的立法阶层的理念;[...]主张刑法领域存在某种直接民主,法律的意志就是作为整体的全部人民的意志,这无异于断言理想便是现实”;另一方面,“正如德拉帕利斯(de la Palisse)先生所言,多数人的意见不能等同于少数人的意见。”
在一种专制的政治体制下,少数人的意见甚至没有机会得到展现;而在议会民主制政体中,社会上并存的多种价值判断将在议会-政治论辩环节得到充分的展示。事实上,在某一罪刑规范的背后往往存在不同的道德-社会规范,在此基础上,借助专制力量或者通过社会以及议会的论辩,由掌握政治-立法权力的主体赋予其中一项规范以优势地位。
根据卢曼的见解,赋予刑法以“社会融合”的功能,旨在借助刑事强制的力量支持和维护只为部分社会主体所共有的利益以及价值诉求。[[21]]
上文考察的有关犯罪的各项“实质”概念,尽管在描述现行刑法规范时存在不足,却可能作为刑事政策标准(criteri di politica criminale)被纳入考虑的范围:申言之,为立法者在作出犯罪化选择时提供指导性准则。正如上文所揭示的,各种不同概念之间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主张犯罪行为必然违反了特定社会中先前已经存在并且得到固化的道德-社会规范:由此产生的结论是,如果不存在已经固化的道德-社会规范,立法者就应当放弃创制新的罪刑规范。
然而,如此意义上的刑事政策指针不见得可以被接受、具有可行性。
事实上,基于社会道德建立的刑法,也即以特定历史时期实际占据主流地位的道德理念为基础建立的刑法,很难发挥批判的功能。这类刑法“限于维护特定历史形态下的‘道德秩序’。一方面,‘道德秩序’所传递的各项价值判断可能早已失去了它们在另一个历史背景下或许具有的意义,不再值得通过刑罚对其给予支持。另一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道德意识往往滞后于社会、经济以及技术发展,以至于不能对基本问题作出有效的应对。相反地,如果要求刑法应当对社会演进做出合理的回应,那么同时就必须具备‘开路者’的功能,建构新的规范从而应对重要法益所面临的新威胁【……】。如此而言,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为了决定哪些类型的行为应当构成犯罪,需要求诸不同于道德-社会标准或者更具进一步意义的其它标准”。[[22]]
一种可能的情形是,某些损害经济、环境或者公共健康的侵害行为的危害性仍然不为全社会所认知,或者仅有部分认知:但这并不意味着立法者对于此类现象就应当保持缄默,而且,从另一方面看,不能排除或迟或早全社会都会认识到对于这些行为值得并且需要通过刑罚予以惩治。
因此,刑法不是也不必须是特定历史语境下先存、固化并且为全体成员所认可的诸项道德-社会规范的单纯宣示。另一方面,在一个世俗化的国家(意大利宪法对此做了明确的顶层设计),“行为的反道德性不是导致刑罚反制的充分理由”。[[23]]
当然,上述论断并不意味着刑法与道德运行在两条没有交集的轨道上。事实上,刑法的一般预防以及特殊预防效力在很大程度上与道德-社会价值判断呈现交织的态势。反映主流道德-社会规范的刑法规范不会陷于专横、武断,因此能最大程度地引导相对人的行为方式;[[24]]在出现违反的情形下,刑罚能为犯罪人所理解,从而有助于防止其进一步犯罪。[[25]]
如果罪刑规范惩处一项对个人法益或集体法益有害的行为,即使它或许仍未受到社会的否定,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在或短或长的时期内该刑法规范将催生一项对应的道德-社会规范:这是一般预防的组成部分,[[26]]早期学理[[27]]和现代学理[[28]]将其视为刑法的“道德化”功能或者“文化引导”功能。
而与特定社会中主流价值判断相冲突的刑法规范则可能陷于失效。禁止实施社会认可的行为以及强令付诸社会否定的行为都无法在相对方的眼中找到合法性。不仅如此:倘若刑法对于被视为第一序列的法益不给予保护或者不提供相称的保护,却以极端的方式保护明显价值位阶更低的法益,它就可能“丧失导向和指引的能力,甚至可能成为滋生犯罪的其中一项主要因素”。[[29]]
总而言之,刑法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关系既非偶然相交,更非毫无关联:应当认为是一种相当复杂、精致的“涵摄关系”。[[30]]
三、立法者界定刑事不法行为时采用的指导标准
学理层面所提出的有关犯罪的各种实质概念表面看起来仅具有描述性特质,但事实上它们追求的是一项明确的意识形态性功能,也即使现行刑法具备或者丧失合法性,以及推动某一方向的规范演进。[[31]] 然而,细加审视可以发现,当下历史语境下,无论是在犯罪构成的建构层面,抑或是在罪刑规范的内容层面,引导意大利立法者之选择的机能不再取决于本体论意义上的诸项标准,而是作为普通法律之上位法渊源的现行宪法。
正是在宪法规定的基础上,立法者能够——而且应当——据此回答刑事领域每一个选择都必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什么使运用刑罚(也即各种法律惩罚中最严厉的处罚)具有合法性?
事实上,应当强调的是,在不同类型的国家中,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尽相同。[[32]]确然地,在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中,基于神圣正义的思想,刑罚可以被视为对犯罪固有之恶的报应进而获得合法性:因此,任何不道德或邪恶的行为都有可能被认定为犯罪并受到镇压。而在一个极权国家中,崇尚的是公民无条件忠于法律,因此要求刑罚承担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实现这一目的,包括采用严酷的措施,着力强化对犯罪人的恫吓并消除其重新犯罪的机会:在此图景下,挑战国家权威的任何迹象性事实均有可能被认定为犯罪而受到惩处。
目前,意大利宪法勾勒的国家形态是一个多元化的世俗国家,其核心价值是宽容与人的尊严,所有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33]]在这样一个国家,立法者不能为追求威权目的或者道德目标而诉诸刑罚:刑罚不能成为报应的工具,不能用于追求高于正义的理念,通过同等的恶来报复犯罪的恶;因此,不能因为各种道德律令谴责某一行为就通过刑罚对其加以惩处。另一方面,意大利宪法保障自然人个体享有一系列权利进而在此基础上以公民而非臣民的身份参与国家生活:所以,立法者不得利用刑罚作为无差别威慑工具以镇压一切对国家不忠的行为以及危险人格的表征事实。
只有基于一般预防(prevenzione generale)的维度,意大利立法者求诸刑罚才具有合法性:刑罚只能作为法益的预防性保护工具(strumento di tutela preventiva di beni giuridici)而得以运用。立法者通过刑罚威胁所追求的一般预防效果受到特殊预防(prevenzione speciale)尤其是宪法(第27条第3款-译者注)明确赋予刑罚的再教育功能(rieducazione)的制约:立法者威胁适用的刑罚的种类和幅度不得在实际科处以及执行的环节对被判刑人的再教育产生不利的影响。[[34]]
那么,对于社会成员的哪些行为可以通过刑罚的威慑予以合法地遏制?根据贝卡里亚的见解,我们可以回答:只能是那些造成一项“社会损害”的行为;借助现代刑法学的语辞:损害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条件或者置其于危险的行为。[[35]]
在犯罪构成(struttura del reato)层面,这一要求外化为侵害性原则(principio di offensività)[[36]]:根据该原则,如果没有侵害一项法益(benegiuridico)也即某种承载价值的、可以施加改变的、可能因人类行为而受到损害的事实或法定情形,那么就不能认为是犯罪。因此,立法者不得单纯基于某人“是谁”或者“意图怎样”而对其施加刑罚,而只能处罚损害法益完整性或者置其于危险的行为。
只有针对侵害法益的行为,立法者才能通过刑罚予以惩处,这一点已为意大利宪法法院所认可。其明确主张:“规范制定领域要求的必要侵害性原则”正是“宪法层面对普通立法者自由裁量权的制约”。[[37]]意大利学理也正确地指出,在宪法规定的国家形态下,立宪者为了揭示犯罪与刑罚的法定主义原则以及刑法规范不溯及既往原则所遣用的“事实”一词(宪法第25条第2款),蕴含着“法益侵害性事实”的意思。[[38]]
另一方面,立法者诉诸刑罚的合法性基础不是任意一项法益侵害,而只能是有责基础上造成的侵害:申言之,限于能够对其行为人予以人身性谴责的侵害事实。由此,有责性原则(principio di colpevolezza)成为指导、限制立法者做出犯罪化选择的诸项原则之一,它是刑事责任人身性(personalità della responsabilità penale)这一宪法原则(宪法第27条第1款)的外化,[[39]]并且与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密切相联。[[40]]事实上,如果科处刑罚的目的是引导社会成员的行为选择,那么只有在受到禁止的事实是行为人自由选择的结果,或者至少是他通过合理审慎能够避免的情形下,才可能实现这种预期的激励效果:意图通过刑罚威胁使相对人排除不在其控制范围内的行为,这是没有意义的。
遵循侵害性原则和有责性原则是立法者合法付诸刑罚的一项必要条件,但仍不构成充分条件:事实上,有关犯罪化的立法选择还应当受制于进一步的约束,尤其是比例原则(principio di proporzione)或比例性原则(principio di proporzionalità)以及补充性原则(principio disussidiarietà)。[[41]]
特别地,比例原则提出的要求是,通过科处刑罚所追求的社会效益(预防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应当与刑罚本身蕴含的成本(尤其是人身自由、财产以及名誉等方面的牺牲)在观念层面做相应的对比。如果从社会效用角度看,刑罚的运用对于社会以及个人产生的损害和刑罚产生的预防效果不具有可比性——显然,这涉及一套相当复杂、极富争议的评价机制[[42]]——,立法者应当放弃就相关行为赋予刑法意义:只有在有责性基础上对某一法益造成的足够严重的侵害才确然地“值得”诉诸刑罚。[[43]]
最后,补充性原则要求只能在没有其它(处罚性或非处罚性)手段可以有效保证法益免受特定形式侵害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刑罚。因此,除了具备“值得性”也即相对行为的严重性具有“比例性”,刑罚还应当是“必要的”:它只能作为最后手段(ultima ratio)而加以应用。正是在此意义上,处于刑法考量范围之外的不但包括“轻微加害”,而且还可能包括虽然具有相当的严重性——这意味着就其本身而言或许“值得”科处刑罚——但是通过运用社会政策或者相较刑事处罚更为宽缓的处罚能使社会成员不再实施的行为。
无论比例原则抑或补充性原则,都与宪法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在抽象层面和行为的严重性不成比例的刑罚对于其受众而言是难以理解的,更不会产生再教育效果:因此,比例原则在逻辑上要优先于宪法第27条第3款规定的犯罪人再教育原则。另一方面,补充性原则与宪法第13条第1款规定的原则也即人身自由的不可侵犯性有紧密的联系。应当强调的是,时至今日我国法律制度中存在的各类刑事制裁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人身自由: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各类金钱罚,在犯罪人财力不济的情形下通过转化机制(刑法典第136条以及1981年11月24日第689号法律第102条以下)可以转变成人身自由限制刑——限制自由(libertà controllata)或更替劳动(lavoro sostitutivo)——甚至监禁刑。强调人身自由的不可侵犯性意味着对这一法益所具有的极高位阶的确认,在此基础上,宪法要求立法者尽可能地限制刑罚的适用:换言之,只能在没有其它合适的手段确保对法益给予同等保护的情形下,作为剩余手段加以运用。
总而言之,在意大利法律制度中,立法者运用刑罚的合法性在于对一般预防的追求,在此过程中应当遵循犯罪人再教育原则以及针对有责性侵害的法益保护比例性、补充性原则所提出的各项限制。
四、犯罪是违法、有责、可罚的人类行为
在研究犯罪时,除了我们在上文中贯彻的总括型进路——即追问犯罪的形式概念以及想象的实质概念——,还应当补充不同的考察进路也即分析型进路:申言之,有必要区别分析每个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并依据精准的逻辑-系统顺序予以排列。[[44]]
诚然,在具体案件中,每个犯罪构成要件要素是刑罚适用性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45]]因此,基于这种纯形式性观点,犯罪的所有构成要件要素都处于同一层面。
然而,如果追问为什么某一要件要素被视为科处刑罚的前提条件——换而言之,犯罪构成中每一要件要素各自承担的功能是什么——,各项回答必然是有差异的。[[46]]
在此以盗窃罪(刑法典第624条)作为示例。一系列要件要素的功能在于客观描述一种行为事实(取得并占有一项他人所有的动产);而其它诸项要件要素决定行为是否以及何时产生违法性,也即法律对其予以否定性评价(事实上,即使存在“取得并占有”的行为,依然可能是合法的,例如一名司法工作人员为履行其职责将被罚没的动产从寓所移往国库);另一些要件要素则是表述据以判定违法行为具备有责性属性(意即能够对行为实施人给予人身性谴责)的各项条件(取得并占有财物以获利的意志;未受物理强制或生命威胁的意志状态;取得并占有财物时的认识能力和意志能力,等等);最后,还有一些要件要素(参阅刑法典第649条)反映的可能是立法者对于违法且有责之行为的可罚性(也即具体案件中科处刑罚的适当性)的各项评价(盗窃行为的被害人是配偶、父母或者子女,等等)。
根据我们在此勾勒的分析框架,犯罪——任一犯罪——都是一项违法的、有责的、可罚的人类行为。
在此意义上,犯罪由四项构成要件组成:(人类)行为(fatto [umano]);行为的违法性(antigiuridicità del fatto);违法行为的有责性(colpevolezza del fatto antigiuridico);违法且有责之行为的可罚性(punibilità del fatto antigiuridico e colpevole)。[[47]]
由于这些要件要素都依照一定的逻辑顺序前后相继,[[48]] 所以:可罚的只能是一项违法且有责的人类行为;有责的只能是一项违法的人类行为;违法的只能是一项人类行为。
显然,行为是犯罪构成的根本与基石[[49]]:通过遣用“行为”这一语词,我们指向的是各项客观要素的整体,它们共同勾勒刻画作为侵害一项或多项法益之特定形式的具体犯罪。[[50]]
有关的典型示例是诈骗罪(刑法典第640条)中规定的行为,它突出了这一犯罪是侵犯财产的特定形式。更精确而言,它刻画勾勒了诈骗罪区别于包括其它侵害财产罪在内的一切犯罪的诸项事实特征,法律就此遣用的语辞是“诡计或欺骗”,它造成“他人陷入错误”、诈骗事实的受害人完成处分行为、行为人或第三人获得“不正当利益”并且 “对他人造成损害”:诈骗罪侵害财产法益的特征——该罪的构成“行为”——正是伴随他人收益的财产损害,其归因于一项特殊的欺诈行为(也即使他人陷入错误并使之付诸处分行为的诡计或欺骗)。
构成行为的只能是一切客观要素,它们共同描述侵害法益的某种特定形式:行为(condotta),包括作为([azione],例如诈骗中的诡计或欺骗)与不作为(omissione)也即没有实施法律所要求的作为(例如,在见危不救罪中,没有通知遗弃或遗失的未满十八周岁人士所在地有权机关——参见刑法典第539条第1款);行为的前提条件(presupposti della condotta),也即必须在行为前或者行为当时存在的情形(例如,刑法典第556条规定的重婚罪要求先行存在具备民事效力的婚姻);结果(evento),也即在时间空间上与行为相分离的、由其引发的情状(例如诈骗罪之中的错误、处分行为、获益以及受损);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rapporto di causalità)(例如,诡计或欺骗应当是被害人陷入错误的原因);行为对象(oggetto materiale),也即受作为(例如,盗窃罪中的“他人动产”)、不作为(例如,刑法典第361-364条各报案不作为罪中的报案记录)抑或结果(例如,刑法典第575、579、584及589条各项杀人罪中的活人)直接影响的人或者物;犯罪行为人所具有的身份(qualità)或者法律、事实关系(relazioni giuridiche o di fatto),这反映在所谓的纯正犯(reati propri)之中,这些犯罪只能由具备特定身份(例如,刑法典第314条侵吞公款罪中公务人员的身份)的主体加以实施;对罪刑规范所保护的法益的侵害(offesa),表现为实害(也即对罪刑规范保护的事实、法律情状之完整性的全部或部分损害:例如,杀人罪中人的死亡是对生命法益的损害,刑法典第635条损坏罪中物的毁坏是对财产法益的损害)或者危险(也即产生一项损害的可能性:例如,刑法典第422条屠杀罪中对公共安全造成的危险)。
应当强调的是,并不是在每个犯罪行为中都同时出现上述要素。应当具备的要素包括一项行为,分为作为或者不作为,[[51]]以及某种侵害,分为实害或者危险[[52]]:而其它要素则只存在于某些犯罪类型中。
一般地,罪刑规范明确规定了行为的构成要素;当然,在某些场合中具有隐含的色彩,因为规范对于行为的成立条件做出的是一种默示的要求。例如,诈骗罪之中,陷入错误的当事人做出一项财产处分行为就是一种隐含要素。
在绝大部分情形下,立法者就犯罪规定的行为构成要素属于积极要素,这意味着在具体案件中行为的成立必须具备这些要素。然而,在某些情形下,对于犯罪的成立法律要求不得存在某种事实或法律情状:这种情形被称作行为的消极要素。例如,根据不少罪刑规范,特定行为产生刑事意义的前提是缺失一项源自公共机关的批准文书[[53]]:作为示例,根据2001年6月6日第380号总统法令第44条第1款b)项的规定,建筑施工行为如果“缺失建筑许可”将受到刑事处罚。另一方面,消极要素的特殊面相还反映在故意层面(这意味着对于批准的缺失事实具备有责性)和过失层面(申言之,只有当批准的缺失事实凭借必要的审慎具有可认识性的时候才能成立)。
为了确定犯罪行为的各项要素,立法者可以运用描述性概念,也可以运用规范性概念(两者的区分在刑事法律继起、[[54]] 故意以及有关非刑事法律的错误等领域具有意义)。[[55]] 如果立法者使用的语辞在描述的同时指向的是可以通过感知或经验予以确证的、物理现实或心理现实的对象,那么这些构成描述性概念:例如,对于性暴力罪(刑法典第609 bis条)中的行为,通过“付诸或承受性行为”这一表述予以部分的描述;在杀人罪中,结果的描述环节运用的是“死亡”一词,而“人”一词则是对行为对象的限定。如果立法者为明确某一犯罪要素时援用的概念指向的是一项或多项法律、非法律规范,那么这时形成的是规范性要素:由此引致的结论是,这类犯罪要素只能在所涉规范的逻辑前提下加以理解。例如,在大部分侵犯财产犯罪中,行为对象应当是“他人的”动产或不动产,也即所有权主体不同于犯罪行为实施人。
犯罪的第二项要件——违法性——反映的是行为与法律制度整体的对立性[[56]]:如果一项规范,无论其属于哪一法律部门(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以及宪法等),赋予实现行为的权利或者使之成为义务时,便不存在这一“与法律的(客观)冲突”。[[57]]
在此环节,学理一般遣用正当化事由一词,用以指称基于允许或要求实施具有刑事意义之行为的规范所产生的各项权利与义务之整体。
作为示例,刑法典第52条明确规定,在行使正当防卫权利的情形下可以实施一项具有刑事意义的行为:换言之,因为其“有必要捍 卫自己或他人的权利免受一项不当侵害的现实危险,当然,防卫应当与侵害成比例”。刑事诉讼法典规定,证人在回答向他提出的问题时应当如实陈述(刑诉法典第198条):由此可能导致的情形是,该证人陈述的事实有损他人名誉,进而符合诽谤罪(刑法典第595条)的构成行为。宪法赋予所有人自由表达其思想的权利(宪法典第21条):在行使该权利时,同样可能发生的情形是,行为人做出有损他人名誉的判断或事实陈述,从而构成诽谤的行为。
如果不存在任何正当化事由,那么行为就呈现违法性,在具备其它犯罪构成要件(有责性与可罚性)的情形下将构成犯罪。相反地,如果存在一项正当化事由,违法性这一要件便呈现瑕疵,进而意味着行为是合法的,自然也是不可罚的:这一合法性覆盖一切法律部门,因此不受任何种类的处罚(民事、行政等等)。在此意义上,学理层面表述为正当化事由的“一般效力” 。[[58]]
在早期、粗疏的刑法制度中,实施一项呈现违法性的行为——也即法律没有许可、没有要求的对某一法益产生侵害的特定形式——便足以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人本身被类同为其它各种因果要素,行为人个体承受处罚的理由仅在于客观地造成了行为事实的发生。
然而,现代刑法已进入了文明的新境域,在此图景下行为人个体与他实施的违法性行为之间的关系内涵更为丰富和复杂:事实上,在查证一项违法性行为存在的基础上,刑法要求犯罪构成层面还应当符合进一步的要件,也即行为人的有责性(colpevolezza)。[[59]]
通过这一表述,我们意在指称就实施某一非法行为对行为人予以谴责所凭借的一系列标准之总体。[[60]] 在现行法制之下,基于违法性行为的实施做出“人身性”谴责并区别其程度的标准包括如下各项:故意(dolo)或过失(colpa);免责事由(scusante)的缺失,也即行为实施时各项伴随情状的正常性;对违反的刑法规范的认识或可认识性;认识能力和意志能力(capacità di intendere e di volere)。[[61]]
立法者对上述部分标准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与此同时,立法者还针对有责性原则的各项要求设计了广泛的例外情形(客观责任[responsabilità oggettiva]、对刑法的认识错误无意义、不可归罪者[non imputabile]之责任);[[62]]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在此领域,宪法法院根据刑事责任人身性这一宪法原则——这在今日几乎已成为有责性原则的同义词——已经废除了其中部分例外情形。[[63]]
故意(dolo)是对违法性行为诸项要素的认识与意志。[[64]] 过失(colpa)则存在于疏忽、不谨慎、不专业或者对预防性法律规范的不遵守之中,它指向违法性行为的所有要素。[[65]]
另一方面,如上文所述,有责性还要求具备进一步的其它结构性要素。首先,行为主体实施行为之时应当不具备免责事由(assenza di scusanti):申言之,要求的是行为当时不存在异常情状,后者在立法评价角度而言是能够以不可抗拒的方式影响行为人的意志或心理能力、进而决定了不可能期待其付诸和实际做出之行为不同的其它行为的情形。[[66]]例如,如果某人故意实施虚假证言、虚假鉴定或翻译以及人身包庇等行为是“出于被迫以求自保或者保护近亲属免受对自由或名誉的严重且不可避免之危害”(刑法典第384条第1款),那么就不应当予以有责性评价,也即“不得予以惩处”。
在此基础上,还要求具备对违反的刑法规范的认识或可认识性:申言之,行为人应当知道,或者至少通过借助必要的谨慎能够知道他实施的故意或过失的违法性行为是为一项罪刑规范所禁止的(参见刑法典第5条,宪法法院通过1988年第364号判决对其予以重述 )。[[67]]例如,某人在无知中实施了一项为罪刑规范所禁止的行为,因为他收到了来自负责监督规范遵守的有权行政机关关于该行为不具有刑事意义的“错误保证”,或者对于同一行为行为人先前已多次获得各种无罪处遇因而认为其不具刑事意义,又或者“行为人社会化的非有责性缺失”(例如移民入境不久,不知晓流动商贩方面的意大利法律规定),宪法法院认为上述诸多情形下行为人并不具备有责性。
最后,如果某人在行为当时不具备可归罪性(刑法典第85条),那么就不存在有责性,因而不应当受到处罚:可归罪的主体必须具备“认识”能力也即知晓自身行为之意义的能力,以及“意志”能力也即遏制或激发自身冲动的能力。[[68]]
一旦查证确实存在一项违法的、有责的行为,我们已经相当接近于结论性宣告:该行为构成犯罪。当然,并不意味着这一结论已然成立。在我国法律制度中,对于刑罚的适用持“有保留”的立场:换言之,只有在具备一系列进一步的条件时,才能予以应用。这些条件如果缺失,刑罚不具有可应用性,进而意味着行为不构成犯罪。
从犯罪构成角度看,在此环节涉及的是最后一项构成要件:违法、有责之行为的可罚性。[[69]]在此范畴内部囊括的各项条件整体,相对于违法、有责之行为具有递进性和外部性,能支持或排除处罚的适当性。[[70]]
在犯罪构成层面要求具备可罚性的基础逻辑可做如下理解:在违法且有责行为和有关处罚之间存在——或者,更好地,可以存在——一定的空间以容纳评价实际处罚之适当性的深层次刑事政策选择,立法者可以直接行使这一选择权,也可以通过授权法官实现该权力的间接行使。
立法者对于处罚违法、有责行为之适当性的选择可以反映为对下列两类条件的评价:
a) 支持可罚性的条件;
b) 排除可罚性的条件(或事由)。
有关支持可罚性的条件,立法者的制度设计反映为“可罚性客观条件(condizioni obiettive di punibilità)”(刑法典第44条)。这里所涉及的各种情状为一项罪刑规范所规定,它们并不以某种方式描述对于受规范保护之法益的侵害,而只是表达对科处刑罚适当性的评价:例如,非法持有改装钥匙或撬锁工具罪(刑法典第707条)中的当场捕获,以及虚假破产罪(破产法第216、217条)中的破产宣告。
排除可罚性——因此其整体可称为“排除可罚性事由”或者“不可罚事由”[[71]]——的情形包括:a)某些与行为实施同步的情况,它们关乎行为人的人身地位或者与被害人的关系(人身性不可罚事由):例如,在大部分侵犯财产罪中,损害其家人的行为人的不可罚性(刑法典第649条);b)违法、有责行为实施后行为人的某些行为(继起不可罚事由或可罚性灭除事由):例如,虚假宣誓罪(刑法典第371条)以及虚假证言、专家鉴证或翻译罪(刑法典第372、373以及376条)中的撤回;c)违法、有责行为实施后发生的某些自然事实或法律事实,它们或者完全独立于行为人的行为,或者不尽止于行为人的某一行为(犯罪灭失事由):例如,有罪判决之前行为人的死亡事实(刑法典第150条),犯罪已过追诉时效(刑法典第157条)以及纯正赦免(宪法典第79条和刑法典第151条)等。[[72]]
如前文所述,有时立法者赋予法官评价实际惩处某项违法且有责行为实施人的适当性的任务。作为示例,试想以替代刑(也即拘役或刑事罚款)惩处的诸多轻罪(contravvenzioni)中存在的金赎制度(oblazione):在此场合中,请求及时缴付某种犯罪最高法定刑事罚款金额50%之款项的轻罪行为人的可罚性由法官基于行为严重性付诸自由裁量(刑法典第162 bis条)。
犯罪诸项要素按照四要件系统顺序——也即第一序位之行为,第二序位之行为违法性,第三序位之违法行为有责性,第四序位之违法有责行为可罚性——予以排列,其反映的逻辑顺序具有规范性基础(刑事诉讼法典第129条):约束法官裁判活动、满足公民利益诉求以及反映(刑事)律师业务流程。
特别地,如果没有任何刑事层面应当予以评价的行为,法官不能以存在一项正当化事由作为理由排除刑事责任;同样地,不预先查实存在一项不可宽赦的故意或过失违法行为,不得主张缺失认识能力或意志能力而排除刑事责任;最后,不预先查明一项违法且有责之行为的存在,不得基于缺失一项可罚性客观条件或者存在一项排除可罚性事由而判定被告人无罪。
这一叙说方式同样适用于存在犯罪灭失事由的场合:从逻辑和法律角度而言,诉讼文书显示的行为不存在、被告人没有实施行为、行为不具有违法性或者行为违法但不具备有责性等情形应当先于犯罪灭失事由而导致判处被告人无罪。
作为示例:首先需要查证是否存在非法拘禁罪(刑法典第605条)意义上的剥夺人身自由之行为;只有在切实确认其存在的基础上,才有意义追问这一剥夺人身自由之行为构成某项合法权利的行使(例如,私人根据刑事诉讼法典第383条实施逮捕)抑或某项特别义务的履行(例如,司法警察根据刑事诉讼法典第380条实施现场强制逮捕);只有在已排除存在任何正当化事由的情形下,才可以进入下一环节追问不正当剥夺人身自由之行为是否由未受强制、有认识和意志能力之主体有意付诸实施;最后,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应当着手查证上述不正当且有责的拘禁行为是否因为诸如犯罪追诉时效期限已过等事由而丧失可罚性。
综上所述,四要件系统理论有助于保证理论分析与司法实践的完整性、合理性以及可查验性:在确证刑事责任过程中不忽视具有法律意义的每一方面;排列诸项犯罪构成要件时遵循的继起顺序反映了法律规范的逻辑脉络,其中容纳的只限于和每项要件密切相关的各个问题;从反面而言,也能容易地检验和质疑不正确或者不相关的各种问题。
五、犯罪的二要件、三要件以及四要件模式:争议问题
四要件理论并不是当代意大利学理中唯一的犯罪分析模式。[[73]]事实上,在该领域内,通过一定程度的简化后,可以认为与四要件理论平行共存的还有其它两种模式:一种是二要件模式,[[74]]它将犯罪构成切分为“客观要件”与“主观要件”;另一种是三要件模式,它将犯罪构成切分为“典型行为”、“违法性”以及“有责性”三项要件。[[75]]
上述各种模式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呈现“客观主义”的特质,申言之,它们都要求解释者从查实行为本身入手,只是在后续环节才进一步考察行为人是否基于故意或过失行事、是否具有可归罪性等要素以最终确定刑事责任。[[76]]
事实上,分析犯罪过程中秉持的客观主义进路是由我国法律制度中犯罪的实际面相所决定的。立法者将行为而不是行为人置于犯罪构成的中心:在意大利立法中,犯罪首先是对一项或多项法益的侵害。原则上,有关犯罪的这一理念既反映在1889年刑法典之中,也体现于1930年刑法典之中,[[77]]它在现行宪法体制下依然不应当被抛弃或成为例外:确然地,如我们所见,意大利宪法所勾勒的犯罪模型的核心在于行为——也即在于对一项或多项法益的侵害——,而有责性在逻辑层面扮演的角色则呈现后继的属性,其旨在后续地界定能够基于行为谴责其行为人的各项条件。
然而,在这一共同前提的基础上,对于某些进一步的问题,学理层面有着一定的分歧。
首当其冲的争议在于是否应当赋予违法性以独立的犯罪构成要件的角色——事实上,这正是三要件理论[[78]]以及四要件理论[[79]]给出的方案——,抑或正当化事由应当被归于典型行为这一范畴内部作为其消极构成要素,也即为了成就具有刑事意义的行为必须缺失的诸项要素。[[80]]
我们主张,在意大利现行法律框架下引入正当化事由作为行为消极要素的理论,一方面显得多余,另一方面——这一点更为重要——则可能导致与现行法律相冲突的后果。 [[81]]
之所以认为其多余,是因为历史上该理念初创于德国,其本意在于弥合该国法律制度所特有的缺漏:对于错误地认为存在正当化事由的情形,缺乏一项排除故意的规范。只有将其视为行为的消极构成要素,各项正当化事由才可能被纳入到德国刑法典有关错误的唯一的规范之中,该条文规定行为人陷于事实错误时排除故意。相反地,在意大利刑法典之中,不但有规定事实错误排除故意的条文,而且第59条第4款明确规定错误认为存在正当化事由时,故意同样应当予以排除。
更为重要的是,正当化事由作为行为消极构成要素的理论与意大利实在法规范并不相容。特别地,有关故意的制度设计要求行为人对于行为诸项要素都具有相应的认识:不仅如此,在行为人开始实施典型行为之时,这一认识应当达到实际认识的高度。正如上述理论创始人之一弗兰克(Frank)在其著作中写道,故意不但要求“对于存在各项积极要素具有认识”,而且还要求“对于缺失各项消极要素具有认识”:作为示例,由此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对于人身伤害故意的成立,行为人不仅应当认识到造成了一项导致生理或心理疾病的伤害,而且应当认识到行为当时不存在正当防卫、权利人同意以及其它授权或要求造成该伤害的各类权利、义务事由。然而,如此宽泛的故意认识内容在心理层面是难以想象的,而且现行法律在此并未做这样的要求(刑法典第43条第1款、第47条以及第59条第4款)。[[82]]
另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涉及可罚性,就此讨论的焦点是它应当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之一,[[83]]还是属于刑法学之中更进一步的不同篇章。[[84]]换而言之,其追问的是:犯罪这一称谓只能指向违法、有责且可罚的行为(根据四要件理论模型),抑或满足前三项构成要件即足以构成犯罪,只是某项违法且有责行为的实施主体是否应受刑罚还需要借助进一步的独立判断,而后者正是以可罚性为其考察对象。
我们赞同前一种主张的理由在于,刑罚是使刑法区别于其它任何法律部门的关键所在,也是使犯罪区别于其它不法类型的关键所在:因此,正是犯罪的固有面相要求将可罚性视为犯罪构成要件之一。抽象意义上的犯罪经由刑罚的法定科处方能得以确定:同样地,只有在成立一项违法、有责且可罚的行为之时才能具体地谈及某种犯罪。
注释:
[[1]] 关于某些争议情形,参见E. Dolcini (aggiornato da A. Della Bella), sub art. 17, in Commentario breve al Codice penale, a cura di A. Crespi, G. Forti e G. Zuccalà, V ed., Padova, Cedam, 2008, p. 67 ss。
[[2]] 以下简称刑法典。
[[3]]关于这一点,参阅G. Marinucci, Relazione di sintesi, in Societas puniri potest. La responsabilità da reato degli enti collettivi, a cura di F. Palazzo, Padova, Cedam, 2003, p. 307 ss.; G. Marinucci, E. Dolcini, Manuale di diritto penale. Parte generale, IV ed., Milano, Giuffrè, 2012, p. 700 ss。此外,应当强调的是,最近意大利最高法院统一部通过2014年4月24日Espenhahn案第38343号判决,明确指出2001年第231号法令规定的“基于犯罪的单位责任(responsabilità da reato degli enti)”既不是刑事责任类型,也不是行政责任类型,而是属于“第三类责任(tertium genus di responsabilità)”。
[[4]] 对此参见G. Stratenwerth, Strafrecht, A.T., IV ed., Köln, Heymann, 2000, p. 31 ss。
[[5]] 参见H. Zipf, Politica criminale, trad. it., Giuffrè, Milano, 1989, p. 145。
[[6]] 参见R. Garofalo, Criminologia, Studio sul delitto e sulla teoria della repressione, II ed., Torino, Bocca, 1891, p. 36。
[[7]] 参见K. Lüderssen, Introduzione a Seminar: Abweichendes Verhalten, II, Bd. 1,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4, p. 7。
[[8]] 参见F. Grispigni, Introduzione alla sociologia criminale, Torino, Utet, 1928, p. 121 s。
[[9]] 有关越轨理论的各种批判性见解,参见F. Mantovani, Diritto penale. Parte generale, VIII ed., Padova, Cedam, 2013, p. 611 ss。
[[10]] 参见V. Manzini, Trattato di diritto penale italiano, V ed., Torino, Utet, 1981, I, p. 38。
[[11]] 参见H. Welzel, Studien zum System des Strafrechts, 1939, 现即Abhandlungen zum Strafrecht und zur Rechtsphilosophie, Berlin-New York, De Gruyter, 1975, p. 138-9, nt. 30。
[[12]] 参见H. Mannheim, Trattato di criminologia comparata, vol. I, trad. it., Torino, Einaudi, 1975, p. 66。
[[13]] 参见S. Vinciguerra, Diritto penale italiano, vol. I, II ed., Padova, Cedam, 2009, p. 282。
[[14]] 参见V. Manzini, Trattato, cit., I, p. 39。
[[15]] 参见N. Luhmann, Sociologia del diritto, trad.it., Bari, Laterza, 1977。
[[16]] 参见G. Jakobs, Strafrecht, A.T., II ed., Berlin, De Gruyter, 1993, p. 13 ss。
[[17]] 参见A. Febbrajo, Prefazione a N. Luhmann, Sociologia del diritto, cit., p. XXXIX。
[[18]] 参见W. Hassemer, Einführung in die Grundlagen des Strafrechts, II ed., München, Beck, 1990, p. 326。
[[19]] 参见K. Amelung, Rechtsgüterschutz und Schutz der Gesellschaft, Athenäum, Frankfurt, 1972, p. 361。
[[20]] 参见N. Levi, Dolo e coscienza dell'illiceità nel diritto vigente e nel Progetto, in Annali dell’Università di Cagliari, 1928, p. 56 e p. 65。
[[21]] 参见A. Baratta, La teoria della prevenzione integrazione, in Dei delitti e delle pene, 1984, p. 5 ss。
[[22]] 参见G. Stratenwerth, Strafrecht, cit., p. 32 s。
[[23]] 参见C. Pedrazzi, voce Diritto penale, in D. disc. pen., IV, 1990, p. 67。
[[24]] 参见C. Fiore e S. Fiore, Diritto penale. Parte generale, IV ed., Torino, Utet, 2013, p. 9; G. Marinucci, Politica criminale e riforma del diritto penale, in G. Marinucci e E. Dolcini, Studi di diritto penale, Milano, Giuffrè, 1991, p. 73; E. Musco, Consenso e legislazione penale, in Riv. it. dir. proc. pen., 1993, p. 81。
[[25]] 参见E. Dolcini, La "rieducazione del condannato" tra mito e realtà, in G. Marinucci e E. Dolcini, Studi di diritto penale, cit., p. 135 ss。
[[26]] 晚近对此较完备的阐述可参见G. de Vero, L’incerto percorso e le prospettive di approdo dell’idea di prevenzione generale positiva, in Riv. it. dir. proc. pen., 2002, p. 439 ss。
[[27]] 参见V. Manzini, Trattato, cit., I, p. 43; N. Levi, Dolo e coscienza dell'illiceità, cit., p. 58。
[[28]] 参见J. Andenaes, Punishment and Deterrenc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4, p. 110 ss.; E. Dolcini, La commisurazione della pena, Padova, Cedam, 1979, p. 226 s.; 教科书层面可以参阅C. Fiore e S. Fiore, Diritto penale, cit., p. 10, 以及G. de Vero, Corso di diritto penale, I, II ed., Torino, Giappichelli, 2012, p. 26 s. e p. 187 ss。
[[29]] 参见G. Marinucci, Politica criminale, cit., p. 73。
[[30]] 参见C. Pedrazzi,voce Diritto penale, cit., p. 67。
[[31]] 类似见解亦可参见 T. Padovani, Diritto penale. Parte generale, X ed., Milano, Giuffrè, 2012, p. 78 s。
[[32]] 有关国家类型和刑罚的功能的关系,参见E. Dolcini, La commisurazione, cit., p. 131 ss. e p. 170 ss.; 有关国家类型与犯罪构成, G. Marinucci e E. Dolcini, Corso di diritto penale, III ed., Milano, Giuffrè, 2001, p. 429 ss。
[[33]] 参见F. Bricola, voce Teoria generale del reato, in Nss. D.I., XIV, 1974, p. 83; G. Marinucci e E. Dolcini, Corso, cit., p. 451 ss.; E. Musco, Bene giuridico e tutela dell’onore, Milano, Giuffrè, 1974, p. 116 ss。
[[34]] 参见G. Marinucci e E. Dolcini, Manuale, cit., p. 9 s。
[[35]] 参见G. Marinucci e E. Dolcini, Corso, cit., p. 429 ss。
[[36]] 有关晚近的文献著述,参见V. Manes, Il principio di offensività nel diritto penale. Canone di politica criminale, criterio ermeneutico, parametro di ragionevolezza, Torino, Giappichelli, 2005; C. F. Grosso, Su alcuni problemi generali di diritto penale, in Studi in onore di Marcello Gallo. Scritti degli allievi, Torino, Giappichelli, 2004, p. 23 ss.; G.Neppi Modona, Il lungo cammino del principio di offensività, in Studi in onore di Marcello Gallo. Scritti degli allievi, Torino, Giappichelli, 2004, p. 89 ss。
[[37]] 相关宪法法院判例参见Corte cost. 24 luglio 1995 n. 360, in Giur. cost., 1995, p. 2668; conf. Corte cost. 11 luglio 2000 n. 263, ivi, 2000, p. 2064 ss.; Corte cost. 21 novembre 2000 n. 519, ivi, 2000, p. 4069 ss.; Corte cost. 7 luglio 2005 n. 265, ivi, 2005, p. 2432 s。
[[38]] 参见E. Musco, Bene giuridico e tutela dell’onore, Milano, Giuffrè, 1974, p. 116 ss.; 此外,G. Marinucci e E. Dolcini, Corso, cit., p. 449 ss以及其注释[1]援引的各项文献; 当然,也有意见主张将侵害性原则降为单纯的刑事政策指导标准,参见F. Palazzo, Corso di diritto penale. Parte generale, Torino, Giappichelli, 2013, p. 78。
[[39]] 参见Corte cost. 24 marzo 1988 n. 364, in Riv. it. dir. proc. pen., 1988, p. 686 ss以及Corte cost. 13 dicembre 1988 n. 1085, ivi, 1990, p. 289 ss.; 学理上,有关有责性原则的宪法意义,参见:针对早期宪法判例,A. Alessandri, Commentario della Costituzione, a cura di G. Branca e A. Pizzorusso, tomo IV, sub art. 27, 1° co., Bologna – Roma, Zanichelli – Foro italiano, 1989, p. 68 ss.; 在教科书层面,M. Donini, Il principio di colpevolezza, in A. Cadoppi, M. Donini, G. Fornasari, A. Gamberini, G. Insolera, N. Mazzacuva, M. Pavarini, I. Rosoni, L. Stortoni, A. Valenti e M. Zanotti, Introduzione al sistema penale, vol. I, a cura di G. Insolera, N. Mazzacuva, M. Pavarini e M. Zanotti, IV ed., Torino, Giappichelli, 2012, p. 291 ss。
[[40]] 一般地,在意大利文献中,关于有责性和刑罚预防功能的关系,参见:D. Pulitanò, L’errore di diritto nella teoria del reato, Milano, Giuffrè, 1976, p. 93 ss.; D. Pulitanò, Politica criminale, in Diritto penale in trasformazione, a cura di G. Marinucci e E. Dolcini, Milano, Giuffrè, 1985, p. 39 ss.; G. Fiandaca, Considerazioni su colpevolezza e prevenzione, in Riv. it. dir. proc. pen., 1987, p. 840 ss.; R. Bartoli, Colpevolezza: tra personalismo e prevenzione, Torino, Giappichelli, 2005, p. 28 ss (以及其中援引的丰富的著述)。
[[41]] 在此文献丰富,言辞表述略有不同: F. Angioni, Contenuto e funzioni del concetto di bene giuridico, Milano, Giuffrè, 1983, p. 163 ss.; G. de Vero, Corso di diritto penale, I, cit., p. 50 s.; E. Dolcini, Sanzione penale o sanzione amministrativa: problemi di scienza della legislazione, in Diritto penale in trasformazione, a cura di G. Marinucci e E. Dolcini, cit., p. 386 ss.; G. Fiandaca e E. Musco, Diritto penale. Parte generale, VII ed., Bologna, Zanichelli, 2014, p. 29 ss.; T. Padovani, Diritto penale, cit., p. 86 s.; F. Palazzo, I criteri di riparto tra sanzioni penali e sanzioni amministrative, in Indice pen., 1986, p. 36 ss.; C. E. Paliero, Il principio di effettività del diritto penale, in Riv. it. dir. proc. pen., 1990, p. 449 ss.; C. Pedrazzi, voce Diritto penale, cit., p. 68 s.; M. Romano, «Meritevolezza di pena», «bisogno di pena» e teoria del reato, in Riv. it. dir. proc. pen., 1992, p. 39 ss.; A. Vallini, Antiche e nuove tensioni tra colpevolezza e diritto penale artificiale, Torino, Giappichelli, 2003, p. 163 ss。
[[42]] 参见F. Palazzo, Introduzione ai principi del diritto penale, Torino, Giappichelli, 1999, p. 72。
[[43]] 参见F. Palazzo, Introduzione ai principi del diritto penale, Torino, Giappichelli, 1999, p. 72,这里他指出在罪刑规范内容层面产生影响的诸多保障性原则中存在“一项有关比例性的实质需求”。
[[44]] 其中有一种可以溯源于20世纪30年代之德国的理论见解,认为任何对犯罪的分析性解构都是有失偏颇的,参见G. Marinucci e E. Dolcini, Corso, cit., p. 618 s.。
[[45]] 参见E. Beling, Die Lehre vom Verbrechen, 1906, rist. 1964, p. 74。
[[46]] 参见E. Beling, Die Lehre, p. 77 s.; E. Schwinge e R. Zimmerl, Wesensschau und konkretes Ordnungsdenken im Strafrecht, p. 33。
[[47]] 参见G. Marinucci e E. Dolcini, Corso cit., p. 625 ss.; G. Marinucci e E. Dolcini, Manuale di diritto penale, cit., p. 171。
[[48]] 在此意义上,有关犯罪的二要件、三要件以及四要件学说,理论上称之为“层进式”犯罪理论:参见M. Romano, Commentario sistematico del Codice penale, I, III ed., Milano, Giuffrè, 2004 pre-art. 39, p. 311。
[[49]] 参见E. Beling, Die Lehre vom Verbrechen, cit., p. 77。
[[50]] 在此意义上,参见G. Delitala, Il ‘fatto’, p. 85 s., 以及 C. Pedrazzi, Il concorso di persone nel reato, p. 32 e G. Marinucci, Fatto e scriminanti, cit., p. 194 s.; 此外,也有学理主张不同的行为概念,其包含产生刑事法律后果所必需的一切客观、主观要素:参见A. Pagliaro, Il fatto di reato, Palermo, Priulla, 1960; Id., voce Fatto (dir. pen.), in Enc. dir., XVI, 1967, p. 950 ss.; Id., Principi di diritto penale. Parte generale, Milano, Giuffrè, VIII ed., 2003, p. 251 ss.; 有关刑法中行为概念的起源与演进,参见A. Gargani, Dal corpus delicti al Tatbestand, Le origini della tipicità penale, Milano, Giuffrè, 1997。
[[51]] 有关不因思想科刑(cogitationis poenam nemo patitur)原则以及“怀疑犯(reati di sospetto)”问题,参见G. Marinucci, Il reato come azione, Milano, Giuffrè, 1971, p. 167 ss,以及更为晚近的,R. Calisti, Il sospetto di reati, Profili costituzionali e prospettive attuali, Milano, Giuffrè, 2003; 学理上也称为“刑法的物质性原则(principio di materialità del diritto penale)”:参见A. Cadoppi e P. Veneziani, Elementi di diritto penale. Parte generale, V ed., Padova, Cedam, 2012, p. 87 s.; G. de Vero, Corso di diritto penale, I, cit., p. 115 ss.; F. Mantovani, Diritto penale, cit., p. 123 ss.; A. Valenti, Principi di materialità ed offensività, in A. Cadoppi e altri, Introduzione al sistema penale, cit., p. 354 ss.; 谈论“无行为无犯罪(nullum crimen sine actione)”原则的学理则参见F. Palazzo, Corso, cit., p. 217 ss。
[[52]] 有关无侵害犯罪(reati senza offesa),以及绝大部分此类犯罪依据侵害性这一宪法原则予以重构的事实,参见G. Marinucci e E. Dolcini, Corso, cit., p. 559 ss。
[[53]] 参见M. Mantovani, L’esercizio di un’attività non autorizzata. Profili penali, Torino, Giappichelli, 2003。
[[54]] 参见G.L. Gatta, Abolitio criminis e successione di norme “integratrici”: teoria e prassi, Milano, Giuffè, 2008, pp. 236 ss。
[[55]] 关于行为规范要素之结构,在教科书层面,参见M. Gallo, Appunti di diritto penale, vol. II, Il reato, parte I, La fattispecie oggettiva, Torino, Giappichelli, 2007, p. 141 ss;关于描述性要素、规范性要素以及宪法第25条第2款规定的精确性原则,参见G. Marinucci e E. Dolcini, Corso, cit., p. 131 ss;对于规范性要素援引的诸项规范之间的时间继起,晚近的详尽阐析请参见L. Risicato, Gli elementi normativi della fattispecie penale, Milano, Giuffrè, 2004。
[[56]] 参见G. Marinucci, voce Antigiuridicità, in D. disc. pen., I, 1987, p. 172 ss以及记载的众多文献。
[[57]] 参见M. Romano, Commentario, I, cit., pre-art. 39, p. 319。
[[58]] 参见G. Marinucci e E. Dolcini, Manuale di dir. pen., cit., p. 237。
[[59]] 关于有责性原则反映法律文明进化程度的主张,参见E. Beling, Unschuld, Schuld und Schuldstufen im Vorentwurf zu einem Deutschen Strafgesetzbuch, 1910, rist. Aalen, Scientia, 1971, p. 15, 以及G. Bettiol, Diritto penale. Parte generale, XI ed., Padova, Cedam, 1982, p. 376 s。
[[60]] 关于有责性“内容”不同学理主张的批判性考察,参见R. Bartoli, Colpevolezza: tra personalismo e prevenzione, cit., p. 47 ss。
[[61]] 参见G. Marinucci e E. Dolcini, Corso, cit., p. 643;关于不同的理论建构,参见de Vero, Corso di diritto penale, I, cit., p. 174 ss。
[[62]] G. Marinucci e E. Dolcini, Corso, cit., p. 470 ss。
[[63]] G. Marinucci e E. Dolcini, Corso, cit., p. 470 ss。
[[64]] 参见G. Marinucci e E. Dolcini, Manuale di diritto penale, cit., p. 291 ss。
[[65]] 参见G. Marinucci e E. Dolcini, Manuale di diritto penale, cit., p. 313 ss。
[[66]] 参见L. Scarano, La non esigibilità nel diritto penale, Napoli, Humus, 1948; T. Padovani, Appunti sull'evoluzione del concetto di colpevolezza, in Riv. it. dir. proc. pen., 1973, p. 554 ss.;E. Dolcini, La commisurazione della pena, cit., p. 268 ss;H. Achenbach, Riflessioni storico-dogmatiche sulla concezione della colpevolezza di Reinhard Frank, in Riv. it. dir. proc. pen., 1981, p. 838 ss;G. Fornasari, Il principio di inesigibilità nel diritto penale, Padova, Cedam, 1990;P. Veneziani, Motivi e colpevolezza, Torino, Giappichelli, 2000, p. 267 ss;F. Viganò, Stato di necessità e conflitto di doveri, Milano, Giuffrè, 2000, p. 151 ss以及p. 245 ss;E. Venafro, Scusanti, Torino, Giappichelli, 2002。最后,在教科书层面,参见G. Marinucci e E. Dolcini, Manuale di diritto penale, cit., p. 348。
[[67]] 参见F. Palazzo, L'errore sulla legge extrapenale, Milano, Giuffrè, 1974;D. Pulitanò, voce Ignoranza (dir. pen.), in Enc. dir., XX, 1970, p. 33 ss;Id., L'errore di diritto nella teoria del reato, Milano, Giuffrè, 1976。
[[68]] 参见 M. Bertolino, L'imputabilità e il vizio di mente nel sistema penale, Milano, Giuffrè, 1990, 尤其是p. 505 ss;关于意大利立法以及司法判例中可归罪性的问题,参见A. Manna, L’imputabilità e i nuovi modelli di sanzione, Torino, Giappichelli, 1997, p. 9 ss。
[[69]] 关于可罚性系统定位的争议,详见下文第五部分。
[[70]] 参见G. Marinucci e E. Dolcini, Corso di diritto penale, cit., p. 652 ss。
[[71]] 参见G. Vassalli, voce Cause di non punibilità, in Enc. dir., VI, 1960, p. 618 ss。
[[72]] 参见M. G. Gallisai Pilo, Estinzione del reato e della pena (dir. pen.), in Nss. dig. it., App., vol. III, 1982, p. 551 ss;L. Stortoni, Estinzione del reato e della pena, in Dig. pen., IV, 1990, p. 342 ss;E. Antonini, Contributo alla dommatica delle cause di estinzione del reato e della pena, Milano, Giuffrè, 1990。
[[73]] 关于八十年代初期的情况,参见R. Riz, La teoria generale del reato nella dottrina italiana. Considerazioni sulla tripartizione, in Indice pen., 1981, p. 607 ss.;有关晚近以来对不同模式的批判性评价,参见A. Cadoppi e P. Veneziani, Elementi, cit., p. 167 ss。
[[74]] 在此意义上,参见F. Antolisei, Manuale di diritto penale. Parte generale, XVI ed., Milano, Giuffré, 2003, p. 214 ss.;A. Fiorella, voce Reato, in Enc. dir., XXXVIII, 1987, p. 782 ss.;M. Gallo, Appunti di diritto penale, II, pt. I, cit., p. 47 ss.;F. Mantovani, Diritto penale, cit., p. 105 s.;V. Manzini, Trattato di diritto penale, I, cit., p. 607 ss。
[[75]] 参见Delitala, Il “fatto” nella teoria generale del reato, Padova, Cedam, 1930, ora in G. Delitala, Diritto penale. Raccolta degli scritti, Milano, Giuffrè, 1976, p. 3 ss。在此意义上,G. Bettiol, Diritto penale, cit., p. 210 ss;A. Cadoppi e P. Veneziani, Elementi, cit., p. 170 ss;G. Fiandaca e E. Musco, Diritto penale, cit., p. 188 ss;T. Padovani, Diritto penale, cit., p. 103 ss;F. Palazzo, Corso, cit., p. 206 ss.;M. Romano, Commentario, I, cit., pre-art. 39, p. 308 ss.;G. Vassalli, Il fatto negli elementi del reato, in Riv. it. proc. pen., 1984, p. 529 ss。
[[76]] 有关犯罪分析中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参见G. Marinucci e E. Dolcini, Corso, cit., p. 619 ss以及晚近的G. Marinucci, Soggettivismo e oggettivismo nel diritto penale. Uno schizzo dogmatico e politico-criminale, in Riv. it. dir. proc. pen., 2011, pp. 1 ss。
[[77]] 参见G. Marinucci e E. Dolcini, Corso, cit., p. 525 ss。
[[78]] 参见D. Pulitanò, Diritto penale, IV ed., Torino, Giappichelli, p. 64 s;G. Fiandaca e E. Musco, Diritto penale, cit., p. 190 ss;F. Palazzo, Corso, cit., p. 206 ss;M. Romano, Commentario, I, cit., pre-art. 39, p. 309 s。
[[79]] 参见G. Marinucci, Fatto e scriminanti. Note dommatiche e politico-criminali, in Diritto penale in trasformazione, a cura di G. Marinucci e E. Dolcini, cit., p. 177 ss。
[[80]] 这一理论主张——可上溯至R. Frank, Über den Aufbau des Schuldbegriffs, in Festschrift der Juristischen Fakultät der Universität Giessen, Giessen, 1907, p. 535——的赞同者包括I. Caraccioli, Manuale di diritto penale. Parte generale, II ed., Padova, Cedam, 2004, p. 381 ss;M. Gallo, Appunti di diritto penale, II, pt. I, cit.,p. 179 ss;P. Nuvolone, Il sistema del diritto penale, Padova, Cedam, 1975, p. 103 ss;A. Pagliaro, Principi di diritto penale, cit., p. 425 ss;F. Mantovani, Diritto penale, cit., p. 241 s。
[[81]] 参见G. Marinucci, Fatto e scriminanti, cit., p. 188s,以及记载的基本文献。
[[82]] 参见F. Palazzo, Corso, cit., p. 304 s。
[[83]] 参见G. Battaglini, Diritto penale. Parte generale, III ed., Padova, Cedam, 1949, p. 275 ss;G. Marinucci e E. Dolcini, Corso, cit., p. 651 ss.; G. Marinucci e E. Dolcini, Manuale, cit., p. 177 ss.; 这一主张——可溯源于E. Beling, Die Lehre vom Verbrechen, 1906, rist. Aalen, Scientia, 1964, p. 51 ss——在晚近德国刑法教科书层面的拥蹇者包括W. Hassemer, Einführung in die Gründlagen des Strafrecht, II ed., München, Beck, 1990, p. 243 ss以及H.H. Jescheck-T. Weigend, Lehrbuch des Strafrechts, A.T., Berlin, Duncker und Humblot, V ed., 1996, p. 551 ss。
[[84]] 参见:M. Gallo, Appunti di diritto penale, II, pt. I, cit., p. 47, 根据其见解,主张可罚性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论者“在决定型犯罪构成中却输入了作为被决定之结果的诸项要素”;A. Fiorella, voce Reato, cit., p. 778, nt. 18; M. Romano, Commentario, I, cit., pre-art. 39, p. 333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