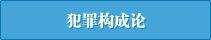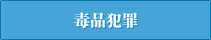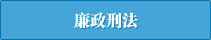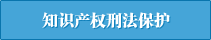魏东:论传统侵财罪的保护法益
论传统侵财罪的保护法益*
——基于实质所有权说的法理阐释与案例分析
魏 东**
(四川大学 法学院,610207)
引用本文时请注明出处:魏东:《论传统侵财罪的保护法益——基于实质所有权说的法理阐释》,载《法学评论》2017年第4期。
【内容摘要】侵财罪保护法益“所有权说”与“占有说”之争的焦点,不在于他人财产所有权是否可以成为侵财罪的保护法益,而在于单纯的占有是否可以充足侵财罪的保护法益。侵财罪保护法益的实质所有权说,既是侵财罪的入罪立法论根据,也是侵财罪的解释论根据。刑法解释论上应采用侵财罪保护法益的实质所有权说,特别注意基于犯罪对象物之“财产所有权”与基于犯罪被害人之“他人”的实质化审查,从法理上厘清司法实践中众多疑难案件的定性处理问题,依法将那些侵犯实质所有权的行为解释为侵财罪。
【关键词】侵财罪保护法益 他人财产所有权 实质所有权说 刑法解释
一、引言
我国刑法学界关于传统侵财罪[1]的保护法益(犯罪客体)问题,目前主要有“所有权说”与“占有说”之争。所有权说主张侵财罪的犯罪客体是他人财产所有权(亦即公私财产所有权,或者国家、集体和公民的财产所有权)。占有说主张侵财罪的保护法益是占有,但并不否定他人财产所有权可以成为侵财罪的保护法益(因所有权当然包含占有),而是认为单纯侵害了财产所有权四项权能之一的占有的也可以充足侵财罪的保护法益。[2]换言之,“所有权说”与“占有说”之争的焦点,不在于他人财产所有权是否可以成为侵财罪的保护法益,而在于单纯的占有——如针对违禁品或者赃物以及暂扣物或者质押物等的单纯占有——是否可以充足侵财罪的保护法益。占有说认为单纯的占有可以充足侵财罪的保护法益;所有权说则认为单纯的占有不可以成为侵财罪的保护法益,而只有他人财产所有权才能成为侵财罪的保护法益。这里对争议焦点的粗略梳理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明确:针对违禁品或者赃物以及暂扣物或者质押物等实施的侵害行为——以非法获取违禁品或者赃物的行为为例——其行为入罪的违法性根据与解释路径应该为何?所有权说因为主张侵财罪保护法益必须是他人财产所有权,因而认为非法获取违禁品或者赃物的行为入罪的违法性根据仍然在于其侵害了他人财产所有权,而这里“他人财产所有权”应当实质化、教义学化地解释为行为所侵之财背后的合法所有人之财产所有权,从而可以进一步确定此种行为入罪的解释路径。我国传统刑法理论在解释非法获取违禁品或者赃物的行为入罪理由时,应当说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已形成了“归根结底是对国家、集体或他人财产权利的侵犯”[3]这一通说,而这一通说直到当下仍然强势地成为了中国刑法学中“有约束力的教义学知识”与“法教义学语句”[4],并且“可以形成有约束力的基础概念、意义模式,尤其是关于法律论证标准的秩序意见”[5]。尽管其在晚近若干年因为占有说的引入而面临批评,但是应当说这些批评仍然难以撼动通说成为当下中国刑法理论解释侵财罪犯罪客体的主导地位。[6]而占有说因为主张侵财罪保护法益既可以是所有也可以是单纯占有,因而认为非法获取违禁品或者赃物的行为入罪的违法性根据可以认为仅仅在于其侵害了占有,并以占有说直接疏通此种行为入罪的解释路径。
一般认为,持占有说的学者是在借鉴吸纳德日刑法学的学术传统与刑法知识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学术见解。在德国刑法学上,以诈骗罪为中心展开的是法律的财产说、经济的财产说及法律-经济的财产说的见解;而在日本刑法学上,以盗窃罪为中心展开的是本权说、占有说及各种中间说(包括基于本权说的中间说与基于占有说的中间说)的争论。[7]车浩教授指出,国内刑法学界的通说认为,财产犯罪的法益或者说客体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但是,随着近年来国内引入了日本学界关于本权说与占有说的争论,以盗窃罪为基本的讨论平台,主张财产犯罪的法益包括占有的看法,日益成为一种有力的观点。[8]那么,占有说作为“一种有力的观点”相对于国内通说(所有权说)而言是挑战者,其挑战国内通说的“基点”是什么,其难以撼动国内通说而成为其自身的“痛点”又是什么?这种学术观察和逻辑梳理可能有助于我们明辨是非。
二、实质所有权说的法理阐释
实质所有权说的核心和要旨是对于作为侵财罪保护法益的“他人财产所有权”的实质化审查判断,其在将传统所有权说明确“升华”为实质所有权说的基础上,具有优于占有说及其他相关学说的实质合理性和强大逻辑解释力。
(一)实质所有权说相对于占有说的比较优势
如前所述,占有说论者所针对并试图逻辑地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获取违禁品或者赃物的行为入罪的违法性根据与解释路径,只能是占有权或者占有状态(占有说),而不能是所有权(所有权说)。占有说论者进一步指出,根据所有权说,“对于盗窃或者抢劫他人占有的违禁品的行为,难以认定为盗窃罪或抢劫罪”,并且“所有权说难以回答抢劫他人用于违法犯罪的财物(主要包括犯罪工具与犯罪组成之物)的行为,是否构成抢劫罪的问题”,以及“所有权说不能回答行为人(甲)骗取盗窃犯人(乙)所盗窃的财物(丙所有)的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的问题”,[9]而认为占有说对此类问题的逻辑解释却可以达致“天衣无缝”,并进而认为“此点”能够成为占有说对所有权说的挑战“基点”。但是笔者认为,占有说恰恰在“此点”挑战中可能仍然难以获得超越所有权说的逻辑说理优势。
从实质上审查,获取违禁品或者赃物的行为,其入罪根据不可能是因为法律要保护违禁品或者赃物的相关占有人之“占有”(占有权或者占有状态),恰如占有说诘难所有权说之入罪根据不可能是因为法律要保护违禁品或者赃物的相关占有人之“所有权”的逻辑说理一样,试图从“违禁品或者赃物的相关占有人”本身之占有或者所有权“这一点”来说明侵财罪保护法益太过于机械而狭隘,此种机械说理的荒诞性显而易见,难分伯仲,因而在“这一点”上占有说难以获得超越所有权说的立论“基点”。不但如此,彻底的实质审查恰恰可以发现,所有权说正是超越了“这一点”而获得足够空间进行逻辑说理——或者从刑法“保护”的法益实质,或者从侵财行为“侵犯”的法益实质进行逻辑说理——而能够合乎逻辑地论证获取违禁品或者赃物的行为入罪的违法性根据与解释路径。如前所述,传统刑法理论通说阐明了:获取违禁品或者赃物的行为,从刑法“保护”的法益实质上看,该行为侵犯了犯罪对象“物”背后始终客观存在的“他人”——即作为真正的犯罪被害人的“他人”的实质化审查——的财产所有权,这是刑法所必须保护的法益,因而具有侵财罪所内含的违法性;从侵财行为“侵犯”的法益实质上看,行为人针对违禁品或者赃物等非行为人自己所有的财物实施侵害行为,实质上恰恰是针对占有人背后的真正的被害人“他人”所有的财物实施侵害行为,当然具有“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的法益实质,从而也具有侵财罪所内含的违法性。但是占有说在此却毫无逻辑周旋的任何空间,缺失基本的逻辑力量,更谈不上超越所有权说。由此也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现象,所有权说必须强调对“他人财产所有权”的实质化审查——主要是犯罪对象“物”之财产所有权的实质化审查与犯罪被害人之“他人”的实质化审查——才能获得更加稳固周全的逻辑解释力,因而有必要将传统所有权说“升华”为实质所有权说。
而占有说论者所面临的理论诘难是:所有权人从其他合法占有人处获取自己所有的财物的行为不入罪的法理基础与解释路径,只能采用背离占有说的“例外说”或者“排除说”。即占有说在这个理论诘难面前被迫消退而采用例外不适用占有说(即“例外说”)或者排除适用占有说(即“排除说”),深刻表明其“不能合乎逻辑地”解决显而易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其根本原因可能正在于占有说忽略了占有背后的“实质”恰恰就是他人财产所有权(实质所有权说)。由此,占有说在挑战所有权说的逻辑论辩中形成了理论困境:不但挑战“基点”难保,而且挑战“痛点”难解。
关于占有说的逻辑悖论,在侵占罪的构成机理中表现尤为明显。“占有”行为当其仅侵犯“占有”(即占有权或者占有状态)本身不构成侵财罪,只有在其侵犯“所有”(即他人财产所有权)之际方能成立侵财罪(即侵占罪),那么,侵占罪作为侵财罪为何只有在行为人将“占有”变为“所有”才能构成侵财罪,欠债不还为何不构成侵占罪?对此逻辑悖论与理论追问,占有说根本就无言以对。陈兴良教授指出:侵占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是以占有与所有的分离为前提的,故而变占有为所有(所有权说)的行为才构成侵占罪;但是“欠债不还”为何不构成侵占罪呢,这是因为“对于货币来说,采用的是占有即所有这一原理”,行为人在获得借款或者合同对价的同时即已经获得作为欠款的金钱的所有权,此时“占有即所有,因而不存在占有与所有的分离”,当然不能成立侵占罪;只有在“基于他人的委托行为所受领的金钱,因为受领的金钱属于委托人所有,因此,如果受托人随意使用该金钱的构成侵占罪”。[10]陈兴良教授的这些论述,完全可以认为是在坦陈作为侵财罪的侵占罪的保护法益只能是所有权说之法理。可见,占有说在诠释侵占罪的法理基础与解释路径时,也只能被迫消退而采用背离占有说的“例外说”或者“排除说”。而秉持占有说立场的张明楷教授在侵占罪问题上似乎巧妙地“回避”了占有说,称“盗窃罪的法益直接影响盗窃罪构成要件的解释与盗窃案件的认定。不仅如此,关于盗窃罪法益的观点,不仅适用于抢劫罪中的财产法益部分,而且也适用于抢夺罪、聚众哄抢罪乃至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等取得罪”。[11]那么,作为非转移取得罪的侵占罪是否可以适用占有说呢?张明楷教授采用了“表面不说,暗中回避”的策略,这种回避而不明说的立场(回避说)在根本上就与“例外说”和“排除说”如出一辙,均属于对占有说的公然“背叛”。相映成趣的是,所有权说在此却获得了完美诠释:作为侵财罪的侵占罪之保护法益“正是”并且“只能是”他人财产所有权,欠债不还不能成立侵占罪的根本原因“正是”并且“只能是”该行为没有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
综上可以发现,当前质疑甚至反对占有说的学术见解日渐上风,不但有学者明确指出“占有不是财产犯罪的法益”[12],而且占有说在“所有权人从其他合法占有人处获取自己所有的财物的行为不入罪的法理基础与解释路径”等理论诘难面前难以自圆其说,甚至被迫消退而“不能合乎逻辑地”内化解决显而易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凸显了占有说缺乏理论解释力、逻辑自洽性和保守性。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占有说在其与所有权说的理论竞争中明显呈现出颓废无为的态势。相对而言,所有权说比占有说具有“更好”的理论竞争优势,因为按照社科法学的方法论特征强调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的“理论的竞争和进步”,对于“同一个现象或是问题,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理论都可以对其进行解释或解决的话,我们该如何作出取舍:哪一个理论相对而言,是更可取的,或者是更‘好’的”;[13]而“更好”的理论的选择判断标准,必须是解释力越强的、更容易得到实证检验的、表述更为精确的以及越保守的(即更能与原有的理论体系相容的)理论。[14]当然,公允地讲,传统所有权说也应当凤凰涅槃“升华”为实质所有权说,以增强其更加稳固周全的理论解释力和逻辑自洽性。
从保护法益的立场看,刑法作为法益保护法抑或秩序维护法,实质所有权说才能彻底反映刑法“保护”的法益实质。而占有说流于形式、疏离所有权实质,其在占有脱离于使用、收益和处分权能的关联性判断时根本无法准确判断刑法保护的法益实质,因而缺乏实质合理性。无论是获取违禁品或者赃物的行为入罪的违法性根据与解释路径,还是所有权人从其他合法占有人处获取自己所有财物的行为不入罪的法理基础与解释路径,都不能仅仅对占有状态进行形式审查,而必须实质化审查占有及其与使用、收益和处分三项权能的整体关联性,方能获得实质合理性。
同理,从被侵害法益的立场看,行为刑法和行为人刑法强调从行为本身造成法益侵害以及征表行为人危险性格的特点,实质所有权说才能周全反映侵财行为“侵害”的法益实质以及侵财行为人所具有的“侵财”法益的危险性格,而占有说无法反映侵财行为侵害所有权的法益实质以及侵财行为人所具有的“侵财”法益的危险性格。
刑法“保护”的法益实质与侵财行为所“侵害”的法益实质的完整统一,构成了侵财罪保护法益(即他人财产所有权)的“二维码”。侵财罪的保护法益只能是他人财产所有权,即侵财行为通过排除所有权人或者占有人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形式,最终在实质上侵害了他人财产所有权,才能成为侵财行为入罪(侵财罪)的违法性根据与解释路径;相反,如果“表面的”侵财行为最终没有在实质上侵害他人财产所有权(如所有权人从其他合法占有人处获取自己所有的财物的行为),则由于其不具有侵财罪的保护法益而不构成侵财罪(但不排除构成他罪)。可见,侵财行为入罪的违法性根据与解释路径,只能定位于审查侵财行为所侵害的他人财产所有权这一违法实质:如果某个行为并没有侵害所有权实质(尽管其可能侵害了其他法益),则该行为不构成侵财罪(尽管其可能构成他罪);如果某个行为侵害了所有权实质,则该行为可以构成侵财罪。
(二)实质所有权说相对于法律-经济的财产说的比较优势
以上主要针对占有说与所有权说的学术之争展开的讨论,期以论证实质所有权说的合理性。但有学者可能认为,实质所有权说还面临着“法律-经济的财产说”(德国刑法理论)和“中间说”(日本刑法理论,具体包括基于本权说的中间说和基于占有说的中间说)的挑战,因而这些关联性的理论问题有待进一步检讨。
关于“法律-经济的财产说”,江溯教授和蔡桂生教授均主张采用此说。江溯教授认为“从我国刑法典和司法实践可以看出,我国关于财产犯罪采取的是法律—经济的财产说”[15],而蔡桂生教授则进一步指出“按照法律·经济财产说的理解,只有被告人的行为侵犯了不违法的经济利益,被告人的行为才成立相应的财产犯罪”[16]。其实,德国刑法理论是在阐释诈骗罪的保护法益时才提出并采用了“法律-经济的财产说”,其目的在于弥补“经济的财产说”的显而易见的缺陷,因为“经济的财产说”无法恰当诠释那些尽管具有经济价值但是不需要或者不应该获得法律保护的“财产”(如自由自在的空气和鸟粪)为何不能成为诈骗罪的保护法益这一疑问,进而在经济价值之外添加了应该获得法律保护的“财产”(如以容器包装后的空气和鸟粪)的限制之后才能成为诈骗罪的保护法益,从而形成了“法律-经济的财产说”。这里,蔡桂生教授使用了“不违法的经济利益”这一语词,其到底有几层意思,可能是一个包括蔡桂生教授本人在内的所有人都难以说明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应当承认当且仅当该“不违法的经济利益”可以实质地转化为“他人财产所有权”时,该“不违法的经济利益”才可以成为侵财罪的保护法益,因而,侵财罪的保护法益仍然必须回归到“他人财产所有权”的实质化审查判断。
至于“中间说”,张明楷教授主张引进此说并进行本土化改造。张明楷教授认为“盗窃罪的法益首先是财产所有权及其他财产权,其次是需要通过法定程序改变现状(恢复应有状态)的占有¼¼就狭义的财物而言,这里的‘财产所有权’可以根据民法确定,即包括财物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与处分权;‘其他财产权’既包括合法占有财物的权利(如他物权),也包括债权以及享有其他财产性利益的权利;在合法占有财物的情况下,占有者虽然享有占有的权利,却不一定享有其他权利,尤其不一定享有处分权”[17]。从张明楷教授的上列阐释内容看,其在承认财产所有权是侵财罪保护法益的前提下,进一步指出“其他财产权”和“占有”也可以成为侵财罪保护法益。其中“占有”问题的讨论已经如前所述,这里不再赘述。那么,如何看待“其他财产权”与侵财罪保护法益之间的关联关系呢?笔者认为,“其他财产权”肯定需要刑法保护,但是仅凭此据难以确证“其他财产权”就是侵财罪的保护法益这一结论的正确性。比如租赁权、质押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等“其他财产权”(指财产所有权之外的其他财产权),尽管其应当获得刑法保护并且可以成为诸如非法经营罪或者侵犯著作权罪等犯罪的保护法益,但是,只有在这些“其他财产权”可以实质地转化为“他人财产所有权”并且被直接侵害时,该“其他财产权”才能够实质地成为侵财罪的保护法益,从而侵财罪的保护法益仍然必须回归到“他人财产所有权”的实质审查判断,其原理如同德国刑法理论中“法律-经济的财产说”一样。
应当说,侵财罪保护法益的实质所有权说,既是侵财罪的入罪立法论根据(立法原理),刑法立法文本仅仅是将那些侵犯实质所有权的侵财行为规范为侵财罪;也是侵财罪的解释论根据,刑法解释论上仅仅可以将那些侵犯实质所有权的侵财行为解释为侵财罪。侵财罪保护法益的实质所有权说(即“他人财产所有权”的实质化审查),加上行为人主观上所具有的“非法占有目的”和故意责任的实质审查,有利于法理上厘清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众多疑难案件的定性处理问题。
三、实质所有权说的案例分析
如前所述,实质所有权说所主张的“他人财产所有权”的实质化审查判断,可以具体细化为基于犯罪被害人之“他人”(之“财产所有权”)与基于侵财罪犯罪对象物之“财产所有权”的实质化审查判断两个方面。而在犯罪对象争议案件中,基于作为犯罪对象“物”之财产所有权的实质化审查尤为关键。按照侵财罪保护法益的实质所有权说,在某一侵害行为针对“物”实施侵害时,该侵害行为是否可以评价为侵财罪所内含的违法性,关键在于犯罪对象“物”之财产所有权是否遭受侵害这一实质审查:若是,则该侵害行为具有侵财罪所内含的违法性;若不是,则该侵害行为不具有侵财罪所内含的违法性(但不排除其具有其他犯罪所内含的违法性)。
(一)所有权人“获取”自有财物的行为定性处理
如前所述,根据实质所有权说,所有权人实施“获取”(如“窃取”、“强取”等)他人占有的自己所有财物的行为,由于他人占有不能否定所有权人的财产所有权,因而没有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只要行为人没有借此实施进一步勒索或者诈骗等后续侵财行为,就不构成侵财罪。这种解释结论现在基本上不存在争议,但是在具体案件中可能还需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如果行为人有进一步的后续侵财行为(可简称“后续行为”),如行为人隐瞒自己取回了自有财物的事实而向对方索赔或者扣抵债务,则其后续行为通常可定侵财罪。但是,此种后续行为在具体罪名的确定上可能还存在争议,值得进一步检讨:有的主张以先前实施的“获取”行为为据确定侵财罪的具体罪名(如盗窃罪、抢夺罪或者抢劫罪),有的主张以后续行为为据确定侵财罪的具体罪名(如诈骗罪或者敲诈勒索罪)。例如案例1。
【案例1】叶文言等盗窃案[18]
2000 年10月5 日,被告人叶文言驾驶与叶文语、林万忠共同购买的桑塔纳轿车进行非法营运, 轿车被苍南县灵溪交通管理所查扣,存放在三联汽车修理厂停车场。后叶文言、叶文语与被告人王连科等合谋将该车盗走。1 0 日晚,几名被告人趁停车场门卫熟睡之机打开自动铁门,将轿车开走。2001年1月 8 日,被告人叶文言、叶文语以该车被盗为由, 向灵溪交通管理所申请赔偿,后获赔11.65 万元。苍南县人民法院以盗窃罪分别判处5 名被告人有期徒刑4年6个月到10 年 6 个月不等的刑罚。后被告人上诉,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最高人民法院刑庭编发这一案件时载明的主要裁判理由是:[19]本人所有的财物在他人合法占有、控制期间,能够成为自己盗窃的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行为人秘密窃取他人占有的自己的财物的行为都构成盗窃罪,是否构成盗窃罪,还要结合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而定。如果行为人秘密窃取他人保管之下的本人财物是为了借此向他人索取赔偿,这实际上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应以盗窃罪论处。相反,如果行为人秘密窃取他人保管之下的本人财物,只是为了与他人开个玩笑或逃避处罚,或者不愿将自己的财物继续置于他人占有、控制之下,并无借此索赔之意的,因其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不以盗窃罪论处。构成其他犯罪的,按其他犯罪处理。
关于叶文言案的定性处理,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叶文言构成盗窃罪,并且这一判决结果获得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可。理论界对此案件的定性处理,确实有支持定盗窃罪的观点,如有学者认为“自己的财物,不成为自己盗窃的对象”,“但是,窃取本人已被依法扣押的财物,或者偷回本人已交付他人合法持有或保管的财物,以致他人因负赔偿责任而遭受财产损失的,应以盗窃罪论处。”[20]
不过,笔者认为,尽管叶文言案的总体裁判立场可以说是采用了侵财罪保护法益的实质所有权说;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叶文言案的裁判理由本身仍然存在一定问题,继而对叶文言等人的罪名认定可能存在疑问。就本案而言,叶文言等人在自己的轿车被交通管理部门扣押后,在深夜将被扣押车辆盗出后藏匿、销售,进而以该车被盗为由向交管部门索赔,此时叶文言等人的“后续行为”才具有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即本案中的公共财产所有权)的违法性实质,而这种“后续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特征但是并不符合盗窃罪的构成特征,因而依法应当以诈骗罪定罪处罚,而不应以盗窃罪定罪处罚。至于最高法在裁判理由中指出“如果行为人秘密窃取他人保管之下的本人财物是为了借此向他人索取赔偿,这实际上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应以盗窃罪论处”,应当说这种解释路径存在一定错误,其并没有恰当运用侵财罪保护法益实质所有权说对行为人先前的“盗窃行为”与盗窃之后的“后续行为”进行行为定型性审查和具体的违法性审查,可能是本案混淆盗窃罪与诈骗罪之间界限的关键所在,其仅仅根据行为人主观目的而对行为人定性为盗窃罪缺乏法理依据。“盗窃”自己所有的被扣押的财物,尽管其可能导致依法没收、收缴或者赔偿落空而至于国家财产受损失或者行政管理秩序被破坏,但是该“盗窃”行为仍然不应定盗窃罪(但不排除构成其他罪时可以定其他罪),其重要法理正在于行为人“盗窃”自己所有的财产本身并不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即并不侵犯侵财罪的保护法益,因而不能构成作为侵财罪的盗窃罪;而可能构成侵财罪的行为只能是其盗窃之后的“后续行为”,即行为人再向交通管理部门提出索赔这种“后续行为”才具有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的违法性实质,这种“后续行为”依法应构成作为侵财罪的诈骗罪(而不是对其先前的盗窃行为定侵财罪),如此才能保持刑法解释逻辑上的一致性和合理性。
其二,如果行为人尽管没有进一步的后续侵财行为,但是行为人窃取或者强取自有财物的行为本身就同时又触犯了其他罪名的,如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或者妨害公务罪、故意伤害罪甚至故意杀人罪等,则应依法定性为相应的其他罪名,但是依法不构成侵财罪。例如:案例2至案例4。[21]
【案例2】王彬故意杀人案[22]
1997年3月28日10 时许,被告人王彬驾驶自己的一辆简易机动三轮车在204国道上行驶,因无驾驶执照,其所驾车辆被执勤交通民警查扣,停放在交警中队大院内。当晚l0 时许,王彬潜入该院内,趁值班人员不备偷取院门钥匙欲将车开走。值班人员吕某发现后上前制止。王彬即殴打吕某,并用绳索将吕某手、脚捆绑,用毛巾、手帕、布条堵勒住吕某口鼻,致吕某窒息死亡。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被告人王彬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王彬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王彬构成故意伤害罪,故撤销一审判决,以王彬犯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最高人民法院刑庭编发这一案件时载明的主要裁判理由是:[23]王彬主观上是想取回自己被公安机关查扣的车辆,也就是自己拥有所有权的财产,而不是非法占有自己不享有所有权的财产,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此,王彬盗取自己被扣机动车的行为不同于盗窃,这也就决定了其在盗取自己被扣车辆过程中致人死亡的行为不能认定为抢劫。
可以认为,王彬案的裁判立场表明,我国司法实践已采用侵财罪保护法益的实质所有权说。因为毋容置疑,若采用占有说,王彬因在侵害他人占有财物时采用暴力手段而致人死亡,就应被定性为抢劫罪。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坚持占有说的部分学者客观上也得出了王彬不构成抢劫罪的解释结论,但是应当注意其解释路径是在采用占有说的前提下,进一步采用“例外说”或者“排除说”才得以获得这个解释结论的,表明占有说的“理论正确性”在本案中存在例外或者排除,因而占有说并不妥当。
但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关于王彬不构成侵财罪(抢劫罪)裁判理由的阐释,主要是针对被告人的主观故意和目的来展开的,认为王彬“不是非法占有自己不享有所有权的财产,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所以依法不予认定侵财罪(抢劫罪)。而对于王彬的行为所侵害的犯罪客体是否包含他人财产所有权的问题,裁判理由只是在阐释其主观故意之中有“不是非法占有自己不享有所有权的财产”的内容,而并没有明确说明王彬的行为没有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从而没有侵财罪保护法益的实质内容,因而王彬不构成抢劫罪。那么就此而论,尤其是从判决说理的周全性看,裁判理由若在说明王彬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同时,进一步说明王彬客观上没有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的实质违法性,则更为精当。
【案例3】陆惠忠非法处置扣押的财产案[24]
2005年5 月10 日上午,因被告人陆惠忠未按时履行民事判决,无锡市开发区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扣押了陆惠忠所有的起亚牌轿车一辆 ,加贴封条后将该车停放于法院停车场。当天下午 5 时许,陆惠忠至法院停车场,趁无人之机,擅自撕毁汽车上的封条,将轿车开走并藏匿于无锡市某宾馆停车场内。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以陆惠忠犯非法处置扣押的财产罪判处有期徒刑 1年。
最高人民法院刑庭编发这一案件时载明的主要裁判理由是:[25]本案定性的焦点在于被告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有证据证明行为人窃取人民法院扣押的财物后,有向人民法院提出索赔的目的,或者已经获得赔偿,则应当以盗窃罪定罪处刑;反之,如果没有非法占有目的,把自己所有而被司法机关扣押的财产擅自拿走,则不能以盗窃罪处理。从本案证据来看,被告人主观上尚没有使法院扣押的财物遭受损失或非法索赔的目的,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据不足,因而其行为不构成盗窃罪。
同样可以认为,陆惠忠案的裁判立场业已表明,我国司法实践已采用侵财罪保护法益的实质所有权说。但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仍有两点:一是,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判理由中指出陆惠忠不构成侵财罪(盗窃罪),认为“本案定性的焦点在于被告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这一点说理如同王彬案的判决说理一样,只说了主观的违法性要素和责任性问题而没有说明客观违法性问题,亦即并没有明确说明陆惠忠的行为没有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从而没有侵财罪保护法益的实质内容(因而陆惠忠不构成盗窃罪)。可见,陆惠忠案的判决说理仍然有失充分,其在说明陆惠忠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同时,还应当进一步说明陆惠忠的行为在客观上“没有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的实质违法性,方可堪称精准。二是,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如果有证据证明行为人窃取人民法院扣押的财物后,有向人民法院提出索赔的目的,或者已经获得赔偿,则应当以盗窃罪定罪处刑,这一观点同样有所不当,理由如前所述:如果有证据证明行为人窃取人民法院扣押的财物后,有向人民法院提出索赔的目的,或者已经获得赔偿,应当承认陆惠忠将自己所有的轿车开走并藏匿的先前“盗窃行为”依法不构成盗窃罪,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一“先前行为”(即先前“盗窃行为”)没有侵害他人财产所有权的违法内容(但是具有非法处置扣押的财产的违法内容),因而不能构成侵财罪(但是构成非法处置扣押的财产罪);仅在其实施了“有向人民法院提出索赔的目的,或者已经获得赔偿”的“后续行为”时才具有侵财罪所内含的侵害他人财产所有权的违法内容,因而其“后续行为”才可能被评判为侵财罪,并且由于其“后续行为”更加符合诈骗罪行为定型特征,因而也只能以诈骗罪定罪处刑,而不能构成盗窃罪。
【案例4】江世田等妨害公务案[26]
1999 年11月间,被告人江世田与张信露等人合伙购买了卷烟机和接嘴机各 l台用于制售假烟。后该设备被政府相关部门组成的联合打假车队查获。张信露与被告人江世田得知后,纠集数百名不明真相的群众拦截、围攻打假车队,将查扣的载有制假烟机器的农用车上的执法人员董金坤等人拉出驾驶室进行殴打。被告人黄学栈与江传阳等人乘机开走 3部农用车。随后, 张信露与被告人江世田又聚集鼓动黄学栈、黄海兵等一群人,毁损、哄抢执法人员的摄像机、照相机等设备,并对执法人员进行殴打,直至公安人员赶到现场时才逃离。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被告人江世田犯聚众哄抢罪,判处有期徒刑1O 年。后江世田等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江世田的行为构成妨害公务罪,故撤销一审判决,以江世田犯妨害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最高人民法院刑庭编发这一案件时载明的主要裁判理由是:[27]本案被告人并不是要非法占有公私财物,而只是不法对抗国家机关的打假执法公务活动, 意欲夺回被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查扣的制假设备。制假设备是犯罪工具,虽属不法财产,但毕竟为被告人所有,抢回自有物品与强占他人所有或公有财物显然不同。被告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只有妨害公务的目的。因此,江世田的行为不构成抢劫罪或聚众哄抢罪,而构成妨害公务罪。
江世田案有两个判决结果。一审法院认定江世田构成侵财罪(即聚众哄抢罪),大致可以认为其在侵财罪保护法益问题上采用了占有说,其解释路径是因为“被告人江世田与张信露等人合伙购买了卷烟机和接嘴机各 l台”已经被联合打假车队查获并占有,那么江世田等人聚众哄抢已被联合打假车队占有的卷烟机和接嘴机等财物,侵害了他人占有,所以认定江世田构成侵财罪(即聚众哄抢罪)。但是,二审法院撤销了一审法院认定江世田构成侵财罪(即聚众哄抢罪)的判决,认为江世田不构成侵财罪(即聚众哄抢罪),改判江世田只构成妨害公务罪。毫无疑问,江世田案终审判决的裁判立场再次表明,我国司法实践只能采用侵财罪保护法益的实质所有权说。
应当说,江世田案终审法院的生效判决是正确的。不过同样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从二审判决说理看,最高法指出“制假设备是犯罪工具,虽属不法财产,但毕竟为被告人所有,抢回自有物品与强占他人所有或公有财物显然不同。被告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其仍然只说了主观的违法性要素和责任性问题而没有说明客观违法性问题,并没有明确说明江世田的行为没有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从而没有侵财罪保护法益的实质内容,因而江世田不构成作为侵财罪的聚众哄抢罪。因而,从判决说理的周全性看,在说明江世田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同时,应当进一步说明江世田的行为在客观上“没有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的实质违法性。
(二)债权人“获取”到期债务人相当于到期债权价值财物的行为定性处理
债权人“获取”到期债务人相当于到期债权价值财物的行为如何定性处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分歧,有的主张定侵财罪,有的主张不定罪。笔者认为,债权人对于债务人的到期债务,有要求债务人履行支付义务的权利,从而到期债务人财产所有权不能有效排斥债权人的到期债权。因此,债权人“窃取”与“强取”到期债务人相当于到期债权价值的财物的行为,依法应当认定为没有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即到期债务人的财产所有权)的实质(并且同时也应当认定债权人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和目的),对此行为依法不应定性为侵财罪。当然,债权人若“窃取”与“强取”到期债务人超出其到期债务价值的财物,则可能具有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即债务人的财产所有权)的实质违法性,进而债权人可能构成侵财罪。例如案例5。
【案例5】但某强取质押汽车收回借款案。[28]
2012年9月至10月,黄某、帅某从被告人但某处两次借款共计20万元,并以黄某一辆汽车作为抵押物进行抵押登记,后黄某、帅某在还款期限到期后未能还款。2013年1月30日,但某伙同他人强迫黄某还钱未果后,但某强行将黄某汽车开走。事后,但某将该车以42.6万元的价格出售。其后,但某向黄某表示要归还超额部分钱款并多次磋商,终因双方在应付利息数额等问题上分歧过大而搁置。经鉴定:黄某汽车价值52.8208万元。公诉机关指控但某犯抢劫罪。
本案公诉机关指控但某犯抢劫罪,其法理依据可能是采用了占有说(或者基于占有说的中间说)。但是,笔者认为,若采用侵财罪保护法益的实质所有权说,则本案公诉机关的指控罪名可能值得研究。
笔者认为,本案但某的行为可以分为强取质押汽车并变卖汽车(第一个阶段)、处置汽车款(第二个阶段)这样两个阶段来具体分析其定性处理问题:
第一个阶段中,但某为实现合法债权而强行开走依法质押的轿车并变卖的行为,依法不构成侵财罪。理由在于:但某将到期债务人黄某的汽车强行开走并变卖是行使合法抵押权的行为,客观上并没有侵犯他人(黄某)财产所有权,缺乏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的违法性实质,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而但某的行为不构成抢劫罪。
第二个阶段中,但某在处置汽车款时,在实现债权后未能及时向黄某返还超额钱款的后续行为,应具体审查该“后续行为”是否具有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的违法性实质。黄某、帅某只是欠但某20万元债务,而但某以42.6万元的价格将该车出售,但该车的实际鉴定价值为52.8208万元。从民法上说,债权人在以变卖抵押物而获得的钱款实现了自己的合法债权后,应当及时将超额部分的钱款返还给债务人(对于超额部分的钱款,但某是实质上的保管人),但是本案中但某并未如此处理,在此意义上说,但某的行为可能涉嫌《刑法》第270条第1款“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规定(侵占罪)。当然,但某在后续处置汽车款过程中没有及时将多余钱款返还给被害人的行为,若有证据证实但某的行为“一开始”就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并且具有侵害他人财产所有权的违法性质,则依法可以定性为抢劫罪,但是在犯罪数额的认定上应当依法扣除其合法债权所对应的数额;若没有证据证实但某的行为“一开始”就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并且具有侵害他人财产所有权的违法性质,而仅有证据证实但某在事后处置汽车款过程中的“后续行为”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并且具有侵害他人财产所有权的违法性质,则应当谨慎地将但某的该“后续行为”认定为侵占罪,并且同样在犯罪数额的认定上应当依法扣除其合法债权所对应的数额;若没有证据证实但某的行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并且具有侵害他人财产所有权的违法性质,则应依法认定但某无罪。
四、结语
传统侵财罪的保护法益(犯罪客体)是“他人财产所有权”,通过对“他人财产所有权”的实质化审查判断,将传统所有权说明确提升为实质所有权说,可以获得优于占有说及其他相关学说的实质合理性、逻辑自洽性和强大解释力。侵财罪保护法益的实质所有权说既是侵财罪的入罪立法论根据,能够科学系统地阐释传统侵财罪的立法机理;也是侵财罪的刑法解释论根据,能够合理有效地解决相关争议案件的解释性疑难,确保刑法司法公正。因此,应当提倡侵财罪保护法益的实质所有权说。
Discussion on theprotected legal interest of traditional invading property crime
——based on the nomological interpretation and caseanalysis
of the theory of substantial proprietorship
WeiDong
(Sichuan University, Law School,610207)
[Abstract] Proprietorship theory and Occupationtheory, two theories about the protected legal interest of invadingproperty crime, the controversial point of which does not lie in whether others’property ownership right can become the protected interest of invading propertycrime or not, but whether pure occupational status can be the protectedinterest of invading property crime. The theory of substantial proprietorship,one of the theories about the protected interest of invading property crime, isnot only the theoretical gist of criminalized legislation, but also the gist of criminal lawinterpretation. The theory of substantial proprietorship should be adopted bythe theory of criminal law interpretation in the aspect of the protectedinterest of invading property crime, especially noticing the substantialexamination towards property ownershipright based on crime targets and otherpeople based on crime victims, clarifying qualitative problems ofnumerous hard cases from the nomological perspective in judicial practice, ipsojure interpreting the acts that invade the substantial proprietorship ascrimes.
[Key words] invading property crimes, the protectedinterest, property ownership right of others, the theory of substantialproprietorship, criminal law interpretation.
*本文系作者所承担的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点课题“刑法解释原理与实证问题研究”(12AFX00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魏东(1966.01—),男,法学博士,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我国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之中规定的传统侵财罪,主要指转移取得型侵财罪和变占有为所有型侵财罪(即侵占罪和职务侵占罪),但是不包括挪用资金罪、挪用特定款物罪、破坏生产经营罪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等四罪。本文后面论述中所用“侵财罪”,在没有特别声明时均指传统侵财罪。
[2]占有说论者在坚持占有说这一总体立场之下尚有进一步区分,如“基于占有说的中间说”兼“以经济的财产说为基础的折中说”(张明楷)、“对财物的支配关系”亦即“所有权和占有权”(周光权)、“限定的占有说”(胡东飞)等多种学说。上列观点分别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838页;周光权:《刑法各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3页;黎宏:《论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载《人民检察》2008年第23期;胡东飞:《财产犯罪的法益——以刑法与民法之关系为视角》,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2014年第2卷(总第38卷),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86-313页。
[3]高铭暄主编:《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480页。
[4]德国学者尼尔斯·杨森指出,若缺乏这种有约束力的教义学知识,有意义的法律论证就不会出现。参见:[德]尼尔斯·杨森:《民法中的教义学》,吕玉赞译,载《法律方法》第18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3页。
[5]德国学者尼尔斯·杨森指出:“法教义学可以确定法律论证所需的特定的概念性、体系性或其他普遍认可的前提;可以形成有约束力的基础概念、意义模式,尤其是关于法律论证标准的秩序意见。”[德]尼尔斯·杨森:《民法中的教义学》,吕玉赞译,载《法律方法》第18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3页。
[6]例如王作富教授认为,对于“抢劫其他违法犯罪分子手中的赃物”的行为应当定抢劫罪,其根据在于“这不是因为侵犯违法犯罪分子的所有权,而是因为按照法律规定,非法所得的赃物应当没收归国家。所以,上述行为实际上侵犯了国家所有权”。参见王作富主编:《刑法分则实务研究(第四版)》(中),中国方正出版社2010年版,第1024页。
[7]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834页。
[8]车浩:《占有不是财产犯罪的法益》,载《法律科学》2015年第3期。
[9]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837-838页。
[10]参见陈兴良:《译序》,载(日)佐伯仁志、道垣内弘人:《刑法与民法的对话》,于改之、张小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译序”第1-5页。
[11]张明楷:《刑法学(下)》(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939页.
[12]车浩:《占有不是财产犯罪的法益》,载《法律科学》2015年第3期。
[13]参见吴义龙:《社科法学的方法论特征》,载《法律方法》第18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7-50页。
[14]参见陈波:《奎因哲学研究》,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74页。
[15]江溯:《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法律-经济财产说之提倡》,载《法学评论》2016年第6期。
[16]蔡桂生:《刑法中侵犯财产罪保护客体的务实选择》,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12期。
[17]张明楷:《刑法学(下)》(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942页。
[18]参见陈民城:《叶文言、叶文语等盗窃案——窃取被交通管理部门扣押的自己所有的车辆后进行索赔的行为如何定性》,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第二庭编:《刑事审判参考)(2005年第2 集),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37~ 44 页。
[19]参见于志刚、郭旭强:《财产罪法益中所有权说与占有说之对抗与选择》,载《法学》2010年第8期。
[20]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8页。
[21]该三则案例均系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参考》所公布的典型案件,详见后文关于该三则案例来源的注释说明。
[22]参见朱伟德:《王彬故意杀人案——对在盗取自己被公安机关依法查扣的机动车辆的过程中致人伤亡的行为应如何定性》,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第二庭编:《刑事审判参考》(2001年第 5 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23]参见于志刚、郭旭强:《财产罪法益中所有权说与占有说之对抗与选择》,载《法学》2010年第8期。
[24]参见陈靖宇、陈利:《陆惠忠、刘敏非法处置扣押的财产案——窃取本人被司法机关扣押的财物如何处理》,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第二庭编:《刑事审判参考》(2006 年第4 集),法律出版社2006 年版,第26 -32 页。
[25]参见于志刚、郭旭强:《财产罪法益中所有权说与占有说之对抗与选择》,载《法学》2010年第8期。
[26]参见陈建安、汪鸿滨:《江世田等妨害公务案——聚众以暴力手段抢回被依法查扣的制假设备应如何定罪》,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第二庭编:《刑事审判参考》(2002年第5 集),法律出版社2002 年版,第53-58 页。
[27]参见于志刚、郭旭强:《财产罪法益中所有权说与占有说之对抗与选择》,载《法学》2010年第8期。
[28]参见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双检公诉刑诉[2014]36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