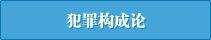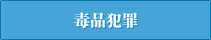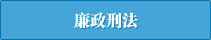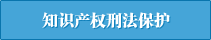邓子滨:中国刑法实质解释论的主要问题与批判
中国刑法实质解释论的主要问题与批判
邓子滨*
引用本文时请注明出处:邓子滨:《中国刑法实质解释论的主要问题与批判》,载魏东主编:《刑法解释》(第3卷),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8页。
目前,在我国刑法学界公开主张形式解释论的学者并不多见,当然对实质解释论表示怀疑的学者逐渐增加。值得注意的是,魏东教授提出了保守的刑法实质解释论的立场,指出:入罪上要保守并充分重视形式审查,坚守刚性化、形式化的入罪底线,即入罪上的刚性与形式立场。与保守的实质解释论相对应的是魏东教授称为全开放的实质解释论,这种实质解释论主张入罪上的弹性与实质立场,不求立法上的最大公正,但求司法上的最大公正。魏东教授认为,这恰恰是保守的实质解释论所反对的。其实,魏东教授所说的这种所谓保守的实质解释论,与我所主张的形式解释论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陈兴良
这篇文章是魏东教授看到《中国实质刑法观批判》(第二版)后要求我写的“命题作文”,他有理由关注这本书,因为陈兴良先生在“修订版序”中将其“保守的实质解释论”评价为与“形式解释论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1]如果有什么人认为陈先生的这一评价有些出人意料,那是因为他们不甚了解下列事实:魏东教授的“保守的”声音是在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之争如火如荼的时候出现的,他“所主张的‘刑法解释的保守性’或者‘保守的刑法解释’,其主要内容有三点:一是入罪解释的原则立场与出罪解释的常态化立场,即主张坚守刚性化、形式化的入罪底线的原则立场,准许有利于被告人的出罪的客观解释、实质解释的常态化;二是入罪解释的例外方法,即主张谨慎地准许例外的、个别的且可以限定数量的客观解释与实质解释对被告人入罪;三是刑法漏洞的立法填补原则立场”。[2]我就奇了怪了,魏东教授的主张明明是形式解释的,为什么非要冠以“保守的实质解释”之名不可?径直叫一个什么“开放的形式解释”不好吗?当然,认不认可陈先生和我的这些评价,是魏东教授自己的事情,只有他才最清楚什么是“保守的实质刑法观”。我的任务只是简明指出实质解释论的主要问题并对其加以批判。简明扼要,直指要害,不耽误读者的宝贵时间。
一、实质解释论是从主观到客观的入罪理论
在我看来,形式解释是指遵循立法原意,依照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的刑法解释论,它由古典学派所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衍生出来,强调追求法律的形式正义;实质解释则认定立法原意并不可寻,强调法律文本和解释者的互动,致力于破除法律的僵硬滞后,尽量扩充可能的文义,在个案的定罪量刑中综合考量各种因素,贯彻以兑现实质正义为目的的刑法解释论。不过,重要的不是形式解释和实质解释各自怎么说,而是看它们究竟怎么做。这里还是先援引《中国实质刑法观批判》中的一个著名案例:偷渡案。
偷渡案涉及以参加夏令营为由“骗取”签证,进入他国后滞留不归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偷越国(边)境罪。所持有的出境证件,即护照和签证都是真实的,也是在国家指定的海关口岸出境的,但在获取签证过程中对出境目的做了不实描述。为此,陈兴良先生专门撰写了“使用骗取的合法证件出境行为之定性研究——顾国均组织偷越国(边)境案”一文,收入《判例刑法学》。陈兴良先生提出:“如何界定这里的合法与非法?按照裁判理由,出境的合法与非法,是根据出境意图判断的,以旅游为名出境,实际上想在当地定居或者从事劳务,这就是非法出境。在这种情况下,对出境的合法与非法的判断,就不是一种形式判断,而是一种实质判断。显然,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我认为,出境的合法与非法是指出境证件的合法与非法。只要持合法证件出境,就属于合法出境。只有无证出境或者持有伪造、变造等证件出境,才属于非法出境。”[3]
再看以下几种情形:(1)事主正常驾车时,看到违法驾驶者左转抢行或者强行加塞并线,没有向违法者让步,进而发生刮蹭,事主建议或同意违法者给钱私了。事主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2)为了买房或者逃避债务,通过诉讼方式进行“假离婚”的,是否构成虚假诉讼罪?(3)吃完饭不给钱的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当真是由意思产生于饭前还是饭后决定的吗?以上案例若要入罪,必由主观开始,也就是由口供开始,先搞定被告人怎么想,再让被告人的行为符合被告之所想。在这一定罪过程,不刑讯逼供怎么行呢?
二、实质解释论的根基是经常修正为法益的社会危害性
以张明楷教授的实质解释为例:将非家庭成员的遗弃行为纳入遗弃罪;将军警人员显示军警身份进行抢劫的行为看作冒充军警抢劫,以便适用抢劫罪的加重构成;在刑法没有规定单位犯罪的情况下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4]凡此种种,都是以社会危害性大为思考起点的。作为实质犯罪论的首倡者,张明楷教授认为,实质的犯罪论主张以犯罪的本质为指导来解释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而犯罪的本质恰恰是法益侵害性,侵害或者威胁了法益是违法性的实质。[5]张明楷教授对于“实质解释论的基本内容”做了归纳:其一,对构成要件的解释必须以法条的保护法益为指导,而不能仅停留在法条的字面含义上。换言之,解释一个犯罪的构成要件,首先必须明确该犯罪的保护法益,然后在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内确定构成要件的具体内容。其二,当某种行为并不处于刑法用语的核心含义之内,但具有处罚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时,可以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扩大解释,从而实现处罚的妥当性。[6]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一些疑难案件中,入罪冲动那么势不可当?陈兴良先生认为,就司法理念而言,社会危害性观念没有受到彻底清算,内涵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理性的观念没有得到弘扬,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社会危害性理论不仅仅是一种学术话语,更是刑法学中的政治话语、意识形态话语。并且,经过数十年的宣传,社会危害性理论已经根深蒂固,形成了思维定势。社会危害性理论恰恰就是实质刑法观的理论基础。[7]因此,不从社会危害性理论批判入手,实质刑法观就难以从理论上得到彻底清理。社会危害性理论本身的反形式主义特征,决定了它就是一种实质主义法学。陈兴良先生进而毫不犹豫地选择形式理性而非实质理性,虽然牺牲了个案公正,使个别犯罪人员逍遥法外;但法律本身的独立价值得以确认,法治的原则得以坚持,这就有可能实现更大程度的社会正义。[8]
张明楷教授在其新近著作中直言:“不深入讨论条文与案件的具体焦点问题,仅抽象地从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是否滥用权力、是否破坏法治的角度进行讨论,就不可能得出合理结论。”[9]而我以为,当下中国大陆刑事法治的“急所”,恰恰是理念、观念问题,而不是处罚必要性等具体考量。不同理念、观念决定着不同解释方法的选择运用,而不是相反。我也不妨直言,某种刑法解释方法的选择以及多种方法的组合与排序,无非是不同理念、观念主导下的师心自用。
就犯罪论而言,学者早已指出:从一开始到目前,我国的犯罪论体系就是实质的,倒是在罪刑法定原则写入刑法典后犯罪论的形式化与实质化才成为一个问题。而且,从资产阶级的犯罪构成到社会主义的犯罪构成,就是从形式主义的犯罪构成向实质意义的犯罪构成的转化。[10]“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构成是一种实质性的犯罪行为的类型。这里所谓的‘类型’是指法律化的行为的类型,是立法者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的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的类型。”[11]传统的苏俄四要件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实际上以犯罪已经成立为前提”的体系,容易脱离法条的形式规定而径直追究实质的犯罪。因此,根据来自苏俄的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总能先找到有罪要件,然后补齐其他要件,易于入罪。在社会危害性理论指导下,先作实质判断,定罪过程不过是为社会危害性寻找证据而已。这种理论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只能革故鼎新,引入德日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通过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层层递进,使定罪活动从客观判断到主观判断、从形式判断到实质判断、从类型判断到个别判断,形成逻辑上的位阶关系,从而保证定罪活动的中立性、独立性与正确性。”[12]
三、实质解释是一种不顾忌手段约束的目的解释
实质论者关注目的,因为目的和实质的关系是友好的;形式论者关注目的,因为目的和形式关系是紧张的。想想那句“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虽出现在民法通则第58条和合同法第52条,所以,真正跟形式过不去的,不是实质,而是目的。张明楷教授认为:“法律解释应以贯彻立法目的为根本任务,当出现了不同的解释结论时,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目的论解释。研究刑法目的有利于立法与司法上合理控制处罚范围,将没有侵犯法益的行为以及侵害程度并不严重的行为排斥在犯罪之外。”[13]对刑法的解释应以刑法保护的价值来超越形式主义的束缚,不论对法律所作的扩张解释或限制解释,都必须符合法律的目的,而不是相反。目的论解释,据称已为人们所全盘接受,更被誉为解释方法之桂冠。[14]
多年以前,我在为一起单位行贿犯罪作辩护时,从公诉人那里领教了“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这句话所蕴含的超规范的解释力。我的委托单位从事拆迁工作,上级主管领导握有拆迁实权,所以单位决定为领导提供了一辆车,使用了4年,但车主是个不相关的人。我认为,机动车采用登记主义,登记给谁谁就是车主,车主对车有法律上的所有权。作为被告的领导,所享有的不过是从所有权分离出来的使用权,而使用权不是财物,不构成受贿罪,因而我的委托人也就不构成单位行贿罪。公诉人则认为,借用不过是形式,实际上该主管领导始终独享着对该车的占有、使用、支配、收益等权利,加起来就足够成为所有权。车主是名义上的,他没出过一分钱,没有实际交易,也没有实际控制,名义车主谈何取得所有权?
到今天为止,我仍然承认公诉人说的“是那么回事儿”,但我仍然认为,那个“形式”“名义”在法律上依然是重要的。法有法的逻辑,即使它在某些案件中是愚蠢的。如果不把这种“愚蠢的”法逻辑一以贯之地坚持到底,或者说,如果把所有掩盖了目的的形式都彻底否定,那么就会滑入一个“本质”的深渊。比如妓女卖淫,一把一利索的交易算卖淫,多次交易的更应该算卖淫;进而,不以次计而以时间计,以合法的、不合法的各种身份或者无身份的各种关系作掩护,一段时间内进行钱色交易的,算不算卖淫?如果算,那么“二奶”“小三”就都是妓女了。或者反过来问:“二奶”“小三”与妓女有何区别?其实,恩格斯曾最为深刻地揭露婚姻的“本质”,大意是说,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就是一种伪善地掩蔽着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卖淫。
实质解释实际就是目的解释。那么,刑法的目的到底指向何处呢?李斯特说,现在刑法不只反对犯罪人,也保护犯罪人;它的目的不仅在于设立国家刑罚权力,同时也要限制这一权力;它不只是可罚性的源由,也是它的界限。因此,刑法不仅要面对犯罪人保护国家,也要面对国家保护犯罪人;不单面对犯罪人,也要面对检察官保护市民。自从有刑法存在,国家代替受害人施行报复时开始,国家就承担着双重责任。[15]话说得没错,实在是很全面,颇得辩证统一之要领。也许赞赏这番话的人没有意识到,权力拥有者很喜欢这样的论断,而且时常被推为高论。这是因为,如果刑法的目的、任务、责任等都是双重或者多重的,就可以降解刑法尤其是罪刑法定原则对权力的压制力度,在实际的刑罚权力运作中就可以增加弄权的合法性。换言之,无论司法官员把力量、重点放在哪个方面,至少都没有明显的不妥。因此,权力得以游走于双重乃至多重目的、任务和责任之间,闪转腾挪,飞檐走壁,凭虚御风,根据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位置。权力自由了,权利就危险了。
问题在于,刑事司法中没有那么多统一,更多的是对立。要么有罪,要么无罪。“不仅……而且”句式被周详教授比喻为双截棍,优势在于其穿透力。它没有长棍的笨拙,没有刀剑的锋利,没有铁锤的重量,不善于使用者还会打到自己。但是,双截棍的所有的短处加起来就是长处,外表不像凶器或武器,容易携带,随便往裤兜里、衣服中一插即可,又随时可以抽出来使用而令对手猝不及防,因而具有非常强的欺骗性。双截棍又有非常强的弹性与灵活性,出招前可用手臂或后背隐藏遮蔽另一截,让对手看不清双截棍以什么确定的、可预判的路线运行。它的一头在运行中若遇到格挡时,另一头却可以转向,甚至借格挡之弹力而加重其打击力。因此,它可以从上下前后左右各个方向循环而灵活地以直线、弧线以及不规则的折线攻击,令对手防不胜防。真正阐述了武哲中的“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的辩证思想。当目的论解释祭出“不仅……而且”时,就是扽出一副双截棍,不知道使用的是哪一截“目的”击中并穿透了刑法规范的肌体。[16]
目的论解释之所以受欢迎,据说是因为特别契合当下刑法所谓保护法益和保护人权的双重诉求,也就是除了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共同诉求外,还多了一层保护网——法虽有明文规定,也要看法益侵害是否达到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为人权提供双重保护,岂不甚好?形式论者还有何话说?可问题就出在这里,争议也出在这里。目的论的实际解释结论,并不如实质论者所宣示的那样,在注重实现刑法的法益保护目的的同时,更注重严格控制解释的尺度,从而实现对国民权利的充分保护。事实是,有很多当罚不当罚尚有疑问的行为,却被目的论“解释进来”而不是“解释出去”,所以实际情况是入罪偏多而出罪偏少。这个判断,可以适用于整个实质解释论的实践。“主要的问题并不是法律的起源,而是法律的目标。如果根本不知道道路会导向何方,我们就不可能智慧地选择路径。”[17]卡多佐的这个说法乍听起来有理,但仔细一想未免自欺欺人。人们时常确实不知路向何方,也没有可信的地图。如果知道,那么人们自然会选择智慧之路。
实质论者往往持客观解释的立场,相信以立法者的用意作为法的目的,不如对法律目的做当下的诠释来得方便。他们自然会说立法原意并不十分明确,可信奉立法至上者又凭什么相信,司法者对刑法目的的理解,比之于对立法者原意的探究更接近正确?立法者是一个集体,但却不能说人多就没有共识,也不能说人少就一定能更好地把握刑法目的。所谓刑法的客观解释,无非是给司法者肢解令其不满的法律并确立自己的法律提供借口。换言之,“当一些法律本身没有包含可以用来证明法庭判决正当性的所谓‘法的目的’时,法庭可以无视法律条文的明确语言表述”。[18]因此,我不相信客观解释,并且认为,放弃对立法原意的探究,转而赋予法律以当下的目的,应当是例外,而不应当是规则。
需要警惕的是,刑法是实现社会管控的重要手段,在这一“逐利”过程中,可能学者与官府是不谋而合的。不谋而合的逐利可能使学者放松对“目的”的审视,很容易被官方目的裹挟,而法律本身又很难迫使拥有权力者放弃政策逐利。因此,试图用目的来判定手段之公正性是危险的,避免危险的唯一办法就是保持不断重新衡量目的的能力。[19]形式论者特别看重刑罚手段是否公正、适当,这不符合刑法的脾气,却符合刑法一代宗师的指点:“目的思想要求手段与目的相适应,而且在其使用中做到尽可能的节制。这一要求尤其适用于刑罚。”[20]而现在的观念之下,刑法似乎更强调打击犯罪的功能,而忽视其用来约束刑罚手段的初衷。因为就打击犯罪而言,根本无需借助刑法,没有刑法,刑罚的施用会更加有效。“就地正法”就是典型的高效刑罚。对手段的约束会大大制约目的的实现,因此,每次见到刑法目的的调整,都应首先想到它的真正动因,不过是想突破某种手段的限制。换言之,刑法不断地重新衡量目的,时而是因为手段的限制使得过去奉行的目的受到指责,时而不过是为了堂而皇之地摆脱对手段的制约。
以目的的正当来论证手段的正当,这是目的论支持者经常陷入的泥潭,并且经常被他们所推崇的目的所反噬。具体而言,就是以正当目的为不法手段正名,或者以宏大蓝图抹杀具体权利。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即便承认目的及其意义,对目的的追求也应当有所节制,“以目的论解释为最高准则”[21]的法学诠释方法也应当及时得到反省。理论上可以继续争辩,但实践中以高尚目的公然纵容卑劣手段的事件一再发生。典型事例就是强制引产大月份胎儿事件。目的会反噬自己。目的不仅可以选择,而且目的支配着手段,手段则为目的服务,于是,手段的自由选择以及过限使用就是无可避免的。所以,目的可以潜移默化地架空法律。因此,“让目的为手段辩解,被认为是应谴责的准则。”[22]要预先假定一种关于合法手段的范围,“除非对于手段的选择有非工具性的限制,否则,任何东西都可以在原则上被当作任何目的的手段。这样就不可能存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不论人们是否喜欢其结果,某些事必须做而其他事必须避免,可能是道德推理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特征”。[23]
重要的是,崇高的目的、宏伟的计划,往往是以人类的苦难和错误作基础的。[24]一旦将某种目的深深地刻上“高尚”二字,任何个人的牺牲以及各种形式的个人牺牲,就会轻而易举并且在所难免。[25]不是有学者直言支持击落被劫持的飞机吗?[26]其理由之一竟然是维护乘客“不被恐怖分子利用的尊严”。[27]人一旦接受“最高的善和最高的目的就是幸福”的思想,就可能被控制在受奴役的地位。人的自由和尊严不允许把幸福和快乐当作生活的目的和最高的善,在自由和幸福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冲突。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种声音:“听我的,你就会幸福。”[28]
四、一点补叙
陈兴良先生在2012年5月第11期“刑法学思潮论坛”总评中用“极致比较”的方式说明实质论的入罪风险大于形式论:“如果是极端的实质解释论,只要有处罚必要性,都要受刑法处罚,而无论法律有无规定;如果是极端的形式解释论,只要有法律规定,都要受刑法处罚,而无论有无处罚必要性。一目了然,当然是实质论的处罚范围大,因为法律规定的范围当然比法律没有规定的范围小得多的多。”无论口头承认与否,变化悄然发生着。实质论者近年来的著述中,所举的例子已经基本都是出罪的了。而关于形式论与实质论的争议,我认为不是偃旗息鼓,而是刚刚拉开序幕,因为以构成要件实质化为代表的整个实质化运动,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实践中,罪刑法定原则屡遭劫难,岌岌可危;理论上,任何犯罪论体系都无从抵敌“不惜一切的实质正义”。陈兴良先生总结说:在解释论中,突破刑法条文的字面含义进行实质解释,就使得形式解释成为不可能。因此,对于实质解释论来说,确实存在一个只要实质解释而不要形式解释的问题。但在形式解释论中,先做形式解释,如果形式解释就排除了构成犯罪的可能性,当然也就不存在再做实质解释的问题。但如果经过形式解释,符合构成要件,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实质解释,如果不具备犯罪的实质内容,仍然可以从犯罪中加以排除。由此可见,形式解释论并不排斥实质解释,而是主张形式判断先于实质判断,由此而将实质判断的功能限于出罪。形式解释论和实质解释论之争,对于形式解释论来说,并不是要不要实质解释之争,而是实质解释和形式解释的位阶之争,实质解释的功能之争。[29]
*邓子滨,男,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1] 参见邓子滨:《中国实质刑法观批判》(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修订版序”第4-5页。
[2] 魏东主编:《中国当下刑法解释论问题研究——以论证刑法解释的保守性为中心》,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26页。
[3] 陈兴良:《判例刑法学》(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4页。
[4] 参见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08页、第683-739页。
[5]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绪论第12页。
[6] 参见张明楷:“实质解释论的再提倡”,《中国法学》2010年第4期,第49-51页。
[7] 参见邓子滨:《中国实质刑法观批判》(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初版序”第7页。
[8] 陈兴良:《刑事法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
[9] 张明楷:《刑法学》第五版(上),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57页。
[10] 参见姜伟:“犯罪构成比较研究”,《法学研究》1989年第5期。
[11] 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修订版,第73页。
[12] 参见邓子滨:《中国实质刑法观批判》(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初版序”第9页。
[13] 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
[14] 参见[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页。
[15] 参见[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96页。
[16] 参见周详:“论一只‘牛虻’在中国刑法学术生态圈的诞生”,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0-91页。
[17] [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62页。
[18] [美]彼得·萨伯:《洞穴奇案》,陈福勇、张世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34页。
[19] [美]阿兰·布鲁姆:《巨人与侏儒》,秦露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
[20] [德]冯·李斯特:《论犯罪、刑罚与刑事政策》,徐久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7页。
[21] 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代序第11-12页。
[22] [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神学》,刘小枫编,刘宗坤、吴增定等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50页。
[23] [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页。
[24] 参见[英]霍布豪斯:《形而上学的国家论》,汪淑钧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1页。
[25] 参见[英]迈克尔·罗森:《尊严:历史和意义》,石可译,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95-96页。
[26] 我向来反对击落被劫持的飞机。参见邓子滨:《斑马线上的中国》,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60-63页。
[27] 张明楷:《刑法学》(第五版上),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22页。
[28] [俄]别尔嘉耶夫著:《论人的使命》,张百春译,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136页。
[29] 参见邓子滨:《中国实质刑法观批判》(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修订版序”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