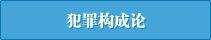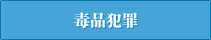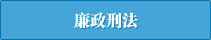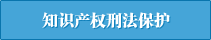姜涛:价值性冲突犯罪及其立法策略展开
2013-07-18 点击次数:4211
姜涛:《价值性冲突犯罪及其立法策略展开》,载《中国刑事杂志》第2013-1期。
【内容提要】在犯罪学上,犯罪有物质性冲突犯罪与价值性冲突犯罪之分,前者意味着犯罪目标是追求某种物质利益,而后者则体现为犯罪人对当前法律、制度等之合理性产生了怀疑。对于价值性冲突引发的犯罪,因其涉及犯罪人对自我之社会存在形成了根本否定,因而较物质性冲突犯罪而言不仅更难治理,而且具有更大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与法益侵害性。 由此决定,刑法对此类犯罪不能采用结果本位主义,而是应该以行为为中心,确立新惩罚主义刑事政策,重视刑法保护的“三化”,并对刑法分则的犯罪归类做出调整。
【关键词】敌人刑法 抽象危险犯 价值性冲突犯罪
近年来,随着恐怖活动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快速蔓延,如何有效治理这些犯罪,成为当代刑事政策学的重要命题。从国内学界来看,“社会稳定与反恐斗争、打黑除恶”一直为学者们所关注,并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学界的基本主张是以重刑主义立法政策应对恐怖犯罪、黑社会犯罪等,主要表现为创制或完善国家有关恐怖主义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方面的立法。⑴而就国外学界来看,雅克布斯的敌人刑法理论以其保护规范适用为出发点,主张将实施恐怖犯罪、经济犯罪、有组织犯罪、性犯罪以及其它危险犯罪的行为人视为敌人,不给予其市民对待,⑵这为西方国家打击恐怖犯罪、有组织犯罪等提供了最有力的理论支撑。本文认为,与传统犯罪相比,恐怖犯罪、黑社会犯罪等的侵害对象不仅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敌视的是社会与法律制度等,犯罪人具有顽固的犯罪意志或内心确信,而且是一种具有共性特征的暴力行为的集合体,带有明显的政治性和社会性,它们追求的往往是民众人人自危的社会心理效应。由此决定,现代刑事政策学应该将此类犯罪视为价值性冲突犯罪,并采取一种不同于传统物质性犯罪冲突的立法应对策略。
一、价值性冲突犯罪:一个法社会学的解读
长期以来,犯罪学界一般把犯罪从类型上区分为少年犯罪、老年犯罪、经济犯罪、恐怖犯罪、组织犯罪、贪污犯罪、白领犯罪、电脑犯罪等类型,这是以犯罪主体、犯罪形式、犯罪对象等为分析视域或工具,并对这些因素结构性考察的结果。⑶刑法学界一般是根据犯罪客体区分出刑法分则意义上的十大类犯罪,或者是借鉴域外经验,把犯罪根据法定刑的设置区分为重罪、轻罪。⑷
上述分类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却都没有关注到犯罪治理问题。现代刑法学强调刑事政策学、犯罪学的重要性,刑法学已不再是贝卡利亚所言称的“有罪必罚、重罪重罚、轻罪轻罚”这种单一的形式逻辑,而是需要从犯罪治理理念出发,对不同的犯罪采用不同的治理策略,这就会带来了犯罪与刑罚模式的变化。长期以来,我们从理论上认为犯罪在不同学科中的意义不同。不管是犯罪学家抑或刑法学家,还是超越了犯罪学与刑法学困囿的社会学者,大都承认这样的结论:犯罪是一种社会应该予以否定而以刑罚加以制裁的行为,犯罪乃是社会公敌,对于这些人只需科处刑罚,以刑罚的痛苦均衡犯罪的恶害,以刑罚报应其罪行。为此,国家需要以强制手段,恐吓欲犯罪的人或将犯罪人以隔离排害。在这种认知之下,只要拥有一部完善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并由司法机关严格执法,则足以合理组织对犯罪的反应。
果真如此吗?笔者认为,这恰是问题的所在。现代刑法学必须重视犯罪学的研究,准确反映特定社会的犯罪结构,并正确认识犯罪的本质特征,这不仅是实现刑法学与社会学沟通的重要手段,而且也是确保犯罪治理成效的重要保障。这是因为:刑法发展不过是一个信息发生和执行器,只有确保源头信息的准确,这才会增大产生最后想要效果的概率。刑法变革之所以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在于它符合社会已然存在的犯罪结构及其变化趋势,符合人们的正义要求,人们应当遵守它。如果刑法变革不能准确反映现实社会中已然存在的犯罪结构及其变化趋势,不仅人们不会遵守刑法,而且刑法适用的实效就会受到威胁,甚至丧失。⑸不难看出,针对“刑法是什么”这一命题的追问,在大陆法系抽象性思维模式的支配下,学者们一般是从既有的概念、原则与规范展开演绎,以犯罪、责任和刑罚为逻辑主线建构刑法帝国。问题只在于,刑法并不是一门自给自足的学问,刑法自身的罪刑图像是什么,也应该放在社会生活中被法律实践映现的社会图像上去理解,正如欧洲法社会学界巨擘埃利希所言:“在当代以及任何其他的时代,法的发展的重心既不在于立法,也不在于法学或司法判决,而在于社会本身。”⑹其中,社会图像是指立于观察者的角度,撷取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下,社会所呈现出的各种形貌。任何刑法理论与实践都以其特有的社会图像为其罗盘指向,而社会图像则复受其背后的社会关系所规范。刑法学上的社会图像,则系讨论刑法学上对社会的观察与预设两个交互影响的问题。其间的连结关系脱离不开对刑法规范本身的效力来源以及规制目的之设定,更重要的是立于社会脉落下的论述。⑺它是从社会的角度,撷取在不同国家在不同时点上对社会现实的具体观察与预设,从而为刑法法规范提供丰富营养和最佳质料。
立足于上述分析视角,我们便能发现价值性冲突犯罪的客观存在。在社会学上,犯罪乃社会冲突的种属,而社会冲突有物质性冲突和价值性冲突之分。社会学研究成果表明,收入分配和财产占有方式的不公正是当前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这就容易引发社会冲突。在冲突论社会学家科塞看来,导致人们形成冲突的原因主要有两类:一是由“物质性原因”,即为了争取物质利益而发生的冲突;二是“价值性原因”,即由于信仰或价值评判标准的差异所导致的冲突。一般来说,物质性冲突对于改善社会制度是有好处的,它不会威胁到这个社会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基础。可是,价值性冲突却不同。如果某个阶级或某个阶层对这个社会存在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或者对这个社会规范人们行为的主要价值准则和制度体系产生了动摇,那么,它就会威胁到这个社会的“生存”。⑻社会学界有关社会冲突的分类对犯罪分类具有重要启示。笔者认为,因物质性冲突和价值性冲突导致的犯罪分别被称之为物质性冲突犯罪与价值性冲突犯罪,前者是为了获得某种物质利益而实施的犯罪,后者则是因为对制度或法律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产生怀疑,因信仰和价值偏离而实施的犯罪。⑼其中,就价值性冲突犯罪而言,它主要有如下特征:
其一,价值性冲突犯罪源于价值观的偏离。如果说犯罪是犯罪学家根据自己的理论构想,并依据一定客观指标所划分的社会冲突的话,那么,犯罪之下的价值性冲突犯罪和物质性冲突犯罪则关顾到了行为人自己以自我影像为表现对象的犯罪定义,也考虑到了社会整体对行为人之行为的意义识别,因而属于价值观问题。从哲学上分析,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对周围的客观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是人们所持有的关于如何区分好与坏、对与错、符合与违背意愿的总体观念,是关于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的基本见解。在价值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人们逐渐形成了关于各种价值的看法,并形成一定的价值观。个人的价值观一旦确立,便具有相对稳定性,并普遍地、深层次地制约、规范、引导着人的全部生活和实践活动。⑽而价值性冲突乃是源自于价值观的偏离,比如,在恐怖活动这类价值性冲突犯罪中,犯罪人通常都享受其行为,认为这种行为是为了追求正义而对抗不公平的社会。同时,恐怖分子一般对团体和首脑十分忠诚,愿意为组织执行任务,为此,行为人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制造人肉炸弹等自杀式的爆炸,且引以为荣。⑾
其二,价值性冲突犯罪比物质性冲突犯罪更难治理。一般而言,价值性冲突犯罪具有更为顽强的犯罪意志和更高程度的法益破坏性。以恐怖犯罪为例,这类犯罪大都具有政治目的,且长期非法诉诸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意图制造极度的社会恐慌,甚至不惜伤害无辜群众。⑿为了有效达成目标,必须能够操纵整个社会,以传递其诉求,这才是恐怖活动的主要目的。正如恐怖犯罪活动专家库珀(cooper)所指出,恐怖活动使民众产生恐惧,但其目的却不在于此,而是为了获取或维持对其他人的控制。⒀从理论上分析,价值性冲突犯罪属于刑法意义上的确信犯(uberzeugungstater),即行为人为了某种理想或信念而形成确信,认为必须以其行动(犯罪,笔者注)使其理念成为事实,即为了实践其确信而实施犯罪,并相信自己所实施的某种犯罪行为是正义的行为。⒁而更为重要的是,对这些犯罪人来说,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在犯罪,而是认为是在进行“革命”。由此决定,价值性冲突犯罪比一般意义上的物质性冲突犯罪更难治理,并且一旦实施,也会造成更大的法益侵害。所以,现代刑事政策必须把价值性冲突犯罪作为规制的重点。
其三,价值性冲突犯罪之违法性意识认定特殊。价值性冲突犯罪人之违法性意识认定面临双重选择:一方面,价值性冲突犯罪大都属于确信犯,而确信犯的故意与违法性意识,一直是故意论和责任论讨论的焦点之一。一般认为,确信犯是基于道德的、宗教的或政治的确信而实施的犯罪。确信犯的实施往往是处于利他的、进步的动机。以恐怖犯罪为例,恐怖分子是指基于传统本身信念并要求外界予以重视的目的,进而有系统地使用高压、胁迫手段的个人,⒂而恐怖活动对抗的往往是恐怖分子认为不公平的社会,包括所有不支持他们的人们,⒃犯罪人也不认为自己是罪犯,宁愿别人称之为“革命分子”,⒄包括分离主义、宗教、解放、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组织形式。⒅因此,就整体犯罪而言,行为人之违法性意识较低。但另一方面,价值性冲突犯罪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或社会理想,通常使用暴力、威胁或骚乱等方式制造恐怖气氛,不仅会造成交通工具、通讯系统、能源供应、金融体系等的滞涨或崩溃,而且往往针对无辜民众实施绑架、爆炸等犯罪,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危害十分严重。对这类具体的法益侵害结果而言,行为人又具有明显的违法性意识。
于此要追问的是,价值性冲突犯罪侵害的是刑法中最重要的法益吗?现代刑法理论认为,刑法的任务在于保护法益,法益亦具有一般法益、重要法益与特别重要法益之位阶区分。长期以来,我们一般习惯性地借鉴德日国家刑法理论及立法规定,把生命权、健康权作为最重要的法益,比如,陈志龙教授将法益的位阶概括为:生命、身体、自由、财产和名誉等。⒆拉伦茨教授则认为,相较于其他法益(尤其是财产性的利益),人的性命或人性尊严有较高的位阶。⒇为何现代学者都把人身法益赋予法益保护位阶的优先性,这是因为:法益有可衡量与不可衡量者之分,如生命、健康等就是不可衡量的(incommensurable),财产则属于可衡量的法益,同时,生命法益不存在质的差别,只存在量的差别。(21)
难道没有比生命法益更重要的法益吗?比较而言,价值偏离应该成为刑法保护中的“特别重要法益”。我国刑法分则把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和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排列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政治权利犯罪之前,这就表明,立法者认为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比单一的公民人身权利要重要。笔者认为,立法者的这一选择是正确的。其一,从实证角度分析,危及国家安全犯罪往往会导致战争或内乱,从而造成多数的、不特定人员的伤亡,并且往往将杀人、伤害、强奸等包括在内,而危及公共安全犯罪也涉及不特定多数人的伤亡,比如,1990至2001年,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在我国新疆制造20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各族群众、基层干部、宗教爱国人士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其中,包括多次在乌鲁木齐公共汽车上实施爆炸,5辆汽车被炸毁,12人丧生,91人受伤。(22)可见,国家安全、社会安全是一种比单一的生命权、健康权更重要的法益;其二,从理论角度分析,个体人意味着人是一个独立人格的个体,国家与社会都为个体服务的,决不能为了维护秩序为由而侵犯个体自由。而集体人则意味着个体乃是社群中的一员,只有集体秩序,才有个体自由,重视个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两种对人之图像的假设,大体上可以对照东方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之间的差异。西方国家是以人为本位、主体性地位为立论出发点;而东方国家则多将人隐藏在集体性、集团性社群之内。但是近年来,随着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西方学者也开始重视社群主义的必要性,强调国家安全、社会安全的重要性,以及由此对公民之个体自由的限制。其三,在国外刑法或我国其他地区刑法中,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或公共安全犯罪大都以特别刑法方式规定,并不规定在刑法典中,而刑法典规定的基本上是常规的自然犯,以我国台湾为例,刑法典并不涉及有组织犯罪,而是以特别刑法——《组织犯罪仿制条例》对此予以详细规定。而学者在论及法益论时,又主要是立足于刑法典进行分析,因而强调人身法益的优先性。
总之,现代刑法应该重视价值性冲突犯罪,并应根据价值性冲突犯罪的本质,寻找有效的、正义的政策选择,以合理组织对此类犯罪的反应。
二、价值性冲突犯罪:敌人刑法的核心命题
雅科布斯认为刑法有两种:一种为市民刑法(Burgerstrafrecht);一种为敌人刑法。如果刑法类型不同,则刑法目的亦不同。在市民刑法之下,刑罚的目的在于保护最低限度的规范认知的市民行为。换言之,为了保障个人自由;而在敌人刑法之下,刑罚在于针对无法提供保证的敌人行为,纯粹是一种排除,功能不外乎是利用物理性威慑来达到事前预防机能(或曰防卫),因此,它更注重维护安全。同时,他还归纳出了敌人刑法的四个特征:“处罚范围的前置化”、“罪刑不均衡”、“向一般犯罪领域的扩散”和“程序保障的限制”。在这种认知之下,他把恐怖袭击、黑社会、严重危及经济秩序等犯罪纳入敌人刑法的范畴。(23)不难看出,雅科布斯是希望将敌人刑法从市民刑法中切割出去,以保护市民刑法的根基。在雅氏的敌人刑法之下,恐怖袭击、黑社会、严重危及经济秩序等重大犯罪人不配被再当作市民来看待,而是应把他当作敌人来战争,而战争的目的只是为了抗击“危险”。(24)
作为市民刑法的例外,敌人刑法理论把恐怖袭击、黑社会等犯罪作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顽疾,主张以严刑峻法对抗此类犯罪。敌人刑法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其一,敌人刑法理论与法治国原则存在内容上的互斥性,(25)敌人刑法乃是市民刑法的例外,两者之间是一种例外与原则的关系,目的还在于捍卫市民刑法的体系性,正如国外学者所言,“敌人刑法的唯一目的,即是为了捍卫体系的存在。”(26)其二,所谓“敌人”是对于某类特别犯罪人的描述,因为该类犯罪人具有特别的危险而应当在立法与司法上予以特别处遇。可以说,雅克布斯眼中的敌人是游离于大众之外,长期决意违反法律的人或“本质上的犯罪人(prinzipiell delinquierende Person)”(27)因此,对市民处罚其已经实施的犯罪,而对敌人则是防范即将实施的犯罪。(28)其三,敌人刑法属于典型的机能主义刑法,以法益保护前置化、法益保护拟制化等有效控制风险,这被雅科布斯称之为“在希望和平的人的手中导致了一种有缺陷的安定”。(29)
雅克布斯的敌人刑法理论也并非没有问题,除了不少学者认为其违反法治国原则外,也存在其他问题:其一,雅克布斯是“规范违反说”的忠实坚持者,(30)但是,如果采用敌人刑法理论,对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等价值性冲突犯罪采用“处罚范围的前置化”、“罪刑不均衡”、“向一般犯罪领域的扩散”和“程序保障的限制”的立法策略技术,则不仅不会强化行为人对规范的认同,反而会造成行为人对规范更为强烈的破坏,这与雅氏主张的“规范违反说”背道而驰。就此而言,即使坚持敌人刑法理论,这一理论也是建立在“法益侵害说”之上的,即这类犯罪在和平时期会造成比一般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治安犯罪更为严重的法益侵害,是人类步入风险社会之后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风险之一,因而需要刑法以法益保护的前置化、抽象化与严厉化等立法策略予以有效应对。其二,雅克布斯除了把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列入敌人刑法理论之外,还把经济犯罪纳入其中。他指出,对恐怖主义犯罪、有组织犯罪、经济犯罪,甚至包括对某些性犯罪的处罚方面,针对行为人本身的危险特质将可罚性前置,在犯罪行为真正实施之前即启动刑法,以保护社会不受这些严重犯罪的侵害。(31)问题是,经济犯罪与恐怖活动犯罪、有组织犯罪并不相同,前者是典型的物质性冲突犯罪,它只为获得物质性利益,因而犯罪手段比较温和,一般并不涉及对人身法益的侵害;而后者则是典型的价值性冲突犯罪,(32)它们是源于对某种社会制度、国家政权或法律制度等的不信任或极度蔑视而导致的犯罪,并且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往往以爆炸、防火等方式实施杀人、伤害,严重侵犯公民的人身法益。因此,把经济犯罪纳入敌人刑法范畴属于明显不当。
敌人刑法作为一种应然的理论建构是否具有正当性?国外学者形成了两大对立阵营,肯定论立足于风险社会下风险控制的需要,认为敌人刑法以其特有的法益保护前置化、抽象化、严厉化等而满足了风险控制的需要,并且也与德日国家近几十年来刑事立法发展趋势相符合。这一主张主要为雅克布斯所主张。但更多学者认为,敌人刑法理论违背了现代法治国原则,同时为了实现虚拟的犯罪风险而侵犯公民自由,也会导致犯罪惩罚成本的提高。(33)在国内刑法学界,对敌人刑法也形成了完全相反的观点。(34)学者们争论的焦点是,敌人刑法中的犯罪包括哪些?学界的普遍担忧是:界定标准的模糊会为国家机器滥用权力打开方便之门,如果在确定具体的适用对象时,把市民也误作为敌人,对其发动所谓的“战争”,其后果就不再仅仅是局部地破坏法治国原则,而是带来司法的任意性和程序保障的缺失。因此,倡导在市民刑法之外,把敌人刑法作为市民刑法的例外,其后果极有可能不是像Jakobs所说的那样有利于维护市民刑法之下的法治国家形象,而相反,它会从内部削弱法治国的思想和侵蚀法治国的生存根基。(35)应当说,在适用对象不明之时,学者们的这一担心不无道理,它的确会给国家滥用刑罚权提供籍口。就此而言,有学者将其称之为“恐惧刑法(Angststrafrecht)”,(36)也有其合理性。
所以,我们需要以更为合理的标准确定敌人刑法中的犯罪包括什么。如前所述,雅克布斯是从犯罪类型上进行区分,认为恐怖主义犯罪、有组织犯罪、经济犯罪,甚至包括对某些性犯罪。国内有学者在论述犯罪人与敌人的死刑问题时指出,“只有在一种法规范的视角之下,才可能划清犯罪人与敌人的界限”,并且“敌人完全是自己选择了与现实社会的对立。敌人可能是他的自我世界中的斗士或者英雄,但是,他不是他的行为所破坏的现实社会的成员。敌人本质上不是公民,而是公敌。”(37)应该说,犯罪类型是对敌人的类型化表述,而从法规范上把敌人描述成完全选择了与现实社会的对立的人,(38)则表达了学者们对敌人刑法之适用对象的界定。不难看出,“敌人”乃是一种战争术语或政治术语,在和平时期使用这一概念必然会带来误解,也因此而遭受学界的猛烈批判。其实,敌人刑法表达的核心思想是,刑法应该积极应对那种敌视社会制度的行为人,这在雅克布斯那里被描述成为“游离于大众之外,长期决意违反法律的人”,而在冯军教授这里被转化成为“与现实社会的对立的人”。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描述性概念是不合理的,因为它们都会把经济犯罪、惯犯等物质性冲突的犯罪纳入到敌人刑法范畴,也会把因反抗家庭暴力、配偶出轨、索要工资等导致的故意杀人而纳入到敌人刑法范畴,从而导致敌人刑法适用对象的扩大化或解释中的随意化现象。如何避免这一问题,则需要明确敌人刑法说适用犯罪的判断标准。只有确立其合理的标准,才能划清敌人刑法的领地,避免刑罚权被滥用。
笔者认为,敌人刑法视域中的犯罪应该是一种价值性冲突犯罪,即现存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产生了怀疑,从而实施的各种犯罪活动,包括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和因价值性冲突导致的其他犯罪。在这几类犯罪中,前三类比较好理解,也与雅克布斯主张的敌人刑法之适用对象具有重合性。不易界定的是因价值性冲突导致的其他犯罪,它所指的是因行为人对现存的社会制度之合理性与合法性产生了怀疑,而实施的以杀人、放火等方式报复社会的行为,比如,在“李垂才爆炸案”中,行为人因多次婚姻失败,并因为邻居债务纠纷和家庭生活困苦等原因,遂产生报复社会的念头,并于2001年3月6日上午11时20分制造爆炸,造成江西万载县潭埠镇芳林村小学1幢两层教学楼被爆炸倒塌,共计43人死亡,27人受伤。这种犯罪就和一般意义上的故意杀人有明显区别,它是一种典型的价值性冲突犯罪。而相反,非价值性冲突犯罪(比如,经济犯罪、性犯罪等)则不应该属于敌人刑法的范畴。
自敌人刑法理论提出以后,它经常被置于被质疑的浪尖上,但这并不能否定敌人刑法“反叛”市民刑法的意义。随着风险社会时代伴随而来的各种风险的频繁出现,民众对风险控制的需求也自然水涨船高,立法者以法益保护前置化、抽象化、严厉化等立法技术有效规制风险,也就成为现代各国刑事政策的基本选择。(39)对此,如果我们再能够以价值性冲突犯罪与物质性冲突犯罪的基本划分去界定敌人刑法视域中的犯罪类型,则敌人刑法大可不必被称之为恐惧刑法,而是有其适用的社会基础。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刑法应该如何合理应对价值性冲突犯罪呢?
三、价值性冲突犯罪:立法策略的逻辑展开
随着我国刑法走向成文化,价值性冲突犯罪在刑法中也有所体现,这集中地体现在刑法分则第一章的危害国家安全罪、第六章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中。在笔者看来,从理论上明确价值性冲突犯罪理论,比在刑法中四处混杂着有关价值性冲突犯罪的规定对于犯罪控制而言更具意义。这构成了价值性冲突犯罪之立法策略技术的理论基础。而就立法策略而言,中国应该立足于价值性冲突犯罪的本质,强化新惩罚主义策略,重视法益保护的早期化、抽象化和重刑化,并对犯罪归类做出必要调整。
(一)价值性冲突犯罪与新惩罚主义刑事政策
刑罚目的历来有报应论和预防论之重大争论,虽然现代各国刑法已经很难看到只选取其一的立法设计,但是在价值性冲突犯罪问题上,随着各种社会风险事件的不断发生以及民众对恐怖袭击、黑社会犯罪危害之感知的深化,决策者也越来越重视积极的一般预防,从而导致犯罪化立法政策在民众与立法者之间达成了共识。新惩罚主义(neuer Punitivismus)刑事政策也因此应运而生。新惩罚主义刑事政策力图在惩罚主义和报应主义之间达到最佳平衡点,即不仅从惩罚主义的立场出发,强调对犯罪的报应,而且立足于功利主义论辩,重视何种报应能够满足民众的“最大幸福”。这一立场为哈特所主张,他在《惩罚与责任》一书中把惩罚的责任分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惩罚的实施对象,即什么样的人应该受到惩罚的制裁;二是惩罚的实施程度,即应当给予多大程度的惩罚。他进而主张对于第一个问题,可以做出惩罚主义的回答,而对于第二个问题,则可以做出功利主义的回答。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兼顾了惩罚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优点,也就兼顾了公平和功利这两个正义原则。(40)这种综合的观点无疑受到了学界的追捧,并形成了刑法学意义上的新惩罚主义刑事政策。新惩罚主义刑事政策首先就是作为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而提出来的,所以在新惩罚主义看来,对行为人惩罚的目的性是很明显的,那就是要强化公民的规范意识,从而达到减少与预防犯罪之目的。其中,在刑事政策制定方面强调社会安全,把预防的重心前移而提前到犯罪预备阶段,(41)并增加刑罚的严厉程度以使行为人不致危害社会,就是“新惩罚主义”刑事政策的基本策略。(42)
为何要对价值性冲突犯罪采用新惩罚主义刑事政策?雅克布斯认为,敌人刑法的“敌人”是针对被认为有危险的犯罪者,即非朋友(inimicus)的,而不是针对施米特说的政治对立意义上的敌人(hostis)。(43)而同时,雅克布斯以其人格体理论来建构其对敌人的理解,他认为,存在于法律上的人格体(Person—im—Recht—Sein)是可交往的、可沟通的,其他人必须和他共处,若他偶尔犯错,从而成为罪犯,也是可以沟通和补救的。他必须承担他的惩罚,这样才能保证对法的忠诚。只有保持了法忠诚,才成其为人格体,若一而再、再而三地背离规范,并使得妨碍沟通的风险增大到无法忍受的地步时,他就不再是人格体,这就需要对其进行刑法强制。(44)归根结底,这类犯罪人是(敌人)因为根本偏离了规范的要求,国家也无法对其沟通和有效规则,所以丧失了人格体的资格,也就不享有法治国意义上的人权保障,自然也就蕴含着被以重刑主义立法策略对待的可能性:其一,需要法益保护的前置化(把预备行为纳入犯罪圈)与法益保护的抽象化(把没有造成法益侵害但具有法益侵害风险的行为纳入犯罪圈),以避免价值性冲突犯罪带来严重的法益侵害结果。其二,对于已经造成法益侵害的犯罪人来说,运用加重的犯罪构成,并可以背离刑罚轻缓化的发展趋势,采用包括死刑在内的重刑罚予以有效应对,并可以将保安处分适用于具有社会危险的人,以减少其对社会带来的风险,有效提升刑法防卫社会的效果。其三,新惩罚主义刑事政策还意味着严厉打击与恐怖活动、黑社会犯罪活动相关的犯罪。以恐怖活动为例,恐怖主义其实包括了许多其它常见的犯罪,例如伪造文书、信用卡诈骗、人蛇走私甚至盗版商品(侵害著作权)等,也包括散布恐怖主义出版品、煽动他人实施恐怖活动、散布虚假的恐怖信息、包庇纵容黑社会犯罪,资助黑社会犯罪或恐怖活动犯罪等,以消除其犯罪的相关因素。(45)
新惩罚主义刑事政策的第一个核心命题是应该惩罚侵犯重大法益的实质预备行为。价值性冲突犯罪之预备犯是否应该纳入刑法调控范围?这主要有肯定论与否定论两种观点,前者认为,价值性冲突犯罪具有较高的危险性,一旦发生恐怖袭击、内乱等价值性冲突犯罪,就会造成严重的法益侵害结果,这种法益侵害结果自然不能为民众所接受,这些犯罪针对第三人生命、健康和财产损害的危险性,就像伪造货币对交易秩序的危险一样,具有提前介入以惩罚预备行为的必要性。(46)后者认为,处罚预备行为会导致刑法丧失其功能,如果把危险人物都纳入刑法调整的话,事实上就没有了以行为为基础的刑法,有的只是以行为人为基础的治安法或警察法。(47)笔者认为,上述“二择一选择题式”的见解都不可取,在刑法的框架体系下,行为之可罚性的有无应该以法益侵害预防的角度出发,以行为人对法益侵害的控制作为检验标准。而预备犯有形式预备犯和实质预备犯之分,前者以行为本身造成法益侵害的抽象危险性为处罚的根据(大致相当于抽象危险犯),而后者以行为本身足以造成法益侵害危险的客观现实性为处罚根据(大致相当于具体危险犯)。(48)很显然,新惩罚主义惩治的不仅是实质预备犯,而且包括形式预备犯,这集中体现在刑法规定了一定数量的抽象危险犯(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在下文还有详细论述)。
新惩罚主义刑事政策的另一核心命题是以保安处分预防和控制价值性冲突犯罪风险。敌人刑法理论处理规范违反者之特别之处在于,它不仅要受到罪责上的惩罚,而是要在行为之前或附带进行保安处分。(49)保安处分是现代刑法和刑事政策上最重要的问题。自18世纪末德国刑法学者克莱茵初步创立保安处分的理论基础以来,诸多保安处分理论的赞同者就保安处分应当立法化并付诸实践的根本问题达成了共识,并在19世纪产生后迅速发展,成为许多国家刑法的组成部分。保安处分被立法化的基本理由是:对于刑法上的犯罪,并非只有期待可以通过刑罚就可以达到完全的控制以及矫正的效果。对于有价值性冲突犯罪倾向的人,无论多么危险,都处在道义性刑法的范围之外,对于由物质性冲突犯罪转向价值性冲突犯罪的犯罪人,通过刑罚处罚明显难以实现将来的犯罪预防任务,这也具有科处保安处分的必要性。(50)事实上,即使与大陆法系传统不同的美国,因为实施了最小剂量毒品法、“三振法案”(threestrikes,you’re out)等法律而带来的监禁率的大幅提高,以及其他的政策改变所产生的刑期更长,被绝大部分“强硬起来”执法方式的支持者认为,这是驱使犯罪率向下走的力量。(51)当然,这也可以被视为是保安处分的“变通方案”。
(二)价值性冲突犯罪与刑法保护的“三化”
刑法保护的前置化、抽象化与严厉化(以下简称“三化”),这是风险社会时代下刑法发展的新趋势。“三化”的出现是否具有正当性?这在学界引起了重大争议。通过对近代刑法与现代刑法的比较,强调法益保护的抽象化与前置化、严厉化,均是现代刑法的特征,(52)并通过处罚未遂犯、危险犯和预备犯等规范和加大处罚力度予以实现。(53)不少学者对此发展趋势持否定态度,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指出,抽象危险犯是对自由法治国刑法及刑法典作为公民大宪章的一个攻击。(54)台湾学者也指出,抽象危险犯与国际上非犯罪化的发展趋势相冲突,同时也违反了刑法的谦抑原则和罪责原则。(55)而国内学者也指出,在行为实施之前采取提前的实际警戒和保障可以阻止危害的结果发生,意味着实施行为时行为人的动机、想法、观念等主观层面的因素均将成为可罚性的判断基准,这是反法治的,也违反了现代刑法谦抑主义。(56)笔者认为,否定立场显然忽视了现代刑法所面临的犯罪结构有别于传统刑法的这一基本事实,价值性冲突犯罪作为一种社会顽疾,虽然在任何时代均存在,但是在当今时代体现得更为明显,一旦实施,其造成的危害也更大,因此,试图以传统刑法的研究范式一以贯之的做法也必然在解释学上捉襟见肘。这是因为:其一,刑法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唯理主义的,当社会发生了变化之后,刑法规范自然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在当今时代,价值性冲突增加不仅是一种客观现实,恐怖袭击、黑社会犯罪等都是农业社会所不具有的现象,而且也是民众感受风险的产物,无论是“9.11”事件造成的巨大伤亡,抑或各国黑社会犯罪带来的贩卖毒品、组织卖淫等,都使一般民众感受到价值性冲突的巨大杀伤力以及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强烈反差。因此,以重刑化立法政策应对价值性冲突犯罪,也往往在民众与决策者之间达成空前共识。其二,刑法谦抑主义原则作为市民刑法的基本理论,虽然有利于划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边界,但也存在着明显的消极影响,即在确保刑法之有限性的同时,却一并抹杀掉了刑法的功能性。同时,如何协调刑法的自由规制机能与秩序维护机能之间的关系,刑法谦抑主义立足于自由主义的立场所提供的标准也是极为片面的,也不是社会的。这都需要以其他的理论分析工具予以补救,敌人刑法理论即是其一。其三,即使是现代责任主义原则,也有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它经历了先从结果责任论到心理责任论、后从心理责任论到规范责任论、再从规范责任论到功能责任论的演变历程。其中,功能责任论的核心主张是,行为人是否具有责任,要根据行为人对法规范的忠诚和社会解决冲突的可能性来决定。(57)很显然,刑法保护的“三化”,乃是功能责任论的一个维度,目的在于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而不是单一地确保公民的自由。
对于价值性冲突犯罪而言,由于其属于“社会顽疾”,行为人具有极高的人身危险性与主观恶性,十分难以治理。而同时,此类犯罪一旦付诸实施,则会带来严重的、现实的法益侵害性。所以,对此类犯罪实行刑法保护的“三化”至为重要:一方面,对价值性冲突犯罪实行法益保护前置化与抽象化,能够满足积极的一般预防之需要。刑法保护的前置化意味着把预备犯、危险犯等纳入到犯罪圈,其中,抽象危险犯是法益保护前置化的主要体现。从理论上分析,刑法保护的抽象化符合积极的一般预防的需要。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认为,刑罚设置与适用之目的,应在于“法秩序防卫”,刑罚的主要任务在于对犯罪人施以再社会化与合规范人格化过程中,达到规范内化的目标。(58)简言之,积极的一般预防在于强化一般民众(包括已然的犯罪人)对法律的信仰。对于价值性冲突犯罪的治理而言,积极的一般预防之刑罚目的旨在通过刑罚对社会普遍产生教育的效果,处罚危险阶段特别是抽象危险阶段的行为,以实现预防和减少价值性冲突犯罪之目的。另一方面,对价值性冲突犯罪采取更为严厉的刑罚,也符合现代责任主义原则。根据责任主义原则的要求,刑罚既然是作为有责的违法行为的抵偿,就必须保持责任内容、责任程度与刑种、刑度的适当的比例或者均衡关系。除非基于预防的需要,国家不得基于任何功利主义的考虑,超越责任程度所容许的刑罚上限,适用与罪行及其罪责不成比例的刑罚。(59)这里的“责任”,与作为犯罪成立条件之一的有责性(也称为责任)不是完全等同的含义,而是由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组成的犯罪性,或者说是违法性与狭义的有责性相乘。这种责任不仅能够确证刑罚适用的正当性,而且是适用刑罚时确定刑种、强度及其极限的根据。为此,刑罚必须与违法性及有责性相适应,而其中的违法性是指客观的法益侵犯性、有责性是指主观的罪过性,二者的统一体(罪行的轻重)就是责任刑的根据。(60)如前所述,价值性冲突犯罪人不仅具有更高的主观恶性,而且也具有更为严重的法益侵害性,所以,加重对其的处罚符合现代责任主义原则。
(三)价值性冲突犯罪与犯罪类别的局部调整
犯罪类别的调整体现为对犯罪本质及特性的尊重,这是犯罪类型划分及采用相应立法应对策略的前提,也是刑法走向科学化的重要标志。长期以来,我们把恐怖活动犯罪归类到危害公共安全罪,而把黑社会性质犯罪归类到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笔者认为,这种分类存在着明显失当,应当做出如下调整:
其一,恐怖犯罪是典型的政治犯罪,应该将其归类为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一章。政治犯罪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政治犯罪是指与政治有关的犯罪,亦即一切出于政治的动机而实施的犯罪;狭义的政治犯罪系指政治反对者或政治异议分子,出于政治性的行为动机或为达成特定的政治目的而实施的犯罪行为。(61)恐怖犯罪通常以政治为诉求,藉由暴力或威胁达到制造恐怖或强制的目的,或者说是一种通过暴力实施的政治犯罪。(62)恐怖犯罪和其他犯罪的差异在于没有谋取利益的动机,通常是超越个人利益,以宣传某种理念或实现最大的宣传价值,以吸引媒体广泛报道。(63)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炸弹袭击、挟持人质、抢劫与绑架等就是常见的犯罪手段,并且“为达目的,不计伤亡”。尽管,恐怖犯罪的被害人往往是“随机选取出来”的无辜被害者,并且也具有高死亡率的特性,但这并不是恐怖犯罪的目的,其目的在于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正如美国学者所指出,恐怖分子是有系统地运用暗杀、破坏、暴力或威胁等攻击手段,迫使个人、团体或政府,屈从其政治诉求。(64)所以,这主要是一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而不仅仅是一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其二,黑社会性质犯罪虽然以藐视国家法律为主要特征,并以获取物质性利益为目标,但其危害的却是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财产等安全,应该归类到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传统刑法学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一种藐视国家法纪、为非作歹的行为,因而被归类于刑法分则“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笔者认为,这一归类并不合理,并不符合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本质,一方面,就黑社会性质犯罪而言,其根本特征是通过犯罪活动以获取经济利益或实现其他目标,正如德国学者所归纳,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一种有结构的犯罪集团,策略性地计划并执行国内或国际的长期犯罪活动,以追求高利润或影响公众生活;(65)另一方面,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以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成员为主体实施的各类犯罪的总称,包括刑法第294条规定的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也包括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聚众斗殴罪、贩卖毒品罪、非法经营罪、故意毁坏财物罪、行贿罪、妨碍公务罪、非法持有枪支罪等以黑社会组织名义实施的犯罪,(66)因而具有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等安全之特性。频繁实施的黑社会性质犯罪是一种严重的危害公共安全行为,因为它不仅在一个社区内制造犯罪的恐慌,而且会因为犯罪而导致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等安全受到侵害,因此,属于典型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
文明世界的一切都是可以控制的。面对愈来愈多的价值性冲突犯罪,民众自然要求国家有所作为,因而各国纷纷制定反恐与打黑方面的立法,不仅扩大这类犯罪之犯罪圈,提高此类犯罪的法定刑,而且强化对此类犯罪的侦破力度,从而将仅具有潜在危险的行为纳入刑法规范之下,并减少此类犯罪的犯罪黑数。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不是敌人刑法理论可以解决的,而是要从犯罪学、犯罪心理学上分析犯罪人犯罪的原因,并把犯罪明确地区分为价值性冲突犯罪和物质性冲突犯罪,以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考夫曼曾指出,“在现代多元的风险社会中,人类必须放胆行事,不能老是在事前依照既定的规范或固定的自然概念,来确知他的行为是否正确,亦即,人类必须冒险行事。”(67)无疑,把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犯罪等定位为一种价值性冲突犯罪,并借鉴敌人刑法理论的基本原理,以寻求建构出能够有效应对价值性冲突犯罪的立法体系,这本就是一种冒险行事。但是,这并不失研究的意义,因为本文的分析不仅构成了敌人刑法理论的超越,而且还能够实现“犯罪不发生最好”的刑事政策目标。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赵秉志:“我国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刑法立法经验考察”,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赵秉志、杜邈:“我国反恐怖主义立法完善研讨”,载《法律科学》2006年第3期;王秀梅:“论恐怖主义犯罪的惩治及我国立法的发展完善”,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3期;姜涛:“当前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若干问题研究”,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梅传强、胡江:“我国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刑法完善——兼论对《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相关条款的修改建议”,载《现代法学》2011年第2期。
⑵林立:“由雅科布斯‘仇敌刑法’之概念反省刑法‘规范论’传统对抵抗国家暴力问题的局限性”,载台湾《政大法学评论》2004年10月第81期。
⑶林山田、林东茂、林璨章著:《犯罪学》,台湾三民书局2007年版,第251—602页。
⑷王文华:“论刑法中重罪与轻罪的划分”,载《法学评论》2010年第2期。
⑸姜涛:“迫寻理性的刑法变革”,载《江苏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4期。
⑹[奥]欧根·埃利希著:《法社会学原理》,舒国滢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作者序”。
⑺Ulrich Becker,Das Menschenbild des Grundgesetzes in der Rechtsprechung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1996,S.118ff.
⑻张翼:“中国城市社会阶层冲突意识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⑼姜涛:“社会管理创新与经济刑法双重体系建构”,载《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6期。
⑽吴向东:“论价值观的形成与选择”,载《哲学研究》2008年第5期。
⑾See Bolz,Dudonis,&Schulz,the Counterterrorism Handbook:Tactics,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FL:CRC Press,2000,pp.7—8.
⑿See Siegel,Criminology,6th edition,West/Wadsworth,1998,pp.305—306.
⒀See Reid,Crime and Criminology,NY:MeGraw—Hill,2003,pp.223—225.
⒁Vgl Ebert,der uberzeugungstater in der Neueren Rechtsentwicklung,1975,S.7,10f.
⒂张中勇:“国际恐怖主义的演变与发展”,非传统安全威胁2002年度研究报告,第33—34页。
⒃同注⒂。
⒄See Schmalleger,Criminology Today:An Integrative Introduction,NJ:Prentice—Hall,1999,p.377.
⒅See C.J.M.Darke,Terrorists’Target Selection,Macmillan Press,1998,pp.16—17.
⒆See Vito,Criminology:Theory,Research and Policy,CA:Wadsworth,1994,pp.289—290.
⒇[德]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85页。
(21)See Robert George,A Problem for Natural Law Theory:Does the“Incommensurability Thesis”Imperil Common Sense Moral Judgments?36 American Journal of Jurisprudence(1992),pp.185—187.
(22)转引自周良沱、章剑:“恐怖犯罪三题”,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23)李茂生:“风险社会与规范论的世界”,载台湾《月旦法学杂志》2009年10月第173期。
(24)Gunther Jakobs.Burgerstrafrecht und Fenidstrafrecht,in Foundations and Limits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al PrOcedure an Anthology in Memory of Professor Fu Tseng Hung edited by Yu Hsiu Hsu Taipei,2003,pp.48—52.
(25)Vgl Jakobs,Feindstrafrecht?——Eine Untersuchung zu den Bedingungen von Rechtlichkeit,HRRS,2006,S.290.
(26)转引自王莹:“法治国的洁癖——对话Jakobs‘敌人刑法’理论”,载《中外法学》2011年第2期。
(27)Vgl Jakobs,Burgerstrafrecht und Feindstrafrecht,HRRS,2004,S.90.
(28)Miguel Polain—Orts:“以功能破除概念迷思:敌人刑法”,徐育安译,载《法学新论》2010年第5期。
(29)[德]雅科布斯:“市民刑法与敌人刑法”,徐育安译,载许玉秀主编:《刑事法之基础与界限——洪福增教授纪念专辑》,台湾学林文化事业公司2003年版,第17页。
(30)Vgl Jakobs,Feindstrafrecht?——Eine Untersuchung zu den Bedingungen von Rechtlichkeit,HRRS,2006,S.290.
(31)Vgl Jakobs,Burgerstrafrecht und Feindstrafrecht,HRRS,2004/3,S.92.
(32)长期以来,我国学界把黑社会组织犯罪定位为一种为了获得某种物质性利益而结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笔者认为,黑社会组织犯罪的本质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聚众斗殴、贩卖毒品、组织卖淫等藐视法律制度的行为,而不是单一地获得某种物质性利益,因此它并不属于物质性冲突犯罪,而是典型的价值性冲突犯罪。
(33)Vgl Bung,Feindstrafrecht als Theorie der Normgeltung und der Person,HRRS,2006,S.68.,Sinn,Morderne Verbrechensverfol—gung—auf dem Weg zu einem Feindstrafrecht?ZIS,2006,S.114;Hoernle,Deskriptive und Normative Dimensionen des Begriffs“Feindstrafrecht”,GA,2006,S.91.
(34)肯定的观点详细请参见冯军:“死刑、犯罪人与敌人”,载《中外法学》2005年第5期;何庆仁:“刑法的沟通意义”,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1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175页。反对的观点可参见刘仁文:“敌人刑法:一个初步的清理”,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6期;王莹:“法治国的洁癖——对话Jakobs‘敌人刑法’理论”,载《中外法学》2011年第2期。
(35)王莹:“法治国的洁癖——对话Jakobs‘敌人刑法’理论”,载《中外法学》2011年第2期。
(36)Bung,Feindstrafrecht als Theorie der Normgeltung und der Person,HRRS,2006/2,S.70.
(37)冯军:“死刑、犯罪人与敌人”,载《中外法学》2005年第5期。
(38)这里所谓的“实在法的基本规范”,是指现实社会所必不可少的法规范,也就是现实社会中保护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的法规范。参见同注(37)。
(39)姜涛:“风险社会之下经济刑法的基本转型”,载《现代法学》2010年第4期。
(40)贺建军:“惩罚的正义——在惩罚主义与功利主义之间”,载《道德与文明》2009年第1期。
(41)黄荣坚著:《基础刑法学》(下),元照出版社2006年版,第508页。
(42)Vgl Meliá,Feind“strafrecht”?ZStW 117,2005,S.270f.
(43)Vgl Günther Jakobs,Feindstrafrecht?Eine Untersuchung zu den Bedingungen von Rechtlichkeit,HRRS,2006,S.294.
(44)转引自蔡桂生:“敌人刑法的思与辨”,载《中外法学》2010年第4期。
(45)比如,英国在美国9.11事件以后通过的“Prevention of Terrorism Act 2005”,就把恐怖主义的鼓励、散布恐怖主义出版品、恐怖攻击行动的预备、恐怖主义的训练、出入恐怖主义训练的场所、制造且持有辅助材料或设备等九种行为纳入到恐怖犯罪之列。
(46)Vgl Wolfgang schauble,Strafbarkeit von Vorbereitungshandlung bei terroris tis chen Handlunge?ZRP,2006,S.71.
(47)Vgl Heribert Prantl,Strafbarkelt von Vorbereitungshandlung bei terroris tis chen Handlunge?ZRP,2006,S.71.,Wolfgang Hetzer,terrorbekampfung—Strafverfolung oder Kriegsführung?Kriminalistik,2004,S.508.
(48)也有学者认为,形式预备犯因其形式上即为所欲实行的目的犯罪的预备行为,并据此预备行为而被刑法规定为目的犯罪的预备犯;实质预备犯则是构成要件行为形式上虽然不是其它犯罪的预备行为,但立法是因其可能成为其它犯罪的预备行为而将其规定为独立的犯罪。参见梁根林:“预备犯普遍处罚原则的困境与突围——《刑法》第22条的解读与重构”,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2期;陈子平:《刑法总论》,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369页。
(49)Vgl Günther Jakobs,Feindstrafrecht?—Eine Untersuchung zu den Bedingungen von Rechtlichkeit,HRRS,2006,S. 294—295.
(50)[日]大塚仁著:《刑法概论(总论)》(第三版),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06—507页。
(51)[美]朱迪·格林:“‘零容忍’:对纽约市警务政策与实践的个案研究”,朱宏译,载《公安学刊》2009年第2期。
(52)[日]生田胜义著:《行为原理と刑事违法论》,信山社2002年版,第19页。
(53)[日]高桥则夫:“刑法保护の早期化と刑法の界限”,载《法律时报》2002年第75卷2号,第16页。
(54)[德]约克·艾斯勒:“抽象危险犯的基础与边界”,蔡桂生译,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2008年第2期,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37页。
(55)林东茂著:《危险犯与经济刑法》,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15—48页。
(56)刘艳红:“‘风险刑法理论’不能动摇刑法谦抑主义”,载《法商研究》2011年第4期。
(57)冯军:“刑法中的责任原则——兼与张明楷教授商榷”,载《中外法学》2012年第1期。
(58)王振:“刑罚目的的新思维:积极一般预防”,载《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59)梁根林:“责任主义原则及其例外——立足于客观处罚条件的考察”,载《清华法学》2009年第2期。
(60)张明楷:“结果与量刑——结果责任、双重评价、间接处罚之禁止”,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61)林山田、林东茂、林璨章著:《犯罪学》,台湾三民书局2007年版,第440页。
(62)See Reid,Criminal justice,MA:Allyn and Baconl,2002,p.130;James M.Luts and Brenda J.Lutz,Terrorism Origins and Evolution,Palgrave acmillan,2005,pp7—9;David J.Whittakered,The Terrorism Reader,New York:Rout Ledge,2001,p.3.
(63)See Albanese,Crime and Criminology,NY:Me Graw—Hill,2003,pp.223—225.
(64)See Siegel,Criminology,6th edition,West/Wadsworth,1998,pp.305—306.
(65)Vgl Dormaan/Koch/Risch/Vahlenkamp,Organisierte Kriminalitatwie Groβist die Gefahr?BKA—Forschungsreihe,Sonderband,1990,S.6.,Burghard/Herold/Hamacher/Schreiber/Stumper,Kriminalistik Lexi—Kon,2.Auff.,1986,S.172.
(66)姜涛:“当前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若干问题研究”,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67)[德]考夫曼著:《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26页。